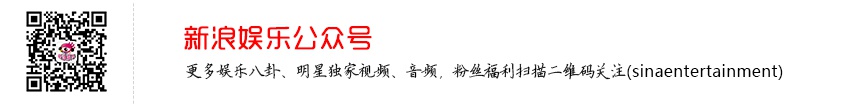文/徐元
1、
最残忍的一幕,发生在尾声:比利·林恩告诉心爱的姑娘:我现在就想带着你跑,当逃兵算了。可是,怀里的女孩却花容失色:逃跑?怎么可能?你不是马上就回战场了吗。
就在这一瞬,比利心碎了。他才发现,火辣辣的一见钟情,其实只是两人之间的一场误会。

然后,他勉强笑了,局促地道别,彻底明白了“我们当兵的,只能拥有彼此”到底是什么滋味。
他也就此下定决心,拒绝姐姐争取来的退伍可能,而要和B班的弟兄们一起返回伊拉克前线。
“李安电影”注册商标式的细腻、感伤、残酷,以及李安其人调教年轻演员的卓绝能力,全都浓缩在了这三分钟的戏里。

2、
读解《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角度有很多,大都言之在理,比如讽刺所谓的“爱国主义”、批评美国公众对于军人的态度、批判美式资本主义支撑的政经逻辑及生活方式……
不过,需要注意,李安电影一向不是“控诉体”,他不是站在原告席上,大声疾呼地指责“你们居然这样”,而是每每坐在被告席上,平静而略带悲戚地承认,“我们就是那样”。
所以,他爱说“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玉娇龙”“人人心中有座断背山”,真是在直抒胸臆。

可爱的啦啦队长菲姗,她钟情的其实是那位出生入死英勇无惧的战斗英雄,而非和自己一样会担心汽车引擎有异响、猫抓坏了沙发等等琐事的同乡小伙子
——就好比殷离对“恶狠狠的张无忌”的痴迷——所以,虽然菲姗矫情且自欺,可你也不能说她的情感不是真挚的、她从英雄比利身上得到的那些触动就完全是虚妄的。

那位不请自来的石油商人呢?词锋犀利的班长一通抢白,让他讨了个大大的没趣。
但实际上,班长又何尝不是在自欺欺人呢:阿兵哥哪里都个个杀戮成性了?而挖油的大叔同情子弟兵,想让他们平安回家的心意,难道仅仅是虚伪吗?
最说明问题的,是班长带着比利去和球场大亨的那场谈判。

比利最后义正辞严,痛陈对方不过想利用他们,是无良奸商在消费爱国主义,当然说得痛快淋漓又大快人心
——然而,如果大亨确实能按每人10万的价码“买下故事”,比利还会严词拒绝吗?还会觉得“一点没有未必不如多少有一点”吗?
——说到底,B班弟兄念兹在兹的预付款,明明就是一桩生意经,他们实则不是真的憎恨自己被商品化,而是没法接受低价罢了。

一贯牙尖嘴利的班长之所以后来语塞,是因为他心里知道,他们受到了两重(层)羞辱——
第一层是,不论前线后方,他们都不得不像玩偶一样被摆布,甚至他们的出生入死、同袍牺牲的伤心事,都要被当做商品来贩售;而第二层则是,即便这样,他们的“价格”都还要被压榨到不堪。
第一层是潜藏的,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因为这几乎是时代或曰社会赋予的一种无差别的待遇;而第二层却非常有针对性,仿佛一记耳光打在了脸上。

于是,这段戏就成了整部电影的缩影:这伙大兵,总是不自知地身处在一个既错误又尴尬的地方,不管此间是一座巴格达的集市,还是一位前伊军少校的居所,还是一处叛军占领的学校,或是体育场的一片草坪、一排座位、一间办公室、一块临时舞台……
最后,他们都要为此付出或大或小的代价。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些阿兵哥,不过是些“理解不了他们有钱人”的底层孩子,要不是偶然被拍到了视频,他们注定会继续默默无闻。
何况,即便英雄地凯旋了,可实际上也并没有谁真的尊重这些实实在在的个体,亲人觉得他们是政客的炮灰,部队上则安排他们担任宣传工具,中产雅痞奚落他们是在战壕里搞同性恋的娘炮。
媒体和商界则把他们视为可供开发消费的“内容产品”,至于跟他们同阶级而相当于父兄辈的舞台装卸工,还会一言不合地跟他们往死里掐架。

唯一跟他们心心相印的,是那支美女啦啦队,一样的穿制服的小集体、一样的吃青春饭,一样的被物化。
在这个故事里,她们恰好是他们的对应存在,而可悲或者说难堪的是,甚至他们之间彼此吸引,也绝非是出于“心有灵犀”(比利语),而只是基于浅薄,以及,荷尔蒙。
但是,李安对所有人都是体谅的,他知道,世事如此,人情如此,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吉光片羽的真情,就足以支撑我们继续向前。

3、
因此,《中场战事》吸引李安的,本质上还是因为它一如既往地讲述了“败者”的故事(别忘了,比利·林恩最后既没能拯救班长,也没能拯救姐姐)。
作为“撤退到台湾”的外省人之子,李安始终着迷的正是各式各样的败者——王佳芝、绿巨人、少年派、李慕白——的故事。
甚至,在他的电影里,实则也没有胜者,因为不管是易先生,还是玉娇龙,或是郎雄化身的父亲们,最后也都赌输了。
 易先生
易先生《中场战事》看似是关于当代美利坚的,是特别案例分析、特别促狭地讥讽美式资本主义的。然而,和以往的李安电影一样,它又绝不仅仅只是瞄准了当下。
在清朝的武林、在印度的轮船、在南北战争的战场、在1970年代的康州中产家庭、在1990年代的台北饭店里,人和物完全不同,但是理性和感性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无法理解,却是亘古不变。
看待历史或者说世间万象的角度,三个台湾外省人侯孝贤、杨德昌、李安,有共通的一面,但是侯孝贤相信人世苍凉,一代代云卷云舒,就这么过去了,谁也莫可奈何,于是他豁达;
 侯孝贤的《刺客聂影娘》剧照
侯孝贤的《刺客聂影娘》剧照杨德昌则认为世界不该如此不堪,我辈理应大声疾呼不为瓦全,于是他刚烈;
 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剧照
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剧照而李安呢,他明白天下大势不可违,人生困境不可解,但我们仍需勉力与生活媾和,于是他隐忍。
 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剧照
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剧照从喜剧的《父亲三部曲》开始,他的电影就具备了这种气质,当然也充满了阶段性的变奏。
除掉“雇佣作业”的《理智与情感》,随后《冰风暴》和《与魔鬼共骑》转入悲剧,作为美国影坛新锐,李安抵达了某种更深沉更辛辣的境界;
至于《卧虎藏龙》和《绿巨人》,愤怒和决绝的气息强烈了,经历了事业大起大落的他,更看重的是奋力抗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
而《断背山》和《色|戒》,基本是一种冰冷蚀骨的绝望,但他又偏爱这森森寒意中,那一抹微弱的温情。
 《断背山》剧照
《断背山》剧照不过,《制造伍德斯托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这接连的三部西片,年高德劭的李安慢慢趋于平静了,他变得更宽容更怜悯。
这三部戏里其实没有坏人,连吃人、杀人好像都不算罪过了(请注意:后两部戏都是无奈杀了同类的少年唱主角)。
这个阶段的“安叔”,更在乎的是各个不同、注定孤单的生命,不可避免地要彼此交汇、撞击、冲突,而迷人的风景,恰恰是这些鲜活的生命相遇的各个瞬间。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剧照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剧照4、
于是,李安现在最痴迷的是人脸,他认为这是远比其他任何情节、场面、特效更精彩、更直接的“戏剧”。
于是,他义无反顾地祭出了4K、3D、120帧、不化妆、大特写这一整套组合拳,为自己的新发现正名。
不过,为此他付出了可观的代价,亦即让《中场战事》变得“不像电影”,反而仿佛是家电卖场里高端电视上的演示片段。

《中场战事》有些部分,的确实现了李安让我们凝视面孔的目的,也带来了某种别开生面的感受。
可是,作为一部依然需要归类为“故事片”的电影,高清电视式的画质、构图,不但并没有带来视觉上的“舒适”,而且终究干扰了我们对故事的消化。
换言之,基于西方千年绘画传统、又经百年电影工业锤炼,而且事实上早就被李安掌握了的传统电影技法(比如宽银幕、大景深、高对比、低照度等等),其实完全可以赋予《中场战事》更出色、更妥帖的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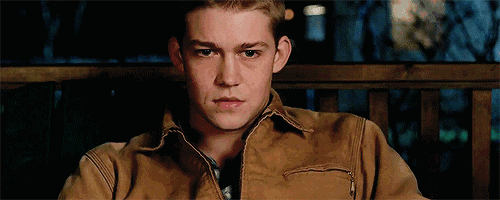
而从另一个角度说,李安在影像上做了一次非常激进的实验,即便令“形式与内容”之间产生了某种兼容故障,也还算无可厚非的话,那么,《中场战事》的“故事本身”还有不足,那就更令人遗憾了。
简而言之,《中场战事》有故事、有情感、打动人,可是最后却令观者难以体会到“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而“表达”,是一个创作者之所以创作的应有之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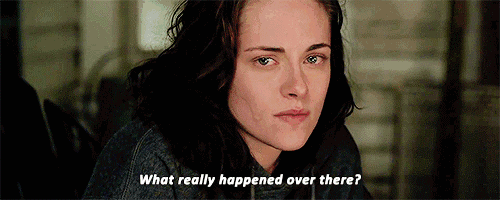
或者这么说,每个角色、每种立场都被有效地展示了,可大体上影片所说的,就止步于“但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的层次了。
然而,这不仅不该让一部回溯伊战的严肃军事题材就此鸣金收兵,也和两获奥斯卡、两获威尼斯金狮、两获柏林金熊的当世大师,蛰伏三年才出手的“所应为”有了距离。

对于“反恐战争”、对于当代美国社会、对于当代美国人,在这些敏感的、而且此前他本人已经在诸如《冰风暴》或《断背山》里有过论断的议题上,李安这一次显得太过避实就虚。
而《中场战事》之所以在美国本土遭到不少评论界的指摘,大概也是由于它让左派和右派都觉得有骑墙、失语之嫌——毕竟9.11、伊拉克、阿富汗以至今天的叙利亚、伊斯兰国串起这段“反恐战争”史,实在是美国国民有切肤之痛、不得不关心的现实困境。
因此,就像比利妈妈吃饭时拍桌子不准讨论政治一样,李安同样不谈国是,真没法让座上的四邻心服口服。

而且,如果说不愿或无法对伊战表态,可能多少是因为李安毕竟是拿绿卡的“局外人”,那么,实则《中场战事》里已经包括了若干个可以深度开掘的其他题目,可也被他一一放弃,就显得太可惜了
——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极度文明的时代,一个杀人者(尽管在战场上)却被顶礼膜拜,实则非常诡异,影片已经略略触及到,却又轻轻揭过了;
又如,B班弟兄性情各异出身不同,但是因为一起出生入死,他们必须而且最终也真的彼此“我爱你”了,那么,这种特殊而奇妙的人际关系本身,就有了值得深入刻画和辨析的空间,而且已经是一些经典军事影片所关注的焦点。
然而《中场休息》着墨太多在比利和他的两位班长的身上,以至于就此问题只能零敲碎打地讨论,甚而只能依靠几段台词来直白地强调;

再如,那些在影片中特意交待了十足十的琳琅满目的食物、白花花的啦啦队员大腿、喧闹盛大光怪陆离的中场秀,都分明可以看出是创作者针对物质至上的美式资本主义或者说美国主义的讥诮,然而却也只在原地打转,不再深入。
甚至,最核心的,原著小说和电影都表示要关注的心理疾病PTSD(军人创伤后应激障碍),该病征到底是怎么回事,又会如何影响在役或退役的军人,《中场休息》也都语焉不详,
最明显的地方,体现在影片中有过三段用单色画面来表现比利的“心理现实”与“真实现实”的分裂(两次在新闻发布会、一次在演奏国歌时),可是这些段落“质量”平平,更何况“数量”还不够,以至于既不能体现作为个体的比利的疑似PTSD症状,也无法象征一批或一代“美国大兵”的心灵状态。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影片没有调整好、起码是没有调配好成分比例——本片究竟是比利·林恩的立场,还是某个旁观者的立场——而且,要命的是,比利的所见、所想、所言还是不统一的,
所以,尽管我们灵魂附体一样,通过比利之眼看到了很多事很多人(尤其是白头大亨的那张自大脸),可是比利的想法和比利的说法,又得换成另外两种视角。
于是到了最后,我们对于比利其人的认知还是迷惘的。
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单纯的19岁得州男孩,还是说他其实有着非常超越其年龄的知识分子型的心智?他究竟是一个行动快过思考的、反射神经发达的“天生的当兵材料”,还是一个信仰存在主义的、擅长谋定而后动的聪明人?

当然,说回来,即便有画质问题、表达问题,《中场休息》依然是一部近年来不多见的出众电影,如果它不是一出“李安作品”,理应获得更多的喝彩。
只不过,李安无论在好莱坞,还是在华语影坛,都已修为到了“国士无双”的境界,大家就必须用更高更严苛的标准去考核他。
因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5、
李安成就空前,确实是为电影而生的天才。

不过,多年来,坊间也有所谓他总是成一部败一部的判词——成本极高却被制片厂放弃发行的《与魔鬼共骑》,至今仍算是美国影史上数得着的一桩公案,而《绿巨人》《制造伍德斯托克》则已经被归为败作(当然,依然是顶级高手级的失手)。
在叫好又叫座的《少年派》之后,似乎《中场战事》又要应验这一“魔咒”了。那么,巧合之中,或许也自有某种难以索解却着实见效的造化在弄人,甚至,我们也不妨说,这和李安骨子里迷恋败者之歌,进而无畏于失败有些关联?
因为,他着实是一个当今影坛不多见的特别爱冒险,特别不愿意重复题材的勇者。

无论如何,就和侯孝贤、王家卫、张艺谋一样,“李安出新电影”,不止是华语电影界的盛事,也算得上国际影坛的大事。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就像《一代宗师》或《聂隐娘》,就算有瑕疵,终归是光彩熠熠、独一无二的存在,必须注目,必须领教。
因为,就算李安败了,也像他的电影里的那些败者一样,令人动容。
 欢迎关注新浪电影官方微信号“玩儿电影”
欢迎关注新浪电影官方微信号“玩儿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