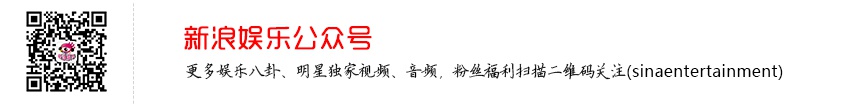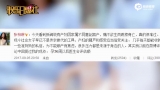坂本龙一
坂本龙一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老去的。
在威尼斯的电影宫里,我们见到了白发的坂本龙一,这是一位三年前曾罹患喉咙癌的音乐家。2016年初,另一位音乐天才大卫·鲍伊因为肝癌而陨落。同住纽约,共处于市中心,坂本龙一相信,“我们可能去过同一家医院”。所幸的是,坂本龙一走出了医院。

两年前,坂本龙一复出为山田洋次执导的导演《如果和母亲一起生活》编曲,接着便为《荒野猎人》、《怒》配乐。而这次,他带着一部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来到了威尼斯电影节。
这部纪录片有坂本龙一各个时期的珍贵画面,包括70年代的演奏现场,80年代在中国长春、大连、北京等地拍摄《末代皇帝》的花絮,《战场上的快乐圣诞》、《遮蔽的天空》的创作心得,以及他前往非洲肯尼亚、北极采风的视像资料,除此之外,坂本龙一还在纪录片中,谈及了罹患喉癌的心路历程,坦露身为艺术家的自己关心环境、政治、社会议题的原因。
在中国,坂本龙一被乐迷称作“教授”,听到这样的称呼,他主动与我来了一个温暖的握手,并说出了相当标准的“你好”、“谢谢”。
对于很多乐迷而言,崇拜和喜爱坂本龙一并不仅仅是因为音乐,还有生活方式以及个人思想,关于这些,《坂本龙一:终曲》可以给人很全面的答案。除此之外,不可忽视的是,坂本龙一那始终如一的绅士态度和优雅气质。
“如何优雅地老去?”我问他。“教授”有点害羞地说“我也想知道”,随后,他想了想,“努力去丰富自己,多读书,看好的电影,以及感受自然。”

“从没有想过会有癌症,这始终像是一个玩笑”
从二十多岁开始工作,坂本龙一就没有停歇过,直到被确诊喉癌,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被透支,“从没有想过会有癌症,这始终像是一个玩笑”,坂本龙一在纪录片里难以置信地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坂本龙一开始生活在美国纽约。在针对癌症的一年治疗期结束后,城中的另一位音乐天才大卫·鲍伊却因癌症而与世长辞。尽管在《战场上的快乐圣诞》中有所合作,但坂本龙一说,两人很少联络,“尽管我们住在同一座城市,都住在市中心,但我们从未碰到过彼此。”
坂本龙一提及了大卫·鲍伊的《Lazarus》,然后是他并不那么喜欢的专辑《The next day》,“最后那张《Blackstar》我真的很喜欢,但是突然间,两天之后,他就去世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一个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死去的人,他想有更多的时间去创作新的音乐,在同时,我也有同样的病,我相信,我们去过同一家医院。”
实际上,坂本龙一在确诊的时候,正在做新的专辑,最初他也抱持着与大卫·鲍伊类似的心情:“不知道自己还剩多少天,不把任何事情看做理所应当,只想留更多的音乐在世上”,“如果可以,我却没有努力去‘挥霍’生命,那是很惭愧的”,如此,他坚持了一阵子。但最后,他还是不得不全面停工。
一年的治疗期过后,坂本龙一感觉自己好了很多。癌症的经历,让他开始更倾向于多做自己的音乐,不只是看着那些电影画面、听导演的想法、从外界角度来创作,而是“表达自己内在的声音。”
“你还有多少次看满月升起的机会? 也许4、5次。也许更少。”得了癌症后,保罗·鲍尔斯写的《情陷撒哈拉》里的这一句,牢牢地刻在了坂本龙一的脑海里。

“是与否,这条路与那条路,都是纯粹的,我的特质。”
纪录片里,有一个雨天,坂本龙一打开花园的小门,把蓝色的水桶盖在头上,以这种独特的介质倾听雨声。
2008年,坂本龙一应老友的邀请,前往了北极,在白雪茫茫的世界里,坂本龙一对着镜头说:“我觉得随时会死去。”在一方硕大的冰山脚下,坂本龙一拿出撞击乐器,在一洞小小的水流里,坂本龙一探入收音器,开心地说,“我这是在‘钓’声音啊”。
“工业革命以后,自然被打造成有形的物体,人们通过它们去听大自然的声音。”坂本龙一说,但他却更迷恋大自然原本的声音。
在此之前,坂本龙一的编曲经历了不同的时期。

电影《战场上的快乐圣诞》是他为电影配乐的开端,动力来源于导演大岛渚的鼓励。谈及大岛渚,坂本龙一忆起第一次见他的场景,“那是东京市中心的一条街道上,在与武装警察对峙的游行人群中,大岛渚站在第一排,太激进了,他那时大概是在40多岁。”
第二次见面,是大岛渚造访坂本龙一的工作室,两人要聊《战场上的快乐圣诞》的电影剧本。坂本龙一回忆,当时他正望着窗外,大岛渚就出现了。

“写出《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时候,我很年轻,那个声音几乎完全是由合成器、电脑或者类似的技术制成的,那时候它们是很少见的,后来我就开始使用常规的乐团,比较少用合成器。近些年,我常常会想,可能在《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之后,我应该多用合成器的,也许我本可以成为一个比现在更独特的编曲者。”
“不过如果我只用合成器作曲,可能导演就会用别人作曲,而不用我了。”坂本龙一笑着说。

在这之后,就是1986年的《末代皇帝》,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是想让他去演戏的。当时,坂本龙一在大连演了两天,之后又去长春电影制片厂。纪录片里,坂本龙一在剧组人员的围绕下现场演奏,贝托鲁奇兴奋地对着镜头说:“这是大师之路的开始。”
完成拍摄后,坂本龙一去了纽约,贝托鲁奇一个电话把他叫到伦敦,一周创作了45首歌,“压力很大的,但现在看起来好像做得不错”。
《坂本龙一:终曲》里没有谈及阿莫多瓦,这是纪录片导演的取舍。在坂本龙一看来,阿莫多瓦是一位非常温和且有创造力的导演,“大多数情况下,几乎所有的导演都非常像独裁者、指挥家,命令和要求人们,但他不是的。”
“其实他很想我尽快地观察西班牙的一切,但是我想我到现在都没有真的观察到,那是我很后悔的地方,我应该花更多时间去更深地理解西班牙的,但是我却没有,因为真正地、深入地、独特地去理解西班牙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它是复杂的、历史性的、具有文化复杂性的,涉及的因素和要素是非常多的,是很长的历史,太难了。”
没有唱片公司的干扰,按照自己的节奏发专辑,既可以通俗又可以做自然音乐或硬核电音,坂本龙一是风格多变的自由音乐家。他坦承对所有的作品都喜爱,但也有偏好,比如说,对比《音乐图鉴》和《未来派野郎》,他会更喜欢前者,“后者好像更像一种流行趋势,不像前者那么无时代性。”

“是与否,这条路与那条路,不管我放了多少元素,自然的声音或是机器的声音,都是纯粹的,我的特质。”
“音乐是需要和平的”
坂本龙一十五六岁的时候,巴黎、纽约、芝加哥以及日本的学生运动正在兴起,那时候读高中的他,变得非常激进,戈达尔成为他当时的偶像。在戈达尔之后,坂本龙一开始看特吕弗和费里尼,然后是贝托鲁奇和大岛渚。
“我是从1992年开始思考环境问题的。”坂本龙一说,“艺术家对自然环境、人类社会的变化是最为敏感的。此后,这种意识开始影响我的音乐。”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坂本龙一定居纽约。“因为多样性。我是一个黑人,我是个穆斯林,我是个LGBT人群,这就是纽约。”
2001年9月11日的早上,两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客机,分别撞击纽约的地标性建筑双子塔(纽约世界贸易中心),迸发出巨大声响,坂本龙一望向窗外,震惊之中,拿出相机,拍下了撞击发生之后的场景。照片中,高楼残体的侧面,有惊鸟飞过,这种对比深深震撼了他。“911事件”发生后,他一直没有在纽约听到音乐,直到事件过去一周,他才在时代广场听到有人唱《Yesterday》。
“音乐是需要和平的。”坂本龙一说。
“为什么我们的世界这么暴力?这让我忍不住想去探寻生命的起源。”于是,坂本龙一在2002年2月去了非洲的肯尼亚,在人们居住的河边,他产生了“只有爱能够战胜恨”的念头。2008年,他又去了北极,体会到了“随时会死”的渺小。2011年,他前往地震核泄漏的福岛探访,还在灾区,为人们演奏了那首名曲《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

如今,坂本龙一还是会和日本的家人相聚一两次,但生活和工作仍然是在纽约,“我仍在关心日本的状况,不管是环境上的,还是政治、社会议题上的,因为与在美国发生的非常相似,右翼正在上升,日本五年了,在美国只是几个月而已。”
谈及中国,坂本龙一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意识到,中国在日本历史上的影响力很大,政治、制度、人口、建筑、食物,几乎一切都是中国带来的,所以我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很大的尊重。”
《坂本龙一:终曲》的最后一个镜头,是他弹奏钢琴的画面,坂本龙一笑着说:“我每天都练琴,确保手指能够保持练习状态。”
“如何优雅地老去”,成为了此次采访的最后一个问题,坂本龙一说,他也想知道答案,也许“努力去丰富自己,多读书,多看好的电影,多感受自然”是有所裨益的。说完,“教授”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握手,我想,答案就在这份传递之中吧。(阿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