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小平/文
“贾宝玉的形象是我创造的,(其他的)都是模仿。”
说这句话的徐玉兰,4月19日在上海华东医院以96岁高龄去世,弟子钱惠丽仔仔细细给她化了此生最后一个妆,于是她躺在那里,平静而余势未尽。走廊里站满了弟子、同行、领导。更外面站着的,是医院不能放进来的大队戏迷。含泪苦等着,只想遗体离开时,能近前说声“侬走好”,就像徐玉兰在世时,戏迷排着轮子,以能去她家里做家务为荣。
徐玉兰在1957年创造了越剧贾宝玉的形象,《红楼梦》成书两百多年,她之前,演过贾宝玉的不知多少,谁成功了?还真没有。梅兰芳的搭档姜妙香有“姜圣人”之称,登台演宝玉自己都尴尬。她之后,有林青霞[微博]、欧阳奋强[微博]等等,从形象到支撑角色的信念感,都多靠她,连李翰祥拍邵氏电影,也把越剧的唱词、调度、制景从头到尾模仿了个够。
徐玉兰这句话,说得字字不虚,如真金,掷地有声。
我亦尚未遇到不会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中国人。
但这句话放回到徐玉兰的人生中,又变得太普通,一代宗师,要给她“划重点”,哪里说起。
 《红楼梦》徐玉兰饰贾宝玉(1958年)
《红楼梦》徐玉兰饰贾宝玉(1958年)part1 这点苦头吃勿消,还要啥漂亮?
不知从哪里说起,于是她去世那晚,我竟说起了她穿过的那些好看衣服,拍过的那些好看照片。
徐玉兰的扮相本不算顶好,台上画眼睛、勒眉毛还差不到哪去,卸了妆,她圆脸、圆鼻头、还有点不严重的斗鸡眼。可是她拍出来照片,气度魅力,全好极了,是“那个年代”女明星特有的“派儿”——有距离感,明明和气地笑着,也光芒逼人。上世纪60年代,《红楼梦》作为外交力量要去香港演出,政府严阵以待,剧组被“关”在广州半个月,做洋装、裁旗袍、踩高跟鞋、学应酬,金采凤、吕瑞娟学得很认真,徐玉兰开玩笑:“旧社会那一套嘛,我都会。”她是真“会”,一个个运动、劫难熬过来后,她又开始按她的心意,爽气地换房子、穿花色衣服、穿高跟鞋,人生最后的年夜饭,也是请医生从指定馆子订了,送进病房。
她台上唱小生,台下爱漂亮,照片里珠宝、貂狐、绫罗绸缎、刺绣光片样样上身,高腰身、廓形大衣、玛丽珍鞋穿了个遍。她对高跟鞋是真爱,九十岁过了,还向再传弟子、工作人员、记者许多年轻女孩说:“年轻穿啥平底鞋,么样子!穿高跟鞋才登样,小姑娘这点苦头吃勿消,还要啥漂亮?”
“漂亮”是要吃苦的,1959年国庆十周年,《红楼梦》进京献礼,怀孕的徐玉兰肚子已经大起来了,但她为了舞台形象,用厚腰带勒勒紧,咬牙演了好些场,结果孩子生下来鸡胸,都说是勒坏了。
此事徐玉兰并不讳言,我第一次听说这故事,就是她亲口讲的,听众有一百多号人。2006年越剧诞生一百周年,央视老早就开始做各种节目,《艺术人生》请到了徐玉兰、王文娟两位老艺术家录节目,节目组为方便管理,按例从学校组织观众,我念大二,正热爱着京剧老唱片里那种“破烂声音”,对“漂亮”的越剧一无所知,但两个要好的女同学是越剧迷,兴奋至极,硬要我作陪。节目录到11点多还不完,正值冬天,棚里实在太暖和,徐玉兰的“上海普通话”实在太难懂,我在观众席里昏昏欲睡,左倒右仰,同学一左一右,我倒一下,她们就暗中戳我一下,我简直想溜回校车里躲着睡觉。而两位老艺术家在台上被大灯烤着,却越来越精神,习惯拨弄嘉宾的主持人,在她们面前沦为配角,徐玉兰讲勒腹登台的故事时,双颊红润,双目有光,节奏控制得当,一如演出,她问观众“狠心伐?”没得到回答,所有人都沉浸在敬仰和感动中了,包括暗中瞌睡的我,还包括灯光下的她自己,都被讲述中的那股气势压倒。讲了许多遍的故事,仍被当事人的光彩照耀得非常纯粹,不打折扣。何况,此前我们还知道了她为能“漂亮”,生了许多病,受了许多气,睡过稻草,趟过泥地,吃的苦不要说夜里11点,就是再说几晚上,都说不完,而观众们是真心想听她说啊,是真心怜爱她又佩服她。
而我之所以没溜走,留在现场听到这个故事,是因为被之前的另一个故事吸引了。
 《红楼梦》徐玉兰饰贾宝玉, 王文娟饰林黛玉(1958年)
《红楼梦》徐玉兰饰贾宝玉, 王文娟饰林黛玉(1958年)part2 “男阿飞”出来了!
还是那夜录制大厅里,徐玉兰说,她和王文娟(越剧王派创始人,林黛玉饰演者)第一次看到电影版《红楼梦》,竟然是在批斗会上。电影拍完,还没等到上海放映,《红楼梦》就成了大毒草,徐玉兰、王文娟文斗、武斗尝遍。徐玉兰学过武戏,不要以为越剧演员的武戏都是花架子,跑码头的南方武戏最要功夫,她能从三张半高的桌子上翻下,但到了这时候,也只有挨打的份。
真是荒唐年代,某天,审问者狠道:“你在旧社会跟多少人困(睡)过?”需要回答吗?只需要徐玉兰委屈、发怒,就可以令观者吃吃偷笑,那份期待,可能就像当时坐在大厅里,等着为徐玉兰慨叹的我们。徐玉兰决定不去满足这种猥琐的期待,她回击了:“旧社会不当婊子就不能活到新社会了?!”
有一天,造反派押徐玉兰、王文娟到银幕底下,原来是要边放《红楼梦》边批斗,林黛玉先进贾府了,全场大叫:女阿飞(流氓)!林妹妹见完贾母凤姐和姊妹们,宝玉回来了,又是一阵大叫:男阿飞出来了!
结果批斗大会草草收场,因为大喊大叫的造反派们看着看着竟流出了眼泪,头目觉得形势不对,不许电影再放下去。
徐玉兰说自己又好气又好笑,苦水全往肚子里咽。这个“宝黛初会”,光一个上场,她想了整整好几个月才有雏形——有文化的贵族子弟,又是大富大贵的公子哥,年龄才13、4岁,让他怎么上场?用书生的形象?演成翩翩公子?小孩子蹦蹦跳跳的脚步?大摇大摆的少爷?都不对。徐玉兰从原著里几次提到手串展开联想,让宝玉摇着手串上场,导演拍案叫好,中国人对贾宝玉从此有了共同的形象认识。
初接宝玉这个角色,当时上海的文化局长徐平羽说,要演贾宝玉,至少要通读10遍《红楼梦》。徐玉兰一听要“晕过去”,但她不仅读完了,还给人物关系分组,和父亲、母亲怎样,跟老祖宗在一起什么状态,与宝钗在一起的变化,与晴雯、袭人她们在一起又怎样,和黛玉的关系最复杂,徐玉兰又细致划分了数个阶段,和编剧多次沟通,做了详细笔记。下了这样的功夫,徐玉兰的宝玉真成为一块不世出之宝,幸好有电影传世。
这部电影是在香港孕育的。前文提到他们赴港演出,夜夜爆满,许多观众场场连看,票子越看越贵,18块的票子被黄牛炒到300块,仍供不应求。著名影人朱石麟就是她们的忠实观众,朱是江苏人,上海出道做编剧、导演,抗战结束后赴港,是香港电影拓荒者之一,在业界颇有影响力。朱石麟越看越欢喜,要剧组留下来,长城公司将会给他们拍电影。长城公司有著名的三公主夏梦、石慧、陈思思,团队以内地影人为主,态度非常积极。上海市委领导认为长城思想左倾,可以合作,但电影一拍几个月,那么多女演员在港,万一滞留、潜逃几个,酿成政治实践哪能办?但拍电影总归是好事,最终谈妥回上海拍,回来后用了海燕厂四个新棚,所有的设备都是全新的。从成片来看,搭景布光水平很高,“宝玉出走”那开阔的远景,也是绘景师傅的手笔,而近涧远湖都是用的自来水。德国进口胶卷由长城公司从香港运来,导演岑范也是“港归”,当时好几个名导演争取拍《红楼梦》的机会,朱石麟自己没回来,让自己的学生岑范掌了镜。
电影拍出来,简直成为外交利器,当然也给国家赚了可观外汇,而上海全面放映《红楼梦》已经是文革结束,1976年36家电影院同时放映,市民半夜1点排队买票,散场后从放映厅里扫出来一堆堆被踩掉的鞋。徐玉兰已成惊弓之鸟,很长时间里都认定,放映是因为又要批判她了。
 1944年9月,徐玉兰、傅全香在美华大戏院演出《黄金与美人》
1944年9月,徐玉兰、傅全香在美华大戏院演出《黄金与美人》part3 黄金与美人
徐玉兰有一个早期作品叫《黄金与美人》,观众都很喜欢这名字,我也喜欢,对于当年的越剧名角,有一种很贴切的隐喻。
这部作品对徐玉兰非常重要。越剧最早的演出形式是“幕表戏”,又叫“提纲戏”“路头戏”,是跑码头班社的一种智慧——人员流动性大,演出条件差,只能在后台贴出剧目大概内容,让演员根据师承传授,自我发挥。徐玉兰当时在宁波搭档“女子越剧第一人”施银花,对方有名有实力,常有意无意地更改唱词,掼过来什么韵脚,徐玉兰必须要接牢,绝不能在台上无以应对。她找准机会说服老板,从上海请编导写了第一个属于她的剧本《黄金与美人》。先挂出上本,演完被戏迷追得太紧,打出广告回应:“积极日夜赶排,一步紧逼一步”。演出海报上,徐玉兰三个字和剧院名字并肩同大,被誉为“标准小生”。这家剧院叫“天然舞台”,座位数是宁波其他剧院的三倍,日夜满座。
天然舞台的老板有位内侄俞则人,沉默寡言,是个教书先生,当红的徐玉兰默默地和他产生了恋情,但俞则人温和内向,一直不敢和大明星订下婚约,他知难而退时,徐玉兰主动写了封信:“幸得相识,不胜欣喜。俞先生的人品、学问都令我欣慕。如蒙不弃,我愿做俞先生的终生伴侣。徐玉兰。”信寄到了,人还是走了,甚至都没向徐玉兰辞行。徐玉兰不泄气,千方百计打听到俞则人搬去城外舅舅家,又冲破重重阻力,找到俞则人,终于订下终身。因为徐玉兰常年演出,两人甚至一年都见不了几次面,到1954年,俞则人从上海财经学院毕业,两人才完婚,恋爱整整谈了12年。并不太长的相伴后,俞则人于70年代自杀,徐玉兰一直没有再嫁。
把徐玉兰带到宁波的施银花是“三花一娟”之魁,“三花一娟”是实际意义上的越剧四大名旦,随后崛起的就是“十姐妹”。这十位女性艺术家奠定了越剧的全盘格局,关系很微妙,是携手前行的姐妹,又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徐玉兰晚年很高兴提到自己把某某某唱赢了,又把某某某唱塌台了,她所提到的对象,都是“十姐妹”里人物。到80年代,她们都已是开枝散叶的宗师了,仍处在你化用了苏州评弹,我马上就借鉴京韵大鼓的竞争里。而这种竞争,某种意义上,是对艺术至善的纯粹追求,这也是越剧在80年代还能不断出新的一大原因。
 徐玉兰《是我错》唱段
徐玉兰《是我错》唱段part4 合一个心肝合一付肠
我曾经完全不懂越剧的好处,比如越剧贾宝玉出走是因为“人间难栽连理枝,世外去结并蒂莲”,简直让我叹气,连高鹗续书中的赤脚一拜都比不上。还有那支[枉凝眉],越剧里是这样唱的:“若说今生没奇缘,为什么合一个心肝合一付肠”,镜花水月怎么变成了心肝肺肚?真是到了许久之后,懂点事了,才被编剧徐进和徐玉兰、王文娟们的高明所震动,他们是真懂自己的观众,也处处照顾着自己的观众,把每部戏都唱成一篇甜蜜的女性童话。
越剧发源于浙上世纪初从浙江嵊州进入上海,恰赶上女性被允许进入戏院,每一代越剧演员都牢牢吸引着城市女观众这个群体。徐玉兰很自豪自己的戏迷除了太太、小姐、女工人,还有不少知识女性,不过这正说明越剧的主要观众是由前者构成的。
徐玉兰1945年排演的《是我错》被视为徐派艺术诞生的里程碑。这是一部家庭喜剧,丈夫嫌弃妻子贫寒,导致妻子不堪婆母凌辱,跳河自尽未遂,却意外得到了财富、地位,丈夫重新“爱”上妻子。于是高烧红烛,作小服低,百般讨好,而受尽委屈的贤德娇妻自然端起架子,百般作势。而之所以此剧能萌发了徐派唱腔,多少是因为男主角对着妻子懊悔、服软,把“是我错,你不错”唱了一遍又一遍,徐玉兰必须对旋律进行调剂。尽管[四工调]的传统风味仍十分浓厚,但大跨度的音程,丰富的甩腔、拖腔,都已经具有了后来徐派的主要特征。
唱段结束在“千错万错是我错”的一跪中,夫妻和好。虽然道歉毫无诚意,丝毫不触及核心问题,丈夫深刻检讨的都是些皮毛淡话,如“倒来香茶我不喝……眼睛白侬眼睛错”之类,而妻子已喜滋滋靠在丈夫臂弯,准备同入罗帐,台下的女性观众们也唇绽笑、面含春,达到观赏高潮。想叹气吗?这个戏目前还在唱,观众仍然很喜欢,越剧和它的观众就是这样一种互相纵容的甜蜜关系。
 《追鱼》徐玉兰饰张珍 ,王文娟饰鲤鱼(1956年)
《追鱼》徐玉兰饰张珍 ,王文娟饰鲤鱼(1956年)part5 欢快刚强、充满激情的徐派
徐玉兰后来排演的人物越来越刚强,高亢有力的唱腔有了越来越合适的承载者。同是传统戏,较晚录制的《盘夫》就更适合她。出场第一个唱段的第一句“奸臣贼子满金殿”,徐派特有,开门见山,出奇制胜。“冤仇报”三字来了个有力的大跳,除了旋律已富有浓郁的徐派特征和韵味,6句唱段“宽—紧—宽—落”的结构,也成为徐派常用形式。至后期的《北地王》、《春香传》、《关汉卿》等,则欢快刚强、充满激情的徐派风貌更臻完整灿烂。
也有用得不那么适宜的。
比如《梁祝-回十八》,旋律、节奏、过门,皆有出新,尤其清板段落,用轻重缓急的变化模仿两人,惟妙惟肖,生动异常,但就是这份灵活奔放,让人觉得这个梁兄这么聪明活跃,凭什么说他“呆头鹅”。还有反映阶级矛盾的新编戏《亮眼哥》,徐玉兰吸取了绍剧的某些音调,希望达到富有泥土气息的效果,但她的音色仍然是华丽的,一点都不像民工。
巅峰之作《红楼梦-哭灵》,也揉入绍剧音调,但因为角色适合,就稳稳妥妥成为经典。 “哭灵”似惊涛拍岸,是很长的一大段唱,把观众情绪推向顶点,接下来的任何唱腔,如果处理不当,势必成画蛇添足之累,但徐玉兰紧跟着一段“问紫鹃”毫不逊色,甚至更为动人。此处的常规做法是唱几句散的、快的,但徐玉兰别出心裁,全部设计为抒情性唱腔,避免了旋律的平铺直叙,音乐过门也比“哭灵”更加精心,弃用了落音加花延续的传统框架,采用更优美的旋律,带来了深邃的意境。另外,通过紫鹃的“四答”,产生戏剧效果,不仅动听,感染力也大大增强。据说周恩来最喜欢这段,每逢见面总要请她唱。
类似的神来之笔还出现在“只求与妹妹共死生”一段中,这是宝玉发现“调包计“后的哭诉,先在高昂的快节奏里,连用两个下句唱腔造成失去常态的不稳定感,末尾竟然是一句舒展、自由、理想化的清唱,这突然的变化、强烈的对比,着实令人难忘。
徐玉兰众多代表作中,我个人最偏爱《追鱼》“说什么姻缘本是前生定”一段。这是徐玉兰从朝鲜归来后的作品,此时她艺术能力、政治地位都稳定成熟,这种状态自然会在作品风貌中有所体现。这一段是贫寒书生张珍的自白,只有12句,却包含了[尺调腔]七字句慢中板、十字句中板、起腔和[弦下腔]缓中板四个层次,并重置了七字句结构,又大手笔地将多姿的旋律,新颖的变化放入稳定自然的节奏中,初听无奇,咂摸不尽,真是达到了很高的美学境界。
徐玉兰的这些录音,真令人赞叹,明明白白勾勒出她如此天才,如此奋进。越剧诞生的晚,留下音像资料的宗师很多。这对于含泪相送的人而言,是幸福的,一段段录音就是她们的“羊公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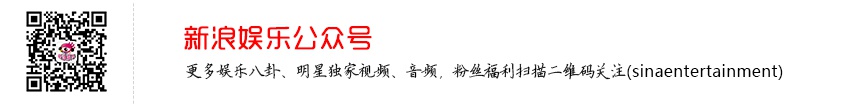































































































 网友偶遇黄晓明baby
网友偶遇黄晓明baby 伊能静儿子正面照曝光
伊能静儿子正面照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