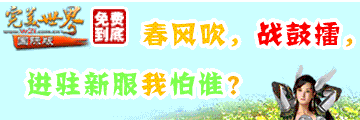|
|
|
|
|
苏阳:来自身体的歌唱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06日18:00 新浪音乐
 苏阳 他曾经和生活在这里人们一样,只生活,不思考。只是因为蒙昧的冲动以及过剩的荷尔蒙,偶然选择了音乐,并摇滚了10年。而这10年更像是某种孕育或者潜藏,真正的种子并没有发芽。也仅仅因为他偶然回到了泥土中,那潜藏已久的种子才开始发芽、生长,那长出的枝叶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 因为一切都来自泥土,那无边无界的土地仍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得多,那其中的歌唱更是如此,将直视我们的现实,像平常那样的自然、安静,不带有任何的焦虑。这个声音,我们等了10年之久,它来自——苏阳。 1.苏阳什么时候开始从事音乐的?最初的想法是什么呢? 答:最初的想法是很简单的,因为一开始在西安,接触了吉他,胡里糊涂地,就开始了瞎玩。那时,应该不叫从事吧。后来被工厂开除后,我再回到了西安,那应该叫从事音乐了吧,就是走穴。那时,全中国都是这样的啊。后来,接触摇滚乐,萌生了很多想法,但是后来都没有实践和完成。直到后来,碰到了文征等人,才开始组乐队,写歌,后来,就这样的。 2.你怎么看你以前的“重金属”摇滚? 答: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部分乐手都是我这样的,痴迷于包括重金属那样的摇滚乐,其实当时我一直狂热喜欢的还有“恐怖海峡”那样的音乐类型,但是可能是重金属更容易模仿,大家都玩这个,没有什么的,只是熟悉摇滚乐的一个形式吧。其实在后来和安彪和老蔡合作的时候,我们尝试过用秦腔的元素融合的,比如有首歌叫《山》,挺不好听的。 3.摇滚了10年之后,你怎么会突然从一个摇滚吉他手变成了一个民间歌手? 答:其实一切都不会是突然的吧。10年摇滚,也不会说就是一直不变地,都在变化中,我后来越来越觉得这样模仿一堆东西,而且身边大部分人也都在这样模仿,很无聊了,我们具备这样的生活吗?这是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思考吧,变化,并且考虑生活和琴,和歌唱的关系,那么,民歌自然会出现在这些影子里。其实,摇滚乐在国外也属于民间吧。 4.如果是生活的话,那么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或者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才使你有了现在的想法? 答:生活,并没有翻天覆地地变化,而是对音乐和生活的看法发生改变,我们的歌唱是为了什么?为了快乐?谁的快乐?作为我的?还是一个摇滚乐手的?还是作为一个人,一个中国小城镇的人的?变化,随之而来。 5.什么原因使你选择了西北的“花儿”?你小时候接触过这些东西吗? 答:其实是2002年准备了一些,后来我还向李伟要了些非洲音乐的田野录音,在2003年我在一次音乐会上用箱琴唱了《宁夏川》。我开始把拨片放在琴的后面,融合中国很多类似三弦的声音。后来我去了海原,宁夏真的是个很不统一的地方,相对银川的逐渐热闹,那里是贫瘠和平静,让我想起来我小时侯隔壁小刚他爸的唱经声,但是,花儿显然和这些不一样,那是自由的歌唱方式,即兴,基本还是在一定的格式里即兴,所以我不相信现在在都市里会有人唱花儿,花儿不是你跟着音乐资料学几段完整的歌。它是一种能力,一种用各种“令”完成的中国即兴,很多中国民间音乐都是这样的,终归我们完成的仅仅是歌曲。应该不能说花儿,我到现在还是否认“花儿”对我的影响有多么重大,从音乐的根本来说,我不会唱“花儿”,只能说我在学习当中,我听的很杂,贤孝啊秦腔啊什么的,但是,我可以用这些民间的属于我们的语言习惯来构成音乐,包括学习它的过程。 6.有没有这种可能,你来自宁夏,一个对大多数人陌生的地方,所以很多听众就会想当然认为你会带来宁夏的什么地域性,所以你选择了花儿? 答: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不应该考虑这个可能,我们用顺手的语言,说些身边的变化,这符合自己的身体,还有一些借鉴,传统民歌的旋律,但是我不会提供所谓的新鲜乡土菜,来博得市场或者什么民歌的名分,我也不是给自己弄一身行头来装成一个所谓的民族歌手,我认为谁表述生活更贴近,谁就可以有更多的爱好者人群自然可以靠近。 7.你怎么看中国传统的音乐或者说民间音乐? 答:我曾经在农村,尝试去听他们歌唱,后来,我觉得,为什么,在我们的思维概念里,民歌就是在农村呢?可是,农村的生活已经结束了啊!我们那里有很多居民都曾经是农民,但是,房产商或者什么的征收了他们的地,给他们房子,每天他们就是在打麻将、谝闲传,越来越多的农民拥向都市,拿起瓦刀,建设高楼大厦。还有,穿得复古衣服长袍大袖的古筝和古琴演奏者?这些就是传统吗?是琴和筝吗?胡琴?胡字的意思就是洋人传入的考证啊!那么,我们的传统呢?黑人用吉他,而不是用部落里的不被人所知的乐器,让Bules传遍世界,我们有吗?我们会在听完一段音乐后说,这很地道,或者说,这是啥吗!就是说我们用了我们自己的音乐习惯。说的更直接点就是要倒过来,很多人用民族乐器完成西方音乐,比如音乐学院的用小提琴教程教出的二胡,比如交响化的民乐队,而我,用西方的世界化乐器说咱们自己的事,用吉他,说银川,宁夏,中国的西北的一些东西,让吉他这样的乐器具备中国人的气质,从我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身体发出,对我来说,这或许是个问题。 8.这些音乐与摇滚有什么不同? 答:我想有着不同,就是说他不应该用简单的摇滚乐来分类,确切地说,这些音乐还在变化中,在路上,而且远没有到被定性的必要,只能说明一种态度,但是,我还是喜欢让旋律真正地发生作用,总之是个态度吧。 9. 你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音乐只是为了诉说身边的事,西方人有西方人的方式,而你有你的方式,你的音乐中要有中国人血液中的“汗味”,你怎么完成这个呢? 答:其实,我可能是在某个别的时间说了这个,音乐,不应该被局限于某一诉说,建立方式,也要加以时日,并且正在进行中。我所说的汗味,可能指热血,指身体。摇滚乐是西方人的汗味,他们的身体,我们应该有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发出声音的方式,这绝非狂妄,而是喜好,或者我们应该有的自然。 10.当你决定转向民间音乐的时候,第一次的演出是在哪里?当时人们有什么反应? 答:2002年完成了《宁夏川》的改编,基本还是在民歌改编的基础上来干的,就是模仿传统民歌的语言和格式,后来我还向李伟要了些非洲音乐的田野录音,在2003年我在一次音乐会上用箱琴唱了宁夏川,当时人们并没有注意我的改变,后来,就有《贤良》和《劳动》和《爱情》这样大篇幅自己编的歌,可能是2004年在“土的声音”的小型演出,在那个(银川)富宁街的小戏社里,专场,那次还是很让我难忘,很多人,在街上听,音箱很大声,但是安静的演出,后来的照片上有好几个人在贴着窗户细心听。当时是20块钱一张票,他们为了省钱,不买,就在外面听,直到结束。警察来了两次,并没有严厉制止,听完了走的。那天晚上的声音,我开始隐约感觉到了一种途径,一种交流的途径。 11.你参加的第一次大型演出应该是贺兰山摇滚节,那次人比较多,你有什么感觉? 答:那次被更多的人听到,也被更多人认识到我们乐队。感觉很高兴,这么多人听,而且大部分人说挺好听的。我们还得到了一个“土根摇滚”的分析归类,这前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2.贺兰山摇滚节后,你先后参加了北京几次民谣节演出,当时北京的独立音乐圈和普通听众对你音乐的反应又是怎样的? 答;在北京的演出,现场观众还是很喜欢听的,我不太熟悉独立音乐圈这个概念,反正朋友们都在鼓励,而且我们越来越演的和观众近了,不排除是风格的或者是特色起到了作用,但是,我想更多的人是在鼓励我们对音乐的态度,我们的现场力求直接。 13.从这些演出中,你获得了什么?对你的音乐有影响吗? 答:其实能慢慢获得一种歌唱的能力,可能比别的更重要,我希望我是进步的,对音乐的影响,可能是有些改变,包括新的乐队伙伴,以前银川的伙伴,后来的陆勋,伢子,程鑫,再后来的王斌,每一个新的伙伴,都会让音乐有一点改变。 14.在很多城市中有些平民,在下班的时候,在街上总去听秦腔之类的,这和你提倡的音乐的民间性有什么关系?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会到街上演出吗? 答:其实我觉得是自发性的结果,如果你让他们参加一个活动,一个规定好的东西,他们未必愿意,但是这样自己找乐子,就不一样了。任何东西,符合我们的生活的东西,就会存在得长久,变成我们的精神粮食,时间长了,就进入到人群的血液里,就是传统。我觉得民间音乐不是谁能够拯救得了的,一种没有自发的艺术,一定没有生命力,那就死得理所应当。在(银川)富宁街的演出,其实就是尝试这样的干法。后来我们去了盐池县,就是大街上,谁也不知道我们是谁,但是他们听到了歌声,而且他们听得很认真,他们喜欢,有机会我会做更多这样的事情。 15.在媒体鼓吹“原生态”的时候,实际上,原有的民间音乐生态已经被破坏,民歌或者民间音乐已经被破坏了,失传或者逐渐萎缩,你怎么看目前的民间音乐? 答:其实你的问题就是你的答案,没有必要再回答了。我会付上我的文字来和你一起说这个事情。 16.你现在喜欢听什么音乐? 答:我总是被你们懂分类的朋友嘲笑,比如那天我说我听一个Fusion乐队——KingCrimson,他们都在笑话我,说这个应该被分类在什么什么里面,我也闹不懂,只是跟着听觉吧,最近是些录音片段,还有以前搜集来的民间音乐。 17.现在说说你的音乐,我是从《土的声音》、《只有一个宁夏》比较多地听到你的新作品,我发现,大多是改编作品,而且我个人发现几个问题,器乐部分和人声有些脱节,民歌过去几乎是没有器乐伴奏的,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答:首先,可能并非所有的民歌都是没有伴奏的,你可能说的是“花儿”,其实民歌的魅力,不在于有没有伴奏,而是他们在歌唱时的力量,他们和生活的关系,和身体的关系。“土的声音”的现场让我们激动了半天,靠近了人群,用歌声,但是后来听录音,简直很糟糕,不是脱节,是跑调,所以后来我开始考虑音律问题,就是我们手里的用校音表对准的12平均率的琴,和我们按照调调分配的旋律,不配套,这个问题在后来的不断演出中得到改善。 18.另外,我认为你的唱腔或者说在整体的创作中还保留了大量的摇滚印记或者说思维方式,更像是位摇滚歌手在唱,是不是因为这样,你才选择了银川方言,来改变过去的习惯? 答:我们说的打破摇滚乐,但是并不是意味着躲避摇滚乐,可以用的,就拿来用,干吗不呢?只要能好掌握一点,还有,语言。其实我的歌唱里不仅仅是银川,还有很多是受青海或者陕西的语系影响,只是顺着这些西北的方言习惯来编制旋律,我并不是在强调某一个家乡地域性,而是强调我们这些人的生长,来自的地方。 19.还有,在北京的一次民谣演出中,你说你们是唯一“带电”演出的乐队,而其他民谣歌手或者乐队都是采用原声乐器,你对民谣电声怎么看?民谣是不是原声才够朴素? 答:很简单,我会弹吉他,不会弹三弦,那我就用吉他,我也习惯了用鼓啊贝司啊什么的。原声是会有形式上的配套,我自己弹的是箱琴。民谣电声我觉得也要看自己适合掌握什么样的声音,箱琴是相对来说好掌握一些,更符合人体的感觉,电琴也可以弹得很民间啊,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你抱个箱琴,不唱你的声音,非要唱那些和你没关系的声音,还不是民谣吧?民谣,其实是外国人的说法,中国人就说民歌,平凡的声音。真正的朴素不是你建立一种民谣风格,而是要学会真诚,我们都要不断地学习。 20.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如果在完成了最初的改编之后,你如何继续你的创造力?你会写一些新的“民歌”吗?或者还是继续改编? 答:其实我有段时间在改编和原创之间徘徊,后来我觉得没必要考虑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好听的歌,还有我需要了解更多的民间音乐,还有学习新的民歌,即将以更快的、更轻松的方式出现,那样多好!其实,往往是有几句传统民歌的调子,后面自己词曲,别的,你就是让我唱那些原来的传统的原曲,我也唱不完整啊!我只是用这些特征——语言特征、旋律特点。后来的现场很好。其实,越来越多的人,真的喜爱这些歌,并且很感动。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我们更多应该讨论精神对于音乐的影响。我们的最根本问题,或者说,能不能真正产生这个时代的民歌语言。我们现在还是在用传统民歌的方法在做现在的音乐,其实,我的歌词后来都在做这样的尝试,我可能需要第二次静下来,慢慢地,产生东西,形式,是最难建立的。因为关系到环境,比如我对打击乐的中国化尝试,因为没有合作者,渐渐破产。 怎么说呢,我看重的是我是否有这个能力,现在还没有走到那里,我也不能说我自己就会怎样。先这样写写唱唱,以后再说。 21.说说你即将发行的唱片?它与以前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答:一些新的伙伴,新的录音方式,在北京,十三月厂牌投资了这张专集,但是,我想我首先喜欢唱片的封面和内页设计,还有我们所有人为之付出的很多努力,包括张然、胡朗琅和小胖子郑子强,我觉得他们的热情和几乎可以说是艰辛的工作,让我感动,别的我没有什么可评价的,只是希望更多的人能收藏这张唱片。12月15日,在北京星光现场会有首发演出。 22.最后一个问题,向所有不知道你的人介绍一下你自己。 答:一个平常人吧,就这样有别人身上所有的缺点,喜爱音乐。别的,就没什么了啊! 采访/刘均 附: 关于歌唱 有一天,我们发现从小熟知的几句民歌,永远不知她的整首是什么样的了,有些时候我是奔波在找寻民歌的路上,我讨厌采风这个词,我更想看到他们的生活,他们在生活里歌唱的态度,他们怎样用身体来完成歌唱,而不是用五线谱或者阿拉伯数字来记下他们的旋律,其实我们不必去远方找寻所谓的艺术梦想,在很多那样的地方,贫瘠但是倔强地长着我们的父辈,苍凉的黄沙滩和土房,黄色的村落,没有一点绿色,冬天枯草边那结实的冰,和来来去去相处一辈子的人,他们能把村子里每一家了解得很熟悉,我们的爸爸和妈妈叔叔和阿姨们,忍受贫瘠,在这里建工厂,造化肥,他们为忙碌后的低工资无法维生而争吵,哭,为生活的一点点改善而从心里笑,我们,还有后来的少年,同样生活在贫瘠的土地上,那样倔强,我们的生活在发生改变,跟随逐渐嘈杂起来的小城镇。日出的时候,各种街心公园,伴随忙碌起来的汽车喇叭声,老人们把迪斯科等音乐开得天响,在跳舞。夏利牌出租车和拖拉机,还有摩托车擦肩拥挤,夜晚来临的时候,站街女和加班辛苦一天的女职员擦肩在并不宽的街道,不远处,即是一大片充斥各种化肥的田野,哪里不是这样呢?一切虚幻而真实,我们的生活更多的由此组成,我们说什么原生态?我们的血液在悄悄地丢掉,因为我们想要换成统一标准的所谓世界化,换成向前看齐的统一姿势,穿上统一品牌的职业白衬衣,我们手里的琴声要用统一经典的音色来衡量优劣,以各种分类,在此包裹下的喉咙和心脏渐渐随着改变,但是,街道的两边,依然结集了各地的方言,陕西人的面馆,乡音明显的宁夏人,甘肃的面馆伙计,新疆的羊肉串,河南来的真假和尚,在西北各种装修很爆发的酒吧里,深夜的划拳声, 浓重的西北口音,依然像在战场,这是我们加快脚步的结果,新世纪的新民间,在新的音乐形式下,曾经发出了鱼鼓书、贤孝、秦腔的声音的人群,在今天,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语言吗?可以有自己的习惯吗?能发出离人群最近的歌声吗?能在生活中歌唱吗?能让眼泪和笑都在歌唱里更直接吗?能尝试让血液回到身体里来吗?通过喉咙,可以有自己的身体发出的歌唱吗?希望能听到我们掩盖在笨拙的表达下的声音,有关逐渐被公路和楼宇吞噬的土地,有关简单卑贱得像蚂蚁一样奔波惶恐繁衍生息的人群,有关我们血液发出的哭和笑,有关变了型的家乡的消息,有关生活的细节,更多,但,不仅如此。总之,我希望在生活里,快乐地歌唱! 文/苏阳
【发表评论】
|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