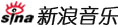|
|
中国之声:独家盘点2008十大民谣唱片
北海道有萨摩琵琶,南美有玻利维亚山歌,北美有布鲁斯传统……中国有迟志强,还有高晓松(听歌),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们把许巍(听歌)称作民谣。大多数听众一只脚踩在柏油马路上,从Soulseek上如饥似渴地寻找他国的秧歌充饥。野孩子是第一个春天,在河酒吧我们开始真正掌握把另一只脚埋在土里的秘密,而08年的时候,开始有更多的理由来把我们身上唯一负面的情绪——乡愁——给对付过去,不过不是Folk,更像是Fusion。(说明:以下十张唱片有个别不是08年发行的,但是,却是在这一年被大家给挖出来。)

《十方》冬子
你去旅游,黄土高原,深山长风,大钟敲古寺,叶落梧桐惊,风景很好,但是你确实是多余的现代化,如果你还想顺着传统找到那颗环保的良心,那么请听[十方]。有鉴于此,我们才能够相信,高渐离的击筑悲歌真的不是故事会,而双手劳动是可以慰藉心灵的。器局宏敞,又能小心翼翼地唱反哺的摇篮曲,这里是一条大河,你会说,时光易逝,水滴中一匹马儿一命归天。大抵如此,总有些时候,你对生活有一些感悟,可是汤姆·维茨安慰不了你,于是轰隆隆的雷雨声在冬子的窗前。

《东方红》赵牧阳
先从标题的对应解释说起,我的意思是,那么这是一个并没有全面解释之道的念头啰?好像没有什么公平和温馨的东西了?所谓的价值观已经衰落了,人民只好去流浪。前摇滚乐手赵牧阳选择了移居和隐居,选择了三弦、花儿和信天游,选择了颗粒无收的秋天和不解释不接受的狠心,听觉上的特征则比艺术涵养更纯粹,就是街头和走穴的囚歌传统,可是能够把悲壮唱成缠绵,确实是更高古的悲壮。

《IZ2007》IZ
IZ是一支由哈萨克人组建的民谣乐队。有个电影里的情节是这样的,有个老头儿,有念珠一串,弟子无数,生活中无数地雷引而不发,后来有一天念珠突然断了,于是他对弟子们喊道:念经,念经,大家一起念经。我相信,大多数人没有去过新疆,不明白游吟和宗教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载歌载舞的传统也多见于王洛宾的报道,现在大家有机会了——对于可见之生活来说,根源和低处文化,比较接近于学术黑话,所以,念经,请大家一起念经。当然,经书不是经书,我们说的是音乐。

《蒙古新民乐》杭盖
让这张专辑在欧洲发表是我们的耻辱,而不是骄傲。请原谅这小小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而杭盖却是那么坦然:开在高山上的花朵,可怜最早凋谢,远嫁婆家的姑娘苍老在爱人怀中……杭盖早先是铁血丹心的摇滚党员,后来一朝悟道,决定不往前冲,反而向后退,于是后退到了草原的深处,自己所从来的地方,结果让把后卫变成了先锋,而原来的先锋听了这些老茧恒生的歌曲,就先疯了。

《灵山的儿女》保新谊
好听,真的好听。好听到明明是在电脑上听,却满耳朵都是百年教堂里散淡的回响。把西洋乐风和原住民名歌融合在一起,我们在青歌赛和春节晚会上听过太多了,但是分明没有“地层下的一点光”,只有这次,把贵州的山歌系在世界音乐的风筝上,飞的那么低——不,这个一点儿也不重要,甚至内涵和指向也不重要,真正的价值在于它包含了一种久违的超逸和矜持。

《脚步声阵阵》美好药店
美好药店不是让人怀疑民谣是否如此,而是让人疑心自己不懂音乐,而民间的最后一点精魄投射在崂山道观的墙上,不是合理性的听觉新欢,分明一个坦荡的鼓书艺人,讲不高明的骗局,骗局也是有冷血的幽默感的,幽默感也是山寨的,有土气的野性,和精明的市场定位。少说几句,少说几句,听众一个比一个狡黠,一个比一个才华横溢……还记得第一次听“四大天王”么,你觉得自己能听懂这个,是多么酷的一件事情。现在依然如此。

《红布绿花朵》小娟(听歌)和山谷里的居民
开头是这样的,写在人生的边边上,这种人生其实不属于山谷,只属于城市,因为山谷里居民是不会怀念山谷的,只有城市里的居民会。通常是这样的,大家都很轻巧,都很柔和,与所爱的人一起,同时出神地创造一些能够引发美好事情的念头,而接下来的故事由小娟讲述,合乎规范,妙语连珠,恰到好处,甚至有的时候能让人心无邪念地欣赏某类过分的精确。

《遥远》王娟
开头是这样的,写在城市的边边上。其实已经不太像民谣了,有点儿像流行。我明白你的感受,你真不喜欢流行,可就是偏偏喜欢王娟。[遥远]表现的不是怎么平衡生活,恰恰暴露了我们止步的边缘所在,差一线就是骚动与崩溃。王娟本人许是也点儿犹豫了,于是把耽美——这么烂俗的形容词——的声音稍稍往后退了一小会儿,退到配器和水泥森林之后,留出一片长满云的天空。

《冬》白水
强烈的弦乐特征和神秘主义倾向是给人的第一印象,对于不惮于精神受缚的新青年们来说,捏造从未见过的高山流水首先是实验的,然后才是抒情的。所以告诫后来人,臆造的浪漫情怀和向壁虚构的古风,不要太忠于自己的品位和生活体验,以免一针见血,以免辗转反侧,以免暴露生活里面的好些个虱子,连难堪的矫情和浅薄的逃避心理都摆在台面上了,你要能听见哲理,大概就是这意思了。

《你等着我回来》张玮玮和郭龙
故事是这样的,有两个羞涩的文质彬彬的流氓,他们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两人分别写了情歌,后来递小纸条的时候,撞车了,于是就相约一起写情歌。他们一开始叫“黄河双煞”,后来被人称作忧伤的民谣歌手,但是大伙儿在低吟浅酌的时候听见了他们的歌词,又管他们叫做诗人。而心里坚持着等那一杯茶的人们,会坚定地热爱这前苏联的手风琴传统、老于世故的单纯,以及锦心绣口喝醉了一口吐出半个深绿的那什么,美好。文/阿布
声明:新浪网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更多关于 民谣 的新闻
-
刘洋:从《校园民谣》到《我唱我歌》 2008-12-26 07:59
刘洋:郑阳的校园民谣 2008-12-26 07:57
洪启城市故事巡演落幕 要将民谣挺进新空间(图) 2008-12-24 21:04
杨嘉淞演绎经典 “杨家将”震撼天津民谣专场 2008-12-16 16:54
冬子(十方)新专辑将首发 根源民谣加中国民乐 2008-11-27 1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