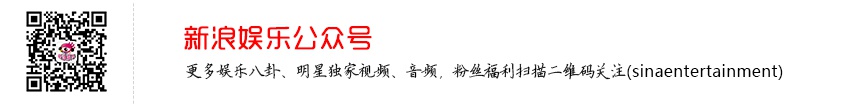郑钧单曲MV发布
郑钧单曲MV发布
□专题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丁慧峰
摇滚歌手、超级奶爸、音乐创作人、动漫公司老板……他当然不仅仅是这些角色,他还发新歌、上综艺、做产品,改编自同名漫画书的动漫电影《摇滚藏獒》即将上映。对,他就是郑钧,日前他更摇身一变成公司高管,带着自己开发的国内首款音乐众创类APP加入太合音乐,担任首席架构官,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专访时,郑钧笑说:“首席架构官,我也不清楚是要干嘛,我只知道我在干嘛,就是做一些架构上的布局吧,特别是在互联网音乐这一块,做一些部署和策略。”说这些话的时候,郑钧已经特别不像是《灰姑娘》、《赤裸裸》、《回到拉萨》那个年代桀骜不驯放荡不羁的摇滚歌手,而是一个创业者,一个时髦的满口“互联网+”的商人了。
谈创业:我是属于行动派的人
“音乐圈的人挺奇怪,版权收益问题在那很久了,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问题但大家都懒得动去解决”
无独有偶,在郑钧加盟太合音乐担任首席架构官之前,何炅[微博]加盟了高晓松[微博]和宋柯掌舵的阿里音乐担任首席内容官,王力宏[微博]也在QQ音乐有了自己的工卡。明星偶像们不约而同拥抱了互联网,但是不同于何炅和王力宏的是,郑钧是带着自己研发的产品和整支创业团队加盟。
王力宏到QQ音乐其实是工作室和腾讯合作,相当于进一步开发明星个人的资源,尤其是在互联网领域深度携手;何炅到阿里担任“首席内容官”,首先他不会放弃自己在湖南卫视的主持工作,本人在阿里音乐全新布局中所担负的职能尚待观察。而郑钧和他的“合音量”是已经成型的APP,这个拥有原创、接力、出品、大赛等功能,覆盖了用户创作音乐和平台互动的需求的产品,基本是郑钧一个人天马行空的创想,目前不仅已经完成融资,并且完成了“百万征歌大赛”,已经有张羿凡的《化妆舞会》等作品问世,首张原创合辑也在准备之中。
在说起这个产品的时候,郑钧的“创业者”角色再次上身,用他的说法——“合音量”是在改变传统音乐创作模式,也是他6年磨一剑的成果。6年前,手机APP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活跃和俯拾皆是,郑钧说6年前也是整个音乐行业最低谷的时候,自己身在其中,“行业的问题出在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反复想了很久,最后想到这样一个办法,当时有一揽子计划没有人听得懂也没有人愿意跟我合作,人都凑不齐。到2014年的时候手机应用已经越来越普及,大环境各方面凑齐就着手这件事,这个项目执行时间也就半年时期吧,本来是第一轮融资的时候,太合的钱总就跟我聊,刚好他们刚并拢完百度音乐,说服了我把整个‘合音量’带过来加入到他们”。
普通人可能觉得“合音量”这个APP太过专业,但对于玩音乐的人来说却方便易用,并且郑钧非常“简单粗暴”地理清了整个行业都纠缠不清的版权收益分成——一首作品获得收益后,将按照用户登记信息进行收益分配,作曲30%,作词30%,编曲30%,演唱10%,这样的模式保护了创作者的最大权益,也实现了集体创作音乐的可能性,郑钧说自己可能是第一个这样做的,“音乐圈的人挺奇怪,版权收益问题在那很久了,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问题但大家都懒得动去解决,我是属于行动派的人,发现这个问题找到解决方法就去干这个事是吧,就这么开始了”。
记者手记
郑钧的“自我架构”
受访时郑钧他刚刚开完会,现在的郑钧就是一副老板模样,连轴转的会议让他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合音量”和《摇滚藏獒》,还有一大堆的活动,还有新歌推出,演唱会也定了好几场,各种角色跳换。郑钧说上一段的清闲反倒是带儿子来广州,看了一个星期动物,没有助手,谢绝朋友,觉得特别好,好到不可思议,但2016开年又进入精疲力尽的疯狂状态。其实不经意间连郑钧都快50岁了,但就像他反复强调的,现在的自己很快乐,因为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他说自己不是合格的生意人,开过农场现在已经荒废,开了公司一年都不去一次办公室,但自认是创意型人才,提供了大量的创意和想法,他的APP如果进一步如愿,的确能够对扶持乐坛新人新歌做出贡献。郑钧对自我的架构,比年轻时候的放荡不羁更清晰。
谈互联网:越难啃的骨头越愿意啃
“如果我继续只是做一个歌手,只是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有演唱会有音乐节也可以活得很好”
“合音量”上线两三个月的时候,郑钧发现有各种公司在偷偷跟平台上的创作人签约,这也逼着郑钧把原来与创作人签的数字协议改为书面合约,而从另一个角度,也验证了这种模式在市场的认可度。郑钧说最开始只有两个老板支持自己,因为这两个老板是业内大佬,所以融资非常容易,而为什么走上正规后这么快选择加盟太合音乐,郑钧就说如果单独自己这么走下去对实现整体音乐上的想法有很多阻碍,所以加入太合的好处,就是加入一个庞大的互联网平台跟庞大的传统唱片公司,很多想法可以实现,因为做音乐也需要各个部门可以配合才能把很多事情做得很漂亮。
郑钧反复强调,自己不是一个歌手的身份加入一家公司,是一个产品创始人的身份加入一个更大的平台,自己的作品还是独立的,这是完全的两个身份,加入太合就是公司行为,“如果我继续只是做一个歌手,只是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有演唱会有音乐节也可以活得很好。但我想用合音量给那些受苦的、有才华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平台。我最初的想法是我提供创意,把想法贡献出来,行业内自己解决,但后来没有人实施那我只能自己来做了。我就是特别喜欢这种,越难啃的骨头越愿意啃,这样才有嚼头”。
郑钧不仅对APP项目信心满满,对未来的互联网音乐布局也是非常乐观。他笑说自己是最早的网民,早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用电脑做音乐,“我是最早买苹果电脑的人,见证了互联网的行业从零到有;我大学是学管理,理工男,对这些事情是很热衷的,然后呢我一直积极参与这件事”。
说起互联网,郑钧更加头头是道——互联网对于传统唱片公司来讲是一个危机,是整个经营体系的崩溃,但是对于音乐人跟音乐来讲互联网是一个空前的机遇,“之前唱片公司模式是唱片公司是主人,音乐人是奴隶跟长工,是卑微的,没有任何尊严;互联网出来以后生产者是主人,创作者跟音乐人成为主人站在这个舞台上,反而是平台跟唱片公司是为音乐人服务的。我就是写歌的人,之前都在说互联网冲击音乐行业,其实是唱片公司被打蒙了,但唱片公司拿到钱也没给我们分,做“合音量”说好听一点是一个音乐人有机会给音乐圈谋福利,从这个角度要感谢互联网”。
谈人生:愤怒的目的不是愤怒
“年轻的时候放荡不羁,但通过放荡不羁才能活明白,然后做一些真正愿意做的事”
如果对郑钧了解不多,很难想象这个当年高唱着“我的爱,赤裸裸”的摇滚青年会成为一个满口互联网思维的“霸道总裁”。在早年的作品《商品社会》中,他非常愤怒地唱着“为了我的虚荣心,我把自己出卖,用自由换回来,沉甸甸的钱,以便能够挤身在商品社会,欲望的社会”,现在在他身上已经找不到几许“愤怒”的因子,而是成为商品社会的弄潮儿。对此,郑钧说:“愤怒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愤怒。那个年纪需要愤怒,现在是愤怒还是慈悲这都是表演,没有意义,重要的还是把事儿给办了。”
除了“触网”,郑钧在很早之前就参加过综艺选秀,当过《快男》评委,在《中国最强音》做过导师,在《中国好声音》做过“梦想导师”,同样是选拔新人,但是在郑钧看来,最大问题是环境,“我对选秀节目的了解比别人多一些,我很早就参加过,但这些节目是以收视率为前提的,不是以发展音乐出唱片、繁荣音乐为目的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综艺选秀的焦点不会是音乐本身,焦点是怎么利用音乐本身,我们要做的是把焦点放在音乐本身,牛叉的歌,牛叉的创作,本身是我的焦点,这个东西获得财富跟尊严是我们要做的事。音乐人完全以他的才华来变现,不是需要别的办法,就会有很多牛叉的作品产生”。
对于当前平台越来越多,好歌却相对越来越少,而新人想要出头也并不容易的现状,郑钧就说,20年前虽然大家都穷,但那个时候创作者赢得的真正的热爱跟推崇,就像《灰姑娘》也不是主打歌,是自发的成为排行榜冠军,没有任何功利色彩是无私的心态;现在一部分人很有钱了,大部分音乐人没有钱,同时有钱跟没钱都没有尊严,因为没有人热爱音乐跟关心你的歌,只要你会表演就行,这种情况下,吸引眼球就是成功者。
郑钧说,当下的音乐环境是空前的冷酷跟残忍的,现在就得改善这个土壤跟环境,因为现在是空前的功利、空前的冷漠,完全以吸引眼球为前提定胜负,没有人在乎音乐的传播跟本身的价值,这样的环境天才自然就会撤退,“所以我认为我在建设一个温室,一个孕育天才的土壤跟环境,这是我们的目的”。
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的郑钧,现在张口闭口都是“颠覆”和“尊严”,但他自己也生活得非常滋润,拥有娇妻贵子,通过《爸爸回来了》也让世人见识到他的生活状态,长期的静修和瑜伽也让他身心健康,对此他笑说:“人应该这样,年龄大就是活明白了,年轻的时候放荡不羁,但通过放荡不羁才能活明白,然后做一些真正愿意做的事。现在也越来越觉得浪费时间也浪费不起了,浪费身体也透支不起了,那就干些有价值的事。”
对于什么是有价值的事,郑钧就很形象地说:“就像开车一样,年轻的时候是跑车但我没有驾驭它,没有方向到处乱跑;现在是轿车我可以驾驭着去我想去的地方,车能为我所用是我的工具,而不是炫耀。年轻的时候不过是自以为司机的乘客,现在的我最快乐,因为我完全可以掌握自己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