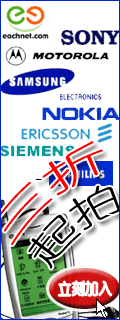|
洛兵
网上有很多人在骂高枫,说他过气了,所以炒作自己。当然,也有很多人在缅怀。我看了那些谩骂,觉得很难受。高枫明明昏迷不醒,怎么炒作?再怎么炒,也不可能拿命来开玩笑啊。我很想告诉他们,高枫虽然身在演艺圈,却是个非常直率,非常真实的人,决不会用这些低三下四的方法来恶炒自己。况且,不管如何,你们或者唱过他的歌,或者被他感染
过,在他的作品里倾泻过自己的情感,被他的音符安慰过,为什么现在,还要这么不留情呢?
有人突然提起了当年高枫被骗那件事。
现在几乎可以公认,那是DJ的错。网上有人说,那天中午,一个武汉大学的学生打开收音机,收听楚天广播电台直播。主持人是很有名的张驰,现场以不通知对方的方式电话采访了高枫,高枫说,昨天玩的女人不爽,身材不好等等不堪入耳的话,他们全寝室都震惊了,没有想到一个大陆的歌手居然说出了如此下流的话。
我没有亲耳听到那个版本,我听说的是,高枫没有说过玩女人什么的,而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圈里的一些朋友,一些作品评头论足,很不客气。显然,这样的话传出去,是要得罪很多人的。
当然,张驰让我们大家都很反感,并且很害怕。后来,广播电影电视部下了一个文件,停止了他的节目。再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各地的音乐节目,很少有直播的了,都是录播。热线也变得几乎没有了。
我们都有黑暗面,都有自己的隐私,写这段不着四六的哥们,你就没有过黑暗的时候,你就没有过卑鄙的时候?歌手也是人,艺术家也是来自大众,为什么不能有黑暗面?至少,对于我来说,我就有很多黑暗面,但我没想过招摇过市,而是小心收藏,时时在努力克制,我并不想因此得到表扬,只是不想让我的隐私曝光,这个要求,可以做到吗。
我发现,很多时候,人们总是把我们想象得过于好,或者过于坏。到了今天,在高枫走了以后,我才深刻地领悟到这一点。
现在我跟这个圈子保持一点距离,并不是害怕流言蜚语,而是我本能地需要离开一些,需要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而不是花天酒地,如高枫一样,即使有惊世之才,依然沦落进去,在不知不觉间把自己彻底毁掉。
《大中国》火了以后,高枫的传言更多。有个笑话就是讲他的,说一大堆人坐飞机,有北京上海广东的音乐人,高枫突然神叨叨冒出一句:
要是飞机掉下来,中国的流行音乐该怎么办呢?
这个笑话,跟有关指南针到了北京到处找崔健查琴的故事类似。高枫听了,淡淡一笑,也就过去了。
他实在是个沉陷音乐的人。他的乐趣都在那里,而不是在鸡毛蒜皮上。这一点我佩服他。我比较易怒,如果受到攻击,肯定要跳出来为自己辩解,跟敌人战斗。这在我没有开始重新写小说之前,一直如此。
我还佩服高枫的一点,是他的才华很管用。
请注意“管用”这个词,这是不同于“实用”的。高枫脑子非常好使,而且有某种贯通艺术门类的能力。他能随意利用一些很微小的音乐元素,创作出非常实惠,甚至媚俗的东西。比如《大中国》。
《大中国》刚刚出版的时候,还叫做《中国》(大中国),题目如此之复杂,做作,炒作都不知道收敛一番痕迹。这首歌,在创作圈里是很不齿的,许多人拿出证据,认为他这首歌糅合了四首民歌,所以是赤裸裸的抄袭。他们说,《大中国》把《茉莉花》《东方红》《国际歌》什么的全都弄到一起,简直是对北京音乐界的污辱。
我觉得没有这么严重。伟大的才华从来都是孤独的,因为它有一种赤裸裸的伟大,而伟大的成功则是只能领先一小步。我在这一点上做得很不好,我总是喜欢走得远一点,慢慢地,失去了身后的跟从者。这一点,高枫做得比我好得多。《大中国》甚至不领先,只是融入群体,所以,我在当时居住的黄寺天天晚上听见民工高唱《大中国》,就知道,高枫做对了。
高枫自己谈过《大中国》的创作,他说,为了表现中国地大物博,人杰地灵,这首歌刻意运用了四个地区的民歌元素,中间有很讲究很技巧的连接,但是不会影响到整首作品的气势磅礴,庄严雄伟。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创作,这是一个工程。”高枫说。
我理解他,我喜欢他的才华。我知道,他除了《大中国》,《伙伴》,《丰收》这种俗气的作品,还有《重来》,《春水流》这样才气横溢,优美深邃的作品。
我们经常在走穴的饭桌上聊音乐,有时候,在回来的飞机上也聊。
你太孤傲了,高枫对我说。
我总觉得写歌是耍小聪明,我不喜欢这样,我说。
不行啊,我首先要站住脚,高枫说。
我理解你,我说,但我做不到。
我们其实可以联合起来,把这个市场完全占领了,高枫说。
已经占领了,我说,你看看,这几年,什么地方不是我们的天下?那帮老家伙要把我们恨死了。
哈哈哈,高枫笑起来的样子很是可爱,非常纯真,带着一种狡黠和智慧。
你的作品我喜欢,高枫说,很是风花雪月,风骚入骨啊,但是,你太孤芳自赏了,你跟大众的距离太远。
我知道这些,我说,我没办法改变。
不见得,高枫摇摇头,又露出了我熟悉的那种若有所思的表情,你没在这上面动脑子,真的。对了,你如果自己去唱,肯定比给别人的要好!
为什么?我说。
我也说不清楚,高枫说,或许,那样更能表达你的意志吧?
你说得有道理,我说,哪天,等我想通了吧。
《大中国》之后,高枫渐渐沉寂下来。但是很快,他又开始蠢蠢欲动,要争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他写了抒情而洋气的《重来》,写了缠绵悱恻的《秋》,写了创新意识浓厚的《葵花向太阳》,写了一咏三叹,美不胜收的《伙伴》,大家却都不知道,或者明知道是他写的,却都认为:高枫就是《大中国》,《大中国》就代表高枫。
我真他妈生气,他说。
这很正常,我说,我也一样,我那些得意之作还不如你的《重来》有名呢。
你的歌不错,主要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唱,高枫说。
怎么讲?
《接风洗尘》要是田震来唱呢?《心有些乱》要是孙楠来唱呢?高枫说,还有你那个什么女人,要是刘德华来唱呢?
《遇上一个成熟的女人》,我说。
就是啊,你看我,写出来,就要给那些大腕唱,不然可惜了,高枫还是那么直率。
我默然。
但是我自己也不能闲着,他思忖道,要找到另外一种方式释放自己,你明白吗,释放我自己!
我点点头,表示很羡慕。这么多年,无数人劝过我唱歌,我却始终不是很起劲,看来,我也要在这上面好好考虑一下了。
很快,高枫写了《坏小孩》,被刘德华们传唱,火遍亚洲,但他还是觉得不够。他要去英国体验生活,或者是做别的事情,我还以为他可以从此脱胎换骨,改变一种新的风格。毕竟,《大中国》完全不能代表他的真实水准。他需要一个新的突破,新的起点。
但是我看见的,是这样的消息:
————高枫英伦体验生活 带回十首新创歌曲
远赴英国感受了伦敦的绵绵细雨之后,高枫带回了十首富有异国情调的新创歌曲。
以一曲《大中国》一炮打响的歌手高枫,赴英国学习归来后,眼下忙着制作在英国期间制作的歌曲专辑。当和记者谈起他新专辑中的一首歌时,高枫忽然冒出一句惊人之语。
高枫:“有一首歌叫《雨》,说是送给一个女孩,其实也可以送给伦敦,我和伦敦有了一夜之欢。”
以雾都著称的伦敦,在高枫眼里更象雨都。高枫笑言,伦敦的雨说来就来,说去就去,而他则承欢在绵绵细雨中。他说:“和它一起吃饭,一起睡、一起玩、一起学习,伦敦成为我的情人,实际上,我在那儿组建了一个乐队,歌手来自不同国家。”
高枫坦言,新专辑里的歌都是在英国期间录制的,把歌曲拿给老外录制,高枫一点也不担心专辑的国内市场,他觉得能够把握国内观众的欣赏口味,他认为观众喜欢简单,直白的东西。
看着眼前的高枫,虽然一身酷酷的装束,可感觉比演唱《大中国》时少了许多活力,不知是英国的细雨,还是伦敦的一夜之欢让火火的高枫变成一幅温柔模样。
这是个叫甘雨的记者写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我和伦敦有了一夜之欢”这句话,突然有点心惊肉跳。高枫的直爽是很可爱的,放在这里,却有些不尽然。圈里有了些传说,但我希望那是假的。世界总是风云多变,波澜诡谲,这些事情,一晃而过,也许不会留下什么吧。
电话又来了。我知道这一天我是不能清静的,我一直在观看,在回忆,在平息心头涌起的淡淡波澜,想睡个午觉,也是不可能了。
张蕾说,昨天正跟丁薇他们在一起。丁薇说,我们还是好好活着吧。
我要去医院,说马上就不行了,金兆钧说,还不知道能不能进去呢。
我听到的消息,医生说,他的治愈率,是百分之零,郭亮说。
我想,这个时刻,高枫在想什么呢?他的事业一帆风顺,正要大展宏图,但却被夺去了性命,这个圈子,真是需要洁身自好啊。才华并不是全部,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时间太短了,我们都需要很多时间,才能完成想要完成的东西。
高枫昨天晚上已经走了,甚至有人这么给我说。
我很沉重,不止是物伤其类。
真的。
我想起九二年,我们风华正茂,正在百花录音棚录制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高枫来了,是来找王迪的。王迪是李玲玉的制作人,找高枫约歌,高枫说写好了,王迪问,在哪里?高枫四下里找着,看到了一把吉他,周笛的,于是就找周笛借来,坐在录音棚门口的台阶上,轻唱那首脍炙人口的《春》。
真不错,王晓京说。
你唱得很舒服,我说。
嗯,很好,周笛说。
这首是《春》,我还要写《夏》,《秋》,《冬》,分别给不同的歌手唱,高枫说。
你的作品,很是风花雪月,我说,但是说不上来,我又觉得你跟我的不大相同。
当然,很久以后,我知道为什么不同了。高枫的作品,总是缠绵悱恻,婉约秀丽,而没有大开大阖,大起大落。《大中国》是个例外,其他的,都是走向优美,而不是豪放。这也难怪,他是湖北人,不是北方人,他骨子里就非常喜欢这样的东西。他的释放,就都建筑在这上面,朝朝夕夕,不能改变。
我记得那天的月亮很亮,清风徐徐,我们都在院子里,听着奇异的高枫,唱得非常好听的高枫,乐感超一流的高枫。而录音棚里,正在播放我们给陈琳写的歌,那是注定要火起来的东西,在北京,我们就要打下自己的世界。
高枫的经纪人大唐在新浪和搜狐做直播,说高枫有了百分之五十和八十的恢复希望。许多网友认为这是炒作。而只有我们几个心头明白,这不是炒作,高枫真的快不行了。我不明白大唐为什么那么说,也许是迫于网友强大的压力,也许是真想炒作,也许,是想安慰高枫的父母。
我知道,高枫入院的时候已经病入膏肓了,我还知道圈里很多人都明白,但是都不好说什么,网上的口水是很可怕的,男的会认为跟高枫有一腿,女的会被他们骂去检查身体。网络从某种角度上说,是一个发泄的地方,平常有什么不如意,都可以在这里倾吐出来。高枫在二零零二年九月,成了网络的一个出口,成了大众意淫,辱骂,羞辱和诅咒的对象,而那些人在骂高枫正在病床上一边数钱一边哈哈大笑的同时,高枫已经上了呼吸机,已经被切开气管,已经要走了。
那几天,铺天盖地,无边无际的谩骂就像层层叠叠的乌云,把高枫的名声染得一片狼藉。当然,他最后选择了死亡,也可以说,死亡帮助他得到了解脱。
相对于他的所有作品,他最后这一步,走得如此豪放,如此坦荡,给他仅仅三十五年的短暂生命抹上了一种辉煌的血色。
九月二十日凌晨,我又睡不着了,又做了一些怪梦。我不知道是蟑螂,还是其他。头天,中国女篮二十九分输给了澳大利亚,南京投毒者已经抓到。还有人来造谣,我刚给郭亮填好一首陈倩倩的词,他就告诉我,说有人听说布什遇刺了。世界依然在动荡,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要我们现在作出判断,就像判断高枫这件事是否炒作一样艰难,而又那么容易出错。
然后,我就把手机设定成无声,就去睡觉了。我从九二年开始录音,一直神经衰弱,都是长时间泡录音棚,昼夜颠倒造成的。我现在的作息时间是有阶段性的:一个月彻底黑白反转,一个月彻底正常。而九月,我是必须在十二点之前入睡的。
我梦见那些完不成的功课。我已经习惯了,我已经死皮赖脸,谁来催我也不怕。我梦见我给人写了歌,拿不回钱,我也不能把人家怎样,这年头,词曲作者总是要受欺压。我梦见姜文和张艺谋要演我的《新欢》,而我跟杨钰莹的经纪人谈得很不错,我想推荐杨钰莹演女主人公烟烟,但被成千上万个网友骂成最不要脸的炒作。我梦见墙壁又在动,我的心头很是不安,我对自己说,不要醒来,不要出事,真的。不要。
但是我醒了。满心乱跳,满身是汗。我并没看见久违的蟑螂,也没有咬我自己的舌头。我才睡了六个小时,却一点都不困了。我心头堵得慌,像做错了什么很不好的事。
不要啊,我暗自祈祷着,抓过手机,看见起码二十个未接电话。我心头咯噔一下,没敢看,急忙上网,打开新浪。
高枫走了。
他走之前一直在昏迷,昏迷之前一直非常坦然,坚强,没有流一滴泪水。这个世界越来越是花花世界,他能够享受,能够体验的东西越来越多。中秋就要到了,家人都团聚在他身旁,而他却毫无所知。他写的音乐在天空上流淌,他要去的地方,我们却不能到达。他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美丽的音乐,却在被人嗤笑,辱骂,骂得昏天黑地,骂得痛快淋漓。他的气管被切开了,上了呼吸机,却有那些或蒙蔽或阴暗的人,在说他吃着方便面一边数钱一边嘲笑歌迷。他用艰难的笔触,留下了遗书,却被认为是一种欺骗。他已经不能活转来,却有人说他有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五十的希望。我要去看他,我要约郭亮周笛,我这几天忙得不可开交,我一定要去看他的,我几乎就要约了,也就两三天的事,他却等不及,这么快,就真的走了。
他才三十五岁。如果他能活七十岁,还可以给我们贡献多少美妙的作品?还可以让多少人欢笑,让多少人振奋,让多少人意趣盎然,让多少人遗忘烦恼?还可以给已经摇摇欲坠,充斥着荒唐可笑的所谓R&B,HIPHOP的中国乐坛带来多少清新之风?他马上就要把民族音乐跟流行音乐学通了,难道天妒英才,这几年的时间,也不肯给他吗?
我可以说我自己要洁身自好,我要保持距离,我要守住自己的阵地,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心灵。但是,我决不会指责高枫,包括他的个人生活。那是他的绝对自由。我尊重他的选择,一如我尊重圈里的各色人等。我现在要缅怀,要为之伤感的,只是他的才华,他的作品。我觉得,一个人可以没有立场,没有主意,没有追求,但是,不能没有真诚,没有激情;正如人类可以没有科学,没有主义,制度和更多的束缚,却不能没有艺术这种美妙的东西。
九三年,还在中央台的胡波组织了一次聚会,请我跟高枫周笛这帮人去,梁雁翎来了,想采用北京年轻音乐人的作品。我们一起去燕山大饭店,聊得很投机,很豪放,酒正酣时走出大门,便是辽阔辉煌的长安街。我们决定不打车了,要从西边一直走到天安门去。
我们一边走,一边笑闹,走在路中央,也不让着车。来往的人群都看着我们,我们并不在乎。我们喝高了,我们的心气儿,在那时候到达了顶点。
暮色四合。大街刚刚喷过水,鲜艳的车灯流淌出一片鲜活的繁华,远远近近的高楼俯瞰着我们,很是宽容,也好像充满了慈爱。我们是被宠爱的孩子,我们冲劲十足,后劲无穷。我们要跟这个城市一起兴旺发达。很多变革就要开始,未来是我们的,我们要把握好每个机会,我们要出头,我们要从各自不同的境遇出发,慢慢走到一条路上。我们要让我们的作品传遍全中国,我们要在那个时候,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幸福。
我好好想过了,我说,绝对可以做到这一点。
是的,很多人比不了我们的!高枫说。
我们要火了,我们要......要牛逼了,我大着舌头说。
以后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周笛说。
我们以后,一定,一定要是兄弟,高枫说。
找个地方......拜把子吧!我差点喊出来。
当然,我没喊出声,因为街景太美,而未来太近,强烈的幸福指日可待,春风得意,让我在后来一段时间也很忘乎所以。也幸好没喊,即使喊出来,即使真的拜了,很多年过去,一切也还是会改变。我说过,人的境遇一旦发生变化,那些回忆,也就只能成为回忆了。
而在很久以后,高枫最难受的时候,我们不在他的身边。经过很久了,他也有了许多休戚相关的朋友。他把田震,黄安叫了过去。高枫艰难地摘下氧气面罩,对黄安说:
能不能帮帮我?
这时候,他已经挺了很久了。他的亲属说,他非常坚强。一直就这么挺了过来。
黄安后来对媒体说,他对高枫讲,如果意识发生混乱,就朝光明面去想想。
他这句话,我想,对高枫来说,算是个最后的安慰吧。
九年以前,《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发行以后,很多唱片公司的人开始找我。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黄小茂说,苏越他们找我填词,是给楚奇楚童的,我很忙,我推荐了你。我谢过黄小茂,心情很是激动。这是王晓京之外,第一次有人约我写东西。
我去到他们公司,一个企宣把歌给我。我拿回来,立刻填好了。简单抒情的一首日本歌,我填了个《你不是我的浪漫女孩》,觉得很有些意境,就到他们公司交活儿。
年轻而帅气的楚奇楚童在汇园公寓等着我。我进去,把歌词递给他们,他们草草看了,递给旁边一个小个子男孩。男孩哼哼了几句,说,好,好!
楚奇楚童有点担忧地说,行不行啊?
男孩笑眯眯地说,别担心,写得很好!你们放心吧。
这里,你看这儿......哥儿俩指着谱子,还有点犹豫。
有我呢!男孩万分自信地说,我来录音,你们俩还担心什么?
我微笑了。我从一进入这行开始,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一直改到对方满意为止。我为此付出过很大代价,王迪有首词就找我改过八遍,还有郭亮,比王迪还多。而眼前这男孩如此干脆,如此快地领会了歌词的意境,这样的合作者,让我多么轻松。
可惜,在这之前,之后,圈内这样的人太少了。
男孩有点爱不释手的样子,拿着歌词,拿着谱子,轻轻哼起来。哼得非常好听,非常有乐感,我想,就是歌手也不一定会这么好听。
你是制作人吧?我说,你真不错。
我在写歌,也在学编曲,以后多交流!男孩站起来,双眼放光,笑眯眯地,热情地望着我。
我想我们能成为朋友的,我殷切地说。
当然!男孩爽快地伸出手来,有点像大革命时期的地下党,认识一下吧,我们是同行,我叫高枫。
2002-9-16
2002-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