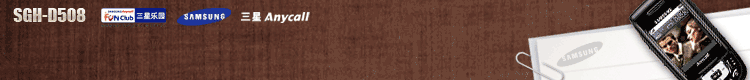贾樟柯进城了!
都说《小武》、《站台》、《任逍遥》构成了贾樟柯的“县城三部曲”,如今,距离高调参赛第6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都大半年了,这个《世界》终于向电影院敞开了公映的怀抱。
“谁有创可贴!”——逼仄的后台,女演员赵涛婀娜的身影中摇曳着脚后跟由不熨贴鞋子折磨而来的伤口;空旷的郊野,拾荒老者木讷的逆光背影映衬着“这么远那么近”的“艾菲尔铁塔”——世界之窗公园伫立的1:3比例缩小版。
就这样,“《世界》——贾樟柯作品”在刻意营造的疏离间隙中从“地下”推到了“地上”。当跌宕的电子乐在富丽堂皇的浩大秀台上升起的时候,没有猝不及防,只是骤然一麻,然后松了一口气,这个《世界》并不完美,但确是一个有趣的明喻,一次见微知著的宏大想象,一趟在割裂的现实围墙与微弱的希望光芒之间摆渡的旅程。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如此罗大佑式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诘问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对于现在的贾樟柯来说,而《世界》的海报上冠冕堂皇地印着“我们是飘一代”——下定义的背后辐射着权力的迁移。张艺谋为“知识改变命运”代言的时候,也许已经明晰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更准确的翻译是“知识就是权力”;而所谓“第六代”中被认定为有大师相的贾樟柯——曾经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旁听生,如今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走出县城进入“世界”后,他坦陈,终于拥有了堂而皇之调动公共资源进行拍摄的便利。
庞杂的线索和断裂的景象,粗糙的Flash故意强调的突兀,类痴男怨女的纠葛,轻描淡写的黑社会暗涌,盲流的国际化勾连,为底层无名民工命名的着力痕迹,还有导演王小帅和画家刘小东“露一小脸”的噱头……《世界》给予我的感觉,“经营”的成分多于“创作”。“进城以后怎么办?”——这是《世界》给当下中国提出的问题,或许也是贾樟柯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也许这是一次挥手告别,也许这是遵循着其成长脉络和运动轨迹的一次拷问和应答。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因缘,从孕育开始,《世界》就不得不在光天化日下逐渐“长大成人”,但是,如果《世界》仅仅被视为一次按部就班的文化事件记录在案,而被忽略掉其作为影像的独立身份,遗忘其进入影院应当发挥的功效,那么它不能被视为一次完满的超越和答复。贾樟柯导演在无数次不厌其烦的访谈对话中一再强调的“进入电影工业”,正是表明了他的清醒,或者还有担忧——“进城赶考”,涂抹在答题卷上的《世界》,看上去光怪陆离,五味杂陈,铿锵圆润,贾导追求的就是万花筒一般的效果,大家随意观看,尽兴发挥。
无论是北京还是深圳,世界之窗公园都位于城市的郊区,城乡结合部缓冲地带,边缘的人们在进城与不进城之间游弋。
我记得某天晚上,胡吗个在浦东大拇指广场上弹唱,旁边是仍未完工的美术馆,顶楼一排整齐的安全帽俯瞰着都市民谣节,歌毕胡吗个下台鞠躬,将吉他凌空挥舞了一下,“再见啊!”——仿佛呼应着《部分土豆进城》中的揶揄:“可是我的外地口音啊!可是我的外地口音啊!”
其实,那天,我很想跟贾樟柯导演说,我也从县城来,我说一口没有人能蓦然判断来处的普通话,好像你现在一样。
于是,我问贾导说,进城以后咋整?贾导说,这是个问题。蒙汗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