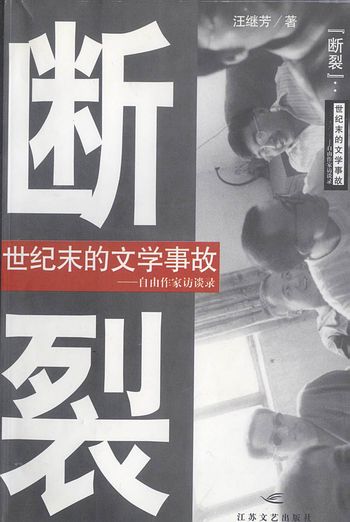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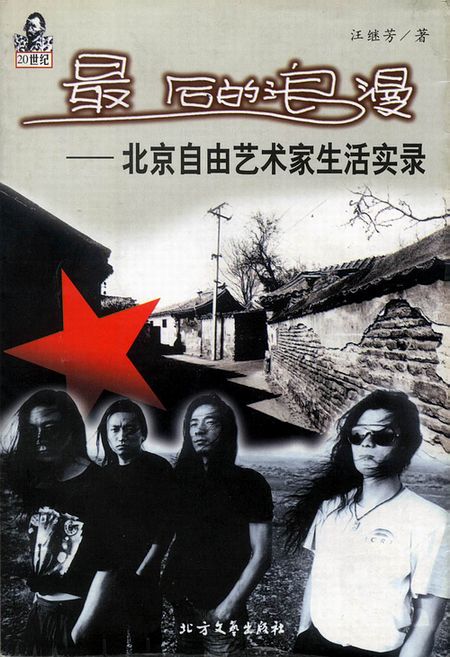
曾经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任编辑的汪继芳,1990年初,离开原单位,陪同丈夫李幸带着他们5岁的女儿前往北京。从此,开始了文化的漂泊生活。
离开北京已整整6年。在北京广播学院毕业读书的4年间,北京留给汪继芳的印象是一个北方的荒凉的都市。然而,89年与李幸来一次北京后,再返回武汉就呆不住了。
一直在做着作家梦的汪继芳,曾是一个标准的文学青年。读大学期间和毕业之后的一年多里,差不多写了五六年的小说。最早,夜深人静时,提一个热水瓶,去教室里写,上班之后是在办公室里写。每完成一篇,都往文学期刊投,屡投屡不中。平淡的经历,使她总想出去闯荡闯荡。再加上在单位总是不痛快,去意早已萌生。虽然不知道出去干什么,可就想出去。
李幸正好有借调到北京的机会,没有犹豫,一家三口就来到了京城。
当时,北京需要购粮本和配给的北京市粮油票才能生活下去,他们就自带来一袋50斤大米和一桶食油。临行前虽然换了不少全国粮票,不过这是一厢情愿,没有指定粮店的购粮本,那时用美元也不能从粮店里买到粮食。
更重要的是,北京文化单位不接纳没有正式关系的人,因此,汪继芳就只好一直在家,成为地道的“坐家”──坐在家里。
女儿与她一样在家“待业”,因为初到北京还没有联系上幼儿园。每天,女儿在院子里自由自在地玩耍,不想玩了就进屋听母亲“讲课”──或是识字,或是画画,或是学做手工,跳绳、跳房子。
为了怕妻女寂寞,李幸买了5只小鸡。因为夜里太冷,第三天就冻死了两只。以后总结经验把台灯点亮放进小鸡睡的纸箱里,但死亡仍不可避免。我们将这些小鸡埋在花坛里,坟堆上,竖着5根小树枝做墓碑。
养鸡不成,又向院里足有七、八米长的一溜花坛发起进攻。先是种上耐旱的美人蕉、地雷花(有的地方叫它洗澡花,原因是用热洗澡水泼它不但不死,反而越长越旺),接着又播了无数粒丝瓜种。院墙边也不让它闲着,种了一排玉米,玉米苗是从野地、沟边挖回来的。为了搞好种植业,汪继芳还专门买了这方面的书。
狂热的种植活动伴随她度过了来北京的最初时光。
短短的时间里,不谙家务的汪继芳竟洗完了家里所有的毛衣毛裤毛背心、床单床罩和被套,整理了无数件衣服。这些衣服上的破洞、开线和脱扣处,以前总在眼前晃动,任丈夫怎么说老婆死了一类的话,还是命令大家将就着穿,没有心情、时间去缝去补。
到北京的第一年,恰逢亚运会。外来人口居住地必然被当地派出所反复盘查,某天夜里,再次来了两位警察,要他们出示身分证明。拿出武汉的身份证,警察又问孩子的,又要拿出单位的工作证。但是警察还是宣布说:你们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某某条例第某某条之规定。
李幸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也在一个大都市里有过正经工作单位。这次虽然没有被抓走,但汪继芳母女却着着实实地惊慌了很长一段日子。每天要骑自行车送女儿上幼儿园或去买菜,自行车还是武汉的牌照,身上没有一丝儿证明自己有资格在北京居住的文件,怎能不时时地心惊肉跳?所以自行车都不敢上大道,总在乡间的小路上窜来窜去,跟鸵鸟似的看不见警察了,但又被村里的恶狗时常惊吓。女儿因此而要求走大道,只能解释说小路来得快。
从一个新闻单位的编辑变成一名自由撰稿人,连自己也是始料不及的。就在汪继芳还未适应这一新的角色时,父母千里迢迢看他们来了。尽管信上可以骗他们,说工作单位在哪儿,工资是多少,但人一到,实际的生活状况就再瞒不住了。
远在郊区,附近连像样的副食商店都没有,孩子在农村小学就读,做饭没有煤气,院子四周飞满蚊子苍蝇……父母唉声叹气,完全不能理解女儿为何丢掉舒适的工作举家北上。这种情况下,岂敢告诉他们自己“赋闲”在家?当一辈子工人的父亲,特别看重女儿由于上了大学在新闻单位工作所给他带来的荣耀。
父母来的第二天清早,汪继芳不得不去“上班”。
当她背着一叠稿纸走出院子时,却一阵茫然,去哪儿“上班”呢?丈夫单位、朋友家里都不方便,最后,选择了离家最近的公园。
这个人烟稀少的郊区公园,一旦将书桌安在这里就令人失望了:篱笆外是隆隆的汽车声,头顶上有蝉儿们疯狂的嘶鸣声。在吵得头发麻、心发慌的状态下,努力写着清淡的流丽的散文。
傍晚,按时“下班”回家。
父母来京期间,很少“请假”陪他们。其实,女儿多么想以本来的面目面对他们。
1992年初春,一位画家朋友来到北京,谈到有关圆明园艺术村的情况。汪继芳感觉他们命运差不多,遭遇、心境也差不多。可以跟他们共命运,同呼吸。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并不关心能否发表,只是愿意交个朋友,来聊聊天。
选择了圆明园艺术村作为我的突破口,是因为曾经有过教训。
在这之前,一次去《北京日报》社,门卫拿出会客单让她填,工作单位一栏,没有填。门卫看了就问:“单位怎么没填?”
“……我……”
“问你呢,单位?”
“没,没有。”
“怎么连单位都没有呢?”门卫认真地问。
“就不能没有单位吗?”
这样一说,门卫态度缓和了,但还是不放她进去。眼看着那些晚来的出示了单位证件的人一个个进去,刹那间,汪继芳明白了自己在这个社会里的处境。
做自由撰稿人随之而来的是那份孤独,自由撰稿人不比做生意的个体户,个体户有自己的客户,与社会有密切的联系,撰稿人虽然也需要出门采访,但更多时候几乎不与任何人来往,写成文字需要大量时间。
在这份孤独里,整日孤零零一个人,到了夜里依然跟自己的影子相伴,而屋外是荒郊野地一片黑咕隆咚。然而,汪继芳还是感激孤独的自由撰稿人生活。这份生活,使她拥有了自信──这是一份从前想也不敢想的奢侈。
在艺术村,汪继芳看到了一群桀骜不驯的年轻人,丢掉铁饭碗,远离家乡,来过这种他们称之为“三无”(无户口、无单位、无家庭)的生活。画家们一边在刚够温饱的日子里喘息,一边在色彩、啤酒、女人中陶醉。此后,多次来到艺术村。在烈日炎炎下,拖着疲惫的身子,每天奔走于十几公里外几十个画家之中。
不过,哪家报刊会发表这种东西呢?
3个月后,这篇将近4万字的纪实文学完稿。一年后,这篇题为《二十世纪最后的浪漫──圆明园艺术村纪实》全文刊登在1993年第3期《钟山》上。
《二十世纪最后的浪漫──圆明园艺术村纪实》全文近四万字。可以说是汪继芳的成名作。此前,她从未写过这么长的纪实性的文字。发表过程一波三折,先后在《报告文学》、《十月》、《花城》及《中国作家》屡试不爽,最后到了《钟山》的编辑王干手里。
1993年3月3日,《钟山》(双月刊)第3期上付排。收到清样同时,汪继芳又在北京城里参加摇滚Party、出入于数支摇滚乐队中,为采写王干所约的《京城摇滚人》。
《钟山》发表“圆明园”以后,纪实类文字似乎成了汪继芳的正业,这方面的约稿开始多起来。
中国的自由撰稿人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年里,以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行走在媒体之间。势必引起各方面的关注。1993年9月,《中国日报》(英文版)发表记者署名文章并配发图片,首次对包括汪继芳在内的“京城四大自由撰稿人”作了详细报道。
1994年2月,《中国妇女报》又配图发表文章专题介绍汪继芳的写作生活。由此关于自由撰稿人现象的报道评说日益升温。1995年,中央电视台在《十二演播室》和《半边天》节目里,又几次拍摄了汪继芳的生活情况。
但是,1996年,汪继芳与李幸带着女儿离开了生活六年的北京,前往南京定居。
到南京后,李幸建议我到南师大教书,放弃写作,教书育人,颇有新鲜感。在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期间,汪继芳向学生强调一种精神和意志,在北京经历的自由撰稿人生活,实际上丰富了她的人生阅历。把所看到和领悟到的一切讲述给学生们,让他们体味和选择,让他们从中得到启示——一个人的成功渠道多种多样,只要你有坚强的意志去奋斗。
原以为大学是个自由、轻松的地方,没想到在体制里到处都一样。整天要创收、交论文、报项目,没完没了的开会和无休止地填表,简直无聊的要命。已经难以适应体制内生活,程式化的东西再也不想忍受。汪继芳认为需要自由地掌握时间,干最爱干的事情。
来南京不久,有关南京自由作家的讯息就连接不断。后来汪继芳陆续认识了朱文、韩东等一批自由作家。一个晚上,与这些作家谈起了轰动一时的“断裂”行为。朱文对汪继芳说,你可以写写“断裂”这件事,很有意思。开始汪继芳去学校图书馆查找有关报刊资料,才发现的确值得一写。
采写与授课发生冲突,开学前,汪继芳终于拨通了院长的电话:请求辞职。
汪继芳的性格是属于叛逆的,无法忍受平庸的生活。从体制内到体制外,敢于叛逆,确实需要付出一点勇气。
《最后的浪漫》和《断裂》)两本书出来以后,在选题上汪继芳便与以前有了明显的区分,因为李幸的原因,他们把把目光转向了很多人想了解的民营电视现状况。于是,两年间先后出版了《身在幕后》还有《中国民营电视现状报告》这两本书。
由于女儿要到北京上学,2002年秋,在南京度过六年后,汪继芳又重返毕业已经18年的京城。也真巧,自大学毕业后在武汉、北京、南京都分别生活6年。
今天,在亚运村附近,好朋友袁梅借她一套房子,汪继芳安心地写作,再次成为“坐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