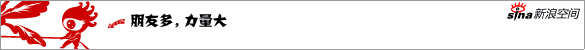|
|
实录:陈凯歌谈新片 比较程蝶衣跟梅兰芳两角色
曹:哪三件事儿?
陈:第一件就是,这个香妈就是福芝芳,好养猫,院儿里好些猫。第二件事儿,那是1958年,他们家有电视。他们家这电视呢,只能进苏联台。是梅兰芳让苏联领导人送的。第三件事儿就是,早上起来看见过梅先生舞剑。他当然不会注意我,也不会知道说,这小孩若干年之后能够拍一个关于梅兰芳的电影,他不会想到。这我觉得这是机缘巧合的事情。
曹:那您父亲,刚才也说过,他曾经拍过梅先生的这个纪录片。在您小的时候或者成年之后,有没有跟您说过,当时在拍摄那些片子的时候,梅先生有些什么样的事儿?给他老人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陈:他提到梅先生是很尊崇的。就是说呢,梅先生这个人特和气。他和气这样一个说法,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时我是不懂的。梅先生在做人上是到了化境。他方方面面都能照顾到,他就是,比如说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他这儿化妆,这边机器全预备好了。他一方面得跟这化妆师催说:“你得快点儿,人家那儿都弄好了。”一方面,他又得说不好意思啊,我催你了。你其实也是为我想把我画得更好一点儿。我毕竟上岁数了。他都能够想得到。所以,齐白石先生能说是而今沦落长安市,唯有梅郎识得君,就是还认识我。所以,他是很周全的一个人。
曹:其实在你之前有很多的导演,也一直跃跃欲试,想拍梅兰芳。可是,梅家也一直没有同意。最终,梅先生的后人还是把改编权交到了您的手上。您,有没有跟他们谈过?他们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陈:我也前两天看到媒体上说,也有人也考虑过这个就是其它很多的导演想拍。我说我是按NBA的说法叫第三或者第四顺位。呵呵呵,不是首选。所以不好意思。恩,跟葆玖先生谈得很高兴,葆玖先生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早认识您了。他说你什么时候认识我?我说我小时候,八九岁我就认识你,他说,你是在哪儿见得我?我说我在街上。那时候,北京骑摩托车的人太少了,他是其中一位。我说我还记得您那是蓝翎牌凤头,单杠小摩托。他说,你那儿记性还不错。我确实是知道,梅葆玖,玖爷,从小就爱玩摩托车。可能这有乃父之风,说老梅先生当年也是修点钟表什么的,对机械感兴趣。所以,葆玖先生呢,我认为在继承了梅先生的艺术的前提下,在性格上也有跟梅兰芳近似的地方。我认为他是一个开朗豁达,懂大义的人。我觉得这也可以说,他在梅兰芳这个片子上,对我有这么多的帮助。那真是尽了对他自己父亲的孝心了。
曹:那现在大家在谈论这个《梅兰芳》的时候,也自然会想起您的另一部力作就是《霸王别姬》。您觉得程蝶衣跟梅兰芳先生在这种个性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陈:其实,我的态度是欢迎比较,都可以比较。但是,两个片子是在不同的时间段拍摄的。那时候,我的年龄跟现在也不同。所以,我自己都觉得,我说的话不一定那么有力量。就是关于这两个人物的比较。因为一个是虚构的人物,一个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一个人物。恩,我想梅先生,天下人公第一,真是真正做到了处变不惊的人。因为,他一生也遇到的事儿太多了。他确实是从来没有张扬的说过自己的长处。他总是谦逊的告诉别人,其实我不如人,我只是万千京剧艺人中间的一个而已。他也从来没有暴露自己在那些重大决定做出的时候,内心的心理活动是什么。我刚才已经说了,他凭什么去美国?1930年美国对中国这个国家有什么了解?资讯不发达,交通不方便,文化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我觉得他是有自己的念头和主张的。他是要去让这个不熟悉中国的这个国度去了解中国有一种艺术叫京剧,这个了不起。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化敌为友的人。怎么才能化敌为友?平等性。极微相似的平等性。所以,为什么他蓄须明志之后,真的有日本人赞扬他说,我并不把蓄须明志这种事儿啊,这样一件事情啊,看成是说全然的出于一种爱国心。我觉得跟他的自身有特别大的关系。他是在,实际上,被歧视全行业被歧视的状态下,几乎是一枝独秀的成为所谓这个旦角之首。他多多少少的会感觉到,他对这个行业,也包括对他个人有一种承担的责任。我一直就琢磨不透,就是他先是到了香港,因为其实1932年,他就搬去上海了。那上海当时是京剧的重镇。那可能现在很多老戏迷还记得当年梅先生的风采。但后来抗难之后,他就去了这个香港。其实,他被日本人拘捕的这事儿是发生在香港。我们在历史上都了解,但是当时日本人给他提过一个条件就是,你可以去重庆,放你走。他从香港搬回上海,这是一个什么意味呢?而且是留着胡子住在上海。南边有梅先生,北边有程砚秋先生。程砚秋先生在卢沟桥务农。我觉得,他不是自大。他是觉得,只要我梅兰芳还在敌战区,还在后方,只要我梅兰芳是留着胡子的,这可能就算做是我对在苦难中的中国的一点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不要事情夸张了。这就是他,这是凡人的想法,这不是伟人的想法。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自己觉得是很不一样的。他,确实是一个有想法的人。我们北京人叫蔫土匪,就是有主意。
曹:还有,我觉得梅先生最了不起的就是说,他身边能够聚集一大批能够支持他的人。比如说,冯六爷,冯耿光是从财政上给予他很大的支持。去美国,还缺那么几万美金,冯六爷愣是给他凑足了这笔金费。还想齐如山先生,过去他从一个痛恨国剧,憎恨国剧,到他写了信给梅先生,对他《汾河湾》提出的一些想法。最后,变成对整个京剧和梅氏体系起到这么大一个促进作用。你觉得他是不是个人有这样人格魅力,能够把这么些个人能够团聚在自己周围。尤其像齐如山这样的,那都是很傲岸很有自尊的那样一代文人。
陈:所以,梅兰芳他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现象。他是发生在民国时代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现象。首先,梅先生他说,我红是为什么呀?是因为有新的观众进来,这都是女性观众。女性观众在民国以后,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那个意义不亚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进了之后,他就说因为不懂戏,所以就要先拣年轻漂亮的看,这是他的自谦之词。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觉得,梅兰芳他是一个五四青年。他是深受时代影响的,像他这样的家庭出身,他有什么的国家民族观念,他应该没有。他就是,我就是唱戏挣饭的,这才是他的本业。对不对,其实张先生对他的评价,进了梅宅之后,与一般读书人家无异。妇女儿童都很安静,这就是有教养的人家。特别在上海这种城市,特别讲究人得有教养。这是这么一个意思。而像你刚才说的,那确实是形成了梅党这样一个概念。数十人,你拿出一个个都是呱呱叫的人物,聚集在他身边。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确实是这样。像齐如山就是官也不当了。是吧,他是清朝同文馆出身,游历西洋,然后回来之后。之所以成为文化现象,就是他是每个人各尽其责的,众星捧月似的,最后做出了一个梅兰芳。但是,反过来看,倘若梅先生没有这样的胸襟志向,他大概也不能容纳这么多人。是吧,因为人都有他的特点的,梨园行我自己就觉得它非常的排外,非常排外。他所以是,梅先生他是所有,为我所用。你只要进言,我就考虑,梅先生甚至有这么一个说法,他一个跟班叫老宋,老宋的媳妇儿其实是一个厨娘,今儿我的那个戏怎么样?我问问宋妈,这宋妈说今儿你这戏课不好看。你的脸跟猴屁股似的,所有人都,诶!怎么这么说话!他说,她不会骗我。她要是觉得不好,我得看看。所以,从这个大官贵戚一直到贩夫走卒,三教九流人等对梅都有一份不同寻常的感情。你想,唐德刚先生就曾经说过这话叫,男人皆欲娶,女人皆欲奖。你说他是做到个什么份上了。
曹:您刚才说到这个五四,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其实当时梅先生在社会各界都很受欢迎。但是呢,当时很多新文化的主将对梅先生有很多的批评,特别是鲁迅先生。我粗略统计,一共有十七处对梅先生的有一些批评或者说负面的想法。但是这个问题跟电影本身无关,就是,我特别想请教导演,您怎么看当时的这种完全两级的这种评断?
陈:所以说,之所以说拍《梅兰芳》有趣,也在于一个,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不是一个顺风倒,一边倒的这么一个人物。新文化的主将不只鲁迅骂他,陈独秀骂他骂得一塌糊涂,说:梅兰芳去了日本,据说很受欢迎。但是,在我看来,若是以他的美貌,那是他本人的耻辱。如果他能代表中国文化,那是中国文化的耻辱。你想,陈独秀,何等样人物!一言九鼎啊!那可以说是批评起来是很有分量的!
曹:那包括当时,这个刘半农,钱玄同,包括这个后来郑振铎。我觉得这个批评的语气都很严厉。非常激烈。
陈:都很激烈!我看资料的时候,还有一位叫熊佛西的。
曹:上海戏剧学院的创立人。
陈:诶!对!说是,听说要去美国,这语气里头啊,几乎是梅先生这要掉冰窟里的感觉似的,要小心了。都是这种语气。
曹:鲁迅先生其实在很多篇文章中都还是谈到说,所谓的他呈现的那种少女形象有点男不男,女不女。这时,当时他可能对戏曲界的总体的一种看法。所以,您这次在拍戏的时候,也特别希望突出梅先生的这种个性,就是在舞台上他比女人更女人。可是,他在生活当中,他比男人更男人!
陈:鲁迅先生的说法吧,可是有失偏颇的。那么鲁迅先生的性格,大家都很清楚了。你看看他所有的杂文集,那除了他是一员主将之外,他也是一员骂将。的确是如此。但且先不去评论鲁迅先生对梅先生的这种判断是否正确,但是至少有一点,我不是很同意的。其实,梅先生是谁?他在文化上代表着什么东西?他代表了在推翻帝制之后在民国出现的一个大的繁荣期。他可以说是在文化繁荣期里面,最璀璨的一个花朵。所以,那个也好玩,他去苏联,然后苏联有个剧作家就问国民党当时驻苏联的大使叫颜惠庆的说:诶!你们怎么弄一个男的严女的呀?这严慧庆也是一戏迷。他就说,要是女的演女的,那有什么稀奇啊?你看,他这话也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鲁迅先生的话里面应该有个文化大革命的味道在里头,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吧,要横扫掉!这不对的这个!而且,这里头还有一个门户之见,那他对齐如山先生他们也是有微词的,说:你们在西洋学了些这个西洋的东西,怎么回了国反而捧起这个戏子来呢?这个东西好像就是有点嘲弄王世襄先生,说您正经的燕京出身,怎么整天玩蛐蛐儿啊?说起怎么天天鉴定明清家具,不务正业!但是,人家王世襄先生是成就了一番大事业的。
曹:我说个题外话,当时上海也有个学者讥讽陈寅恪先生你这么大学问,你怎么就研究一“柳如是”!
陈:所以,这里头呢,我觉得历史的功过是非不去说它。但是,我们看梅先生的态度,梅先生在这样多的讥讽中间,没有出来反驳过。没有一次说,诶!你们各位啊!出来见见,我们沟通一下!也没有说,你们懂么?他既没有以谦卑的态度去面对他们,更没有以傲慢的态度去对待他们!鲁迅先生不懂戏,这是肯定的!这是一定的!他除了当时在绍兴,当年那个可能化州乌篷船社火,那个可能听过一两嗓子,我估计其他的,他也就不太了解了。
曹:他爱看电影。
陈:他爱看电影,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他表现了梅先生的一个态度。就是功过是非,任人评说的一个态度。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相关专题:《可凡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