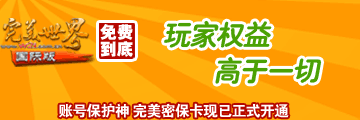|
不支持Flash
|
|
|
答谢培君对《大地之歌》的四个问题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21日09:21 金羊网-新快报
编者按 1月24日本报刊出谢培的评论文章《四问<大地之歌>》,对广东现代舞团的作品《大地之歌》提出置疑。文章刊出后,曹诚渊先生深受震动,写下本文作为回应。一方面,曹先生感觉到自己的作品被误解了,另一方面他也想通过媒体表达一下自己对艺术评论的一些看法。我想关于艺术作品的批评总是仁者见仁的事情,一方面我们“要捍卫说话的权力”,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需要检讨艺术评论在写作中的一些问题。艺术评论需要发现隐藏在创作者背后未能知觉的领域,艺术作品也需要艺术评论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解读。两者之间不是对立。 ■文/曹诚渊 谢培君的文章《大地之上,如何跳舞?———四问现代舞〈大地之歌〉》猛烈批评了最近由广州交响乐团和广东现代舞团联袂演出的节目“当交响乐遇上现代舞”———《大地之歌》。本来任何人看完了节目,便有发表感想的权利,无论是批评还是赞赏,对表演者和创作者来说,拜读后都会有所获益———最低限度,可以从文章中知道别人的想法如何!谢培君的文章引起我的特别注意,是因为她使用了许多现代艺术的术语,但为文的立场角度却是典型地传统,以致文章充满了奇怪的虚伪和概念上的混淆,更有一种隐约的野蛮状态,是一个有趣也可怕的现象,因此为文稍作回应。更重要的,是借此澄清一些被曲解和被滥用的现代舞概念,也算是在学术上的一点思考所得吧! 首先要指出的是,谢培君在文章中努力为自己营造一种视野高越、胸襟广阔的形象,包括极度赞扬前两年的两台“当交响乐遇上现代舞”节目──《火浴凤凰》及《风林火山》,大概认为这样一来,当他在批评《大地之歌》的时候,可以显得更清高,更有说服力?可惜谢君在描写《火浴凤凰》及《风林火山》的时候,只是引用了我在《大地之歌》的场刊资料中的文字,了解现代舞蹈艺术的人都知道,场刊上的文字只是描写了创作时的最初启发点,让观众欣赏舞蹈时有所参照而已,观舞者本人对舞蹈的体会和联想才是真正被解读的本体,有些资深的观舞者因此更索性不看场刊里的节目文字介绍。谢君却把文字照本宣科,甚至误会为节目的演出实体而大加赞扬,使我不得不怀疑谢君倒底有没有真的看过《火浴凤凰》及《风林火山》。 还是切实回答谢君的四个问题吧!其实谢君的四个问题也不是真的希望有人来回答的,他只是借此来评论《大地之歌》而已。现代舞没有固定的程式,观者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诠释和启悟,至于喜欢与否,更是观者的自由,而自由的现代舞该当如此!不过,谢君为文既然是以问题的方式出现,我身为《大地之歌》的编舞和广东现代舞团的艺术总监,少不得为他的四个问题填个答案,图个完整;而更重要的,是谢君的问题,和问题背后的思考逻辑,正正昭示着许多文化人对现代舞的误解,他们早已脱离“看不懂”的简单层次,而尝试用各种现代理论来解剖现代舞;可是在分析解剖现代舞的过程中,又不自觉地抱持着一种传统心态,就是把自己定下的理论作为唯一最终的批评标准。每个人当然有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事物的自由,可是只是用一把单一的尺子(或理论)来品评自由而千变万化的现代舞的时候,批评的声音在许多时候便免不了变成无的放矢了! 第一个问题:“撞击交响乐,《大地之歌》的方式理智吗?” 谢培君的问题重心是:现代舞是要以小见大,而《大地之歌》的主题太大,舞蹈负载不起。她说:“到目前为止,广东现代舞关注和呈现的主题当中,最为贴切和出色的全部都是小主题,或者是找到了以小见大的突破点,这是由于现代舞的特性决定的,甚至说,这是很多艺术创作的通理。” 我不知道谢君说的是那一条“通理”?而这条“通理”竟然可以把原本是自由的现代舞创作限制在“小主题”当中。而谢君认定现代舞的特性决定它要“以小见大”,却教本来是挺自由的现代舞者都要停下来,想一想,甚么是大,甚么是小? 那甚么是“大主题”、甚么是“小主题”呢?谢君大概认为《大地之歌》中提到的“龙的民族”、“人生层面”、“生命感悟”等便是“大主题”,可惜他没有说明那些成功的舞团作品是“小主题”,好让我去比较一下。不过,让我去做一假设:可能谢君认为属于“小主题”的,是两个人间的“恋爱”吧(过去广东现代舞团的许多节目均以此为题),如果谢君从未恋爱过,会觉得两个人之间的爱,是小意思,我们可以从这小爱“见”到对国家、对民族、对全人类的大爱。可是对真正身陷恋爱其中的人来说,对另一个人的爱,可以是他生命的全部,可以为之抛弃国家、牺牲性命。同理,对于一些谢君认为是“大”的主题,比如说“生命感悟”吧,在一些拥有宗教情操,或者感情丰富的人来说,只是日常生活中理所当然的心路历程而已,实在没有甚么大不了的! 所以,当谢培君在《大地之歌》中,只能觉得“一种大而无当,空空如也的感觉”时,不用过于焦虑,因为和谢君有相同感觉的观众,必然大有人在。而同晚的观众里,也必然有觉得“小得其所,充充实实”的人。无他,是每个人的立场不同,起点不同,层次不同而感受各异而已,实在跟甚么“大主题”、“小主题”无关,更不要以甚么“以小见大”的陈年理论来栓着自由的现代舞。 第二个问题:“音乐与舞蹈的呈现为何割裂?” 这个问题奇怪!谢培君认为“闭眼安静听《大地之歌》,或者说当做默片一样地去看《大地之歌》,都好过全面的视听纠缠。两者之间的撞击,显得前追后赶,格格不入”。然后谢君发问:这是否“因为一开始的选题方向出了问题”,并“因为想要承载传达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却无法抓住一个好的突破口,只能以虚入虚?”最后谢君又以发问的口气回答了自己的问题:“试问一下,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在强大的音乐背景下,却只坚实地描述好一个小的但却精致的点,四两拨千斤,是否也是能够完整融合的一个办法?” 在这个问题的自问自答的背后,突显了谢君观看现代舞时的心态和写文章时的思考逻辑,这种心态和思考逻辑正是今日许多自诩为高人一等的文化人在评论别人作品时的通病。谢君并不欣赏《大地之歌》,而在文章中还有意无意地表达出他认为舞蹈应该怎样编的想法,也就是说,谢君已经有了一个对甚么是好舞蹈的观念上的框架,然后拿着这个框架去套他所看见的现代舞。 最明显的,第二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框架:“音乐与舞蹈的呈现为何割裂。”谢君的意思是音乐与舞蹈要融合无间,而割裂了就是不好,所以当《大地之歌》的“音乐到了某个高潮,却发现舞蹈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将大家推向高点”,所以“节奏上的不连贯和气势的缺乏”,使之不能成为谢君心目中的好舞蹈。 我不想纠缠在《大地之歌》的舞蹈与音乐是不是真的割裂的问题。不过,整个第二个问题的问题所在,却是谢君为现代舞设定的框架:音乐与舞蹈不能割裂。传统舞蹈中的审美要求确是要音乐、舞蹈甚至舞台上其它元素的完整融合。但现代舞的出现便一直打破常规,刺激着观众去重新审视过去的审美观念。在音乐和舞蹈之间的关系,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便已经有许多不同的新观念出现,包括音乐和舞蹈是对话关系、是背景关系、是疏离关系、是回响关系、是对抗关系,当然也有谢君问题里的割裂关系。这些音乐与舞蹈之间的实验性尝试就算在中国也已经屡见不鲜,而真正的现代舞蹈创作更是自由翱翔在跟音乐的不同关系之间。 此外,谢君在第二道问题的自问自答里,其实展示了另一种更叫人吃惊的心态。每一个现代舞各有自己独特的面貌,犹如每一个现代人各有自己的个性。我们在品评现代舞的时候,就像进入别人的内心世界,每个世界都千姿百态,有自己的颜色、节奏、纹理和质感。真正懂得欣赏和评论现代舞的人,必然会首先尊重别人的内心世界,就像一个旅行者每次来到新的旅游点,他可以有千百种理由去喜欢或是不喜欢一个地方,他可以把自己的观点逐一陈述,最糟糕的却是在那里指手画脚,要把这里从大变小、把那里从小变大的,那不但是缺乏尊重,更是野蛮了。 其实,也不能过于责怪谢君的野蛮心态,这种心态是一脉相承于传统的舞蹈评论方式。传统的所谓舞蹈评论中,评论者永远是高人一等的权威人士,以权威的心态对作品进行点评。恰恰现代艺术对这些权威形象嗤之以鼻,因为现代舞就是在叛逆和反对权威的路上走过来的。在真正的现代艺术评论中,评论者与被评论者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对作品进行讨论,意见可以提出,观点可以交流,却是建立在尊重每一个作品的本身价值和独特个性之上。那些“你应该怎样修改你的作品才可以变得更好(合乎我的口味)”的貌似文明,实际野蛮的论述,请谢君以后在评论现代舞的时候,最好避免。
图:李剑扬/摄 第[1] |
不支持F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