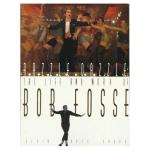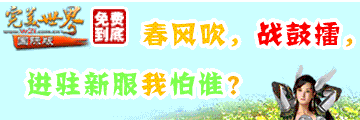|
不支持Flash
|
|
|
|
陈炜智等著《音乐剧史记》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07日11:41 新浪娱乐
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挑灯夜读是一种绝好的休闲。大年初二晚上,我收到台湾朋友寄来的曾合作过的同行陈炜智和陈芸芸半年前在台湾出版的新著《音乐剧史记》,出于对知识的渴求,披衣起坐,逐页品味,整夜无眠。屋内有R&H《南太平洋》音乐相伴,窗外鞭炮齐鸣,焰火五光十色,闪出那瞬间的美丽,反过来映照屋内,妙不可言,给我有点孤独的春节,频添了一番情趣。 现代人喜欢“清除他们自己的历史”(emptied of hisown history),这种反历史心态在音乐剧领域的表现,集中反映在只对当代音乐剧感兴趣,尤其对远离正宗的欧洲音乐剧,表现出反常的疯狂,甚至把麦氏四大音乐剧视为世界四大音乐剧。整个华人音乐剧被一种完全错误的信息所牵引和误导,出于一种极不正常的歌舞病态。在这种情形下,继去年六月笔者《音乐剧的文硕视野》出版刊行一个月之后,华人音乐剧界又一部“清新脱俗”之作《音乐剧史记》(上下二册)在宝岛台湾出炉。笔者尽管到春节期间才得以触摸全书,但仍感欣慰。 一、 体例:师承司马迁和艾瑟·默登 本人看书从习惯上讲,喜欢首先看目录,再看章节,分析作者如何为自己的专著谋篇布局。显然,作者在写作体例上深受两位作者的影响:一位是中国历史学家司马迁的“纪传体”体例,一位是美国当代音乐剧史学专家艾瑟·默登(Ethan Mordden)的篇章题目命题法,后者出版发行的系列断代史专著,每本名字都取自于当时一首有名的音乐剧歌曲曲名:Make Believe: The Broadway Musical in the 1920's;Sing for Your Supper: The Broadway Musical in the 1930s;Beautiful Mornin': The Broadway Musical in the 1940s;Coming up Roses: The Broadway Musical in the 1950s;Open a New Window: The Broadway Musical in the 1960s;One More Kiss: The Broadway Musical in the 1970s。 司马迁修撰《史记》的最高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体系。他终其一生写作的《史记》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以和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相适应。其中:“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以后所有的正史,几乎毫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著作形式。今天,我们很高兴地看到,音乐剧学者陈炜智和陈芸芸也沉迷于此,奋笔力耕,不惜牺牲“百分之百原创”的初衷,为华人世界奉献了被称为“纪传体”的《音乐剧史记》。 《音乐剧史记》是台湾音乐时代文化事业公司“音乐剧系列”中的一种,分上下两册出版发行。作者按《史记》中为人称道的帝王本纪、侯国世家、红伶列传等体例,对音乐剧的百年轨迹进行论述,力图通过简明的体例、生动的文笔、新颖的版式、精美的图片等多种包装要素的“整合”,为读者提供一条认识百老汇音乐剧的新通道。正如居其宏教授在序中所言:“若以游戏心态待之并从纯粹的形式因素着眼,采用这种体例写作,比之于学术性论著来,毕竟少了些枯燥和沉闷,为大陆音乐剧出版物带来某些新鲜活泼的因素。” 当然,司马迁修撰《史记》如果自我标榜“百分之百的原创”,也是无法写就自己功泽万世、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巨著的。《音乐剧史记》在内容、体例、取材、史料运用、述史框架、纪传与传记文学上借鉴《史记》和美国其他音乐剧史专著,在篇章取名上则“拷贝” 艾瑟·默登(Ethan Mordden)的首创思路,正反映了学术研究过程中借鉴(或“传承”)的重要性。 任何学科的史学研究,永远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原创! 二、内容:传记而非通史 有了一个看起来很新颖的体例结构,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作者如何在这个体例统筹下进行具体资料和内容的建构和设计。 百老汇百余年来大师荟萃、名家辈出,历代经典作品更是经久不衰,让百老汇成为世界音乐剧事业发展的朝圣之地。马丁·高特弗雷德(Martin Gottfried)曾将百老汇创作历史上不同时期涌现的作曲家分为三类:巨星(Giant),他们制定了早期音乐剧的基本模式,形成了百老汇音乐剧创作的传统;大师(Master),他们是具有自己不同风格和特点的创作者,是音乐剧得以发展和繁荣的中坚力量;专家(Professional),他们一般都保持着传统的作曲-作词合作模式,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但他们的作品却代表了百老汇的最高水准。我们认为,作曲大师是如此,舞蹈编导、唱词作者、导演和制片人又何曾不可如此分类? 在《音乐剧史记》中,作者仿效司马迁《史记》体例,把著名制作人和导演归入“帝王”级别,以“本纪”记之;把杰出词曲创作者和剧作家、编舞家等归入“侯国”级别,以“世家”记之;把著名女演员归入“士大夫”级别,以“列传”记之。看看目录可知,属于帝王本纪的有歌舞大王齐格菲尔德、剧坛霸主罗宾斯、天王导演普林斯、金牌制作人麦金什;属于侯国世家的有美国戏剧音乐之父科恩、音乐剧场师爷小哈姆斯坦、祖师爷的传人桑坦和多栖才子佛斯;属于红伶列传的有摩根、米勒、布莱斯和塔克;摩曼、马汀;沃登、里薇拉;皮特斯、贝蒂露波(注意:这个译名非常色情,可以作为性幻想对象)和麦当娜。很难想象,仅仅结网并聚焦于这几个人物展开的百老汇音乐剧通史,将是多么残缺不全?又将如何让人信服?! 当然,音乐剧史上各类名家林立,高手如云,且不说超越,想要跻身其间确实是谈何容易。如何取舍?这对我们音乐剧史学者将是考验。 过去的事情既然已经成为过去式,历史学家就应该找到合适的支点,尽力客观地、全面地重建往事,求其近乎原貌。本书作者的动机非常明显,希望借用《史记》外壳,运用文学性较强的文笔,将本书写成音乐剧领域的《史记》,不仅具有纪传体体例,也希望直攀通史巅峰。这种写作手法未尝不可运用,但取样绝对不能以偏概全,如果只以区区几个“帝王将相”就可以概括一部音乐剧整体思潮,就能够描绘出百老汇的百年历史,那么,不仅人物众生不丰满,史料基础薄弱,而且论述闪烁,呼应游离,离目标的误差很大。犹如一颗参天大树,根不深、叶不茂,惨白无力! 柏林在哪里?格什温兄弟在哪里?波特在哪里?堂堂大名的罗杰斯在哪里?伯恩斯坦在哪里?韦伯又在哪里?史学致知必须广收资料,归纳史实,推演证据,以解释往事。如果只重形式而非内容,就不能做到中立以达超然客观之效,专著的价值也就将大打折扣。可以毫不过分地说,本书只是几个人栩栩如生的传记,远未呈现出百老汇音乐剧通史的风貌,甚至误导了百老汇百年历史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根据我对作者的了解,这不应该是作者的水平和风格! 历史绝对不是个人爱好,人们对史学求真求实的可能性,始终充满期待。 三、取材与史料运用:丰富但偏废 百老汇音乐剧史虽然时而真相难明,时而真伪莫辨,但较之其他学科,由于只有百年历程,仍然具有相当的真相可求;对于真相的探讨,即使做不到绝对客观,但至少应该合情合理、自圆其说。 既然作者已经把百年音乐剧史押宝在狭隘的几个人身上,那么,在收集资料和史料运用上,自然而然地会画地为牢,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进行音乐剧“纪传体”的自主解释和专业遐想。此时,即使摘取的资料再丰富多彩、文笔再生动无比,全书就必然会胸大腿短,四肢发育不良。 一部音乐剧百年史,如果只顾主流,无视支流,必将游魂难归,难见其全;如果把支流误作主流,甚至把历史人物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总体评论,则失之更大,从而让历史弯曲失衡,失去其应有的生命与本质。 司马迁修撰《史记》如果从一开始就缺乏整体章节规划,如果仅仅是历史材料毫无次序的堆积与分析,是完成不了一部伟大的著作的。尽管作者在自序中解释:在这本书中,哈氏只能屈居侯国地位,是因为只有当他与其他人(如罗杰斯)双剑合一时,才能成为德泽万物、风行草偃的万岁爷。我们很难想象,在这部看似百年通史的专著中,按今天的标准他是侯王,明天按另外的标准,就能跻身于帝王宝座,这成何体统?!按《史记》等级分类,作为作曲家,罗杰斯的影响力再大,也不可能荣跃“帝王”皇座,但问题是:没有罗杰斯的百老汇音乐剧通史,注定是破落不全的。而且,在音乐剧场“黄金年代”(1930’s—1960’s)里,作者将罗宾斯推向皇位统治百老汇30多年,看起来实在很有点“皇帝的新衣”。就影响力而言,在笔者眼里,罗宾斯在罗杰斯面前,整个就是穿开裆裤的小学生,只有洗耳恭听的份。 一代怪才佛斯身兼编舞大师和超级名导风采,是20世纪60—70年代百老汇的旗帜,佛斯舞步(the Moves of Bob Fosse)更是以其“Less is More”的风格名扬天下,巡演世界。 一个罗宾斯,一个佛斯,如果按导演成就来决定席位的话,尽管因为罗宾斯的成就开启了音乐剧历史上一个全新的“编舞兼导演时代”,但后者的独特性和巨大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1972年,他分获奥斯卡、托尼和艾美最佳导演奖,这是百老汇历史上任何一个导演也没有取得的成就,但他在《音乐剧史记》中远没有罗杰斯幸运,尤其是,大放异彩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佛斯,竟然莫名其妙地在80年代—2000年的年号下排为侯国世家。我要跳着佛斯舞步为佛斯大师鸣不公!问题是出在《史记》体例上,也许这部宏观视野的历史巨著体例根本就不适合于具体学科视野的百老汇音乐剧?还是出在作者写作观念上,也许作者本身就有自己的个人偏好?大家可以争议。 从书中看得出来,作者对“天王导演”普林斯推崇备至、顶礼膜拜,但并未全方位地展现其真相。《伙伴们》和《富丽秀》之后,普林斯与桑坦相继又推出《小夜曲》、《太平洋序曲》、《理发师陶德》以及《欢乐岁月》等具有鲜明艺术风格的概念音乐剧作品。只是,他们似乎过于关注音乐剧艺术本身的探索,而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大众的欣赏趣味,因而这些作品在票房上都不很成功,象《欢乐岁月》等甚至几乎就是商业上的彻底失败之作。普林斯一度失去了人们的信任,直到1986年,他紧紧抓住韦伯的《剧院魅影》这根稻草,才起死回生。科恩其实并不一直是音乐剧“革命家”。自《演艺船》之后,他没有像大家期望的那样发扬光大,而是在传统和未来之间飘摇不定。当然,尽管他后来创作的剧目大多描写浪漫的爱情故事,不少音乐看起来同剧情关联不大,但科恩凭借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还是将每一部剧中的音乐都打造得非常美妙。像《可爱的艾德琳》(陈书中译成《歌女阿德蕾》),由在《演艺船》中表现抢眼的海伦·摩根出任主演,科恩为之写出了像“我为何而生”(Why Was I Born?)这样的佳曲。音乐剧的星空也不是一概的女色,很多男演员有非常杰出的表现,可惜全部被湮没在女演员的大腿、露波和肥臀之下。 《音乐剧史记》一书从总体建构上来说,没有呈现出起码的完整与和谐,从史料收集和整理上看,也缺乏有条不紊、轻重缓急、提纲挈领之整合功力。作者采用了一种在华人看来还算是比较新的写史体例,试图围绕音乐剧大师进行历史阐述,但在内容、体例、取材、史料运用、述史框架的整合与互动上,明显缺乏圆熟的驾驭能力。看来,要纠正本书中明显存在的、在既定框架内收集和运用史料的短视与局限,是否需要推翻《史记》体例似的音乐剧历史编写法?在我看来,采用覆盖洋洋三千年中华历史的《史记》体例套写音乐剧百年史,很有故弄玄虚、杀鸡用宰牛刀之嫌,根基一点不扎实。这种新思路并不能完整地、有效地整合各类史料和资源,从而达成音乐剧通史的目的。这是问题,是作者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 记得炜智兄第一次对我说要用史记体例书写音乐剧史时,我当时感到非常新奇,同时十分担心设置什么本纪、世家、列传之后,容易堕入形式大于科学的泥沼。现在出现这么多重大遗漏,看来是必然的结果。虽然司马迁也有所变通,但是,该列入本纪、世家、列传的是什么人,人物的身份已是硬性的定势,套入即可。而音乐剧史的人物该怎么授予“职称”,怕不是那么容易套进的。硬要以史记体例谋篇,难免率性、轻佻。其实,二位陈君的著作,书名改为“史话”就会避免由于许多学术上的缺失引来的质疑,也可以免除读者的追究,就尽可去大说所涉人物事业之外的八卦甚至风流韵事。当然,若将此著视为“史话”,作者也许又不甘心了,因为他们一心想写的是“通史”、“史记”。看来,难得两全啊! 四、行文:诗情史意与写实叙事 笔者与本书作者陈炜智曾基于“Broadway Musical Play”思想,在新浪网发表“不是不好,而是不对”,对音乐剧《金沙》进行评论。我们之所以强调“经典音乐剧”,以及连带相关的一切美学标准,是因为它基本上是以“整合性的叙事”为基础,具有浓厚的写实叙事特色。音乐歌舞剧场就是某种程度的“总体剧场”,在剧场组成的每一元素、每一层面上,都能、也都“必需”传达意义。这个“意义”恰恰正是“叙事”这个词组中所指的“事”。“叙”的动词牵涉到一切技巧、手段、美学,而“事”的名词则包涵可能存在的故事、情节、具象的人物、角色、抽象的哲思、概念等等。 在《音乐剧史记》中,作者进一步介绍,并强化了写实叙事思想。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处。一处是介绍小哈姆斯坦的“存在的实体”(BEING),这个观念告诉人们:它潜藏在角色的内心和歌曲的深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进入这个存在实体的机关要道,唯有不欺不瞒、真诚以对,才能收敛起表演者的锋芒,把这个艺术的存在实体虔诚地展露在观众面前,所有的声乐技巧、明星气质和表演理论等等,都只是辅助表演者呈现这个存在实体的助力。还有一处是概念音乐剧大师桑坦介绍的“戏感”(theatricality):《西区故事》最珍贵的贡献就在于它的“戏感”,而罗宾斯是将“戏感”处理得最好的编舞和导演。他不仅以舞剧的方式处理音乐剧,严格控制每一个细致的动作,启发演员、鼓励演员运用他们的肢体语言,去传达编剧没有写出来的台词、作词者没有写出的歌词,去把那些无声的歌曲“唱给观众听”,而且,他善于运用戏剧导演的手法创作芭蕾,要求舞者去思考每个美丽动作背后的戏剧动机,每个王子公主人性底层的心理变化。他不仅在编舞之外,开拓了“不舞之舞”的场面调度手法,而且将稍纵即逝的“现场表演”这一抽象概念提升到能与白纸黑字写下的“戏剧文本”(包含脚本、乐谱、歌词等)平起平坐的地位。所以,罗宾斯的编舞和导演特重“戏剧感”,只要会让作品停滞不前,哪怕是再精彩的章节段落,他也会二话不说给与删除;一旦戏剧进展原地踏步,他就会想尽办法让剧情快速滚动。
【发表评论】
|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