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遭遇里的赛德克人(组图)
文/林易融
1895年台湾割予日本,赛德克人遭遇挟统治之力的日本人;还来不及全面理解日本文化,1945年国民政府来了,赛德克人又要瞬时渗入汉人文化;当赛德克人还在试图融入主流社会,本土化浪潮袭来了,告诉他们“你是赛德克人,不是泰雅人”。从日化、汉化、再到去泰雅之名,一百多年的光景,赛德克人不断遭遇着文化“更替”带来的不适应。
 《赛德克-巴莱》重现日本人进入雾社大街情景。
《赛德克-巴莱》重现日本人进入雾社大街情景。遭遇日本
“樱都”雾社(赛德克人祖居地)的二月,正是樱花乍开的季节,从埔里到雾社的迂回山路上,尽是蔓延的原生樱花树,花色灿烂。回看伊能嘉矩、鸟居龙藏、森丑之助等日本学者的研究手记,在一百一十年以前,他们竟未尝见过雾社春天伊始的樱花盛开,第一次踏入雾社时,他们承担着更沉重的任务。
日本殖民政府从大英帝国殖民政策的分析中,深知人类学研究对殖民政策制定的重要性,参照18世纪英国人的殖民手段,日本人对殖民的朝鲜及台湾展开人类学调查研究工程。1896年夏天,台湾割让予日本的翌年,日本人类学学者衔日本殖民政府之命,携带大小研究工具,背载笨重的玻璃底片,身着背心、腿缠绑腿、脚踩矿靴,多以徒步方式深入台湾山区,开始台湾本岛的田野调查。进行学术记录的同时,也学习原住民话语,协请原住民搬提行李,指引山路进入各部落。目的是为殖民台湾做准备。
首入雾社山区的是伊能嘉矩(1867-1925),他被称为“替台湾原住民进行族群分类”第一人,但其分类报告,并未见“赛德”之名。祖居雾社山区称呼自己“Seediq”的人们,因为黔面、出草等习俗,被伊能嘉矩归类在“泰雅族”名下的大分类,或称“纱绩族”。肇始伊能的分类,赛德克人被注记在日本殖民政府的户籍簿里,然后隐埋在泰雅名下,持续生活超过了一百年。
鸟居龙藏(1870-1953)在1900年夏天也进入雾社,他端出专业测量工具,对原住民仔细丈量身高、手脚大小、五官长短、牙齿数量,将温热的原住民面容,透过科学方法转列成一排冰冷数据。
森丑之助(1877-1926)将赛德克人的多彩外貌与生活环境,冲洗成了黑白照片。
赛德克人,对于远在两千两百多公里以外的东京人,可能只是鸟居书籍报告的铅化数字,或是定格在森丑之助的一祯祯黑白照片中那些不穿和服的番民。
 实行“理番”政策时,原住民手举起日本国旗
实行“理番”政策时,原住民手举起日本国旗日本殖民政府再利用原部落之间的生活摩擦,制定“以番制番”统治法;从部落中挑选要员,培养成“日本教育模范”;带领部落头目走访日本内地,参观现代化军事设施,以此些举措强化赛德克人的日本殖民教育。但对世居雾社的赛德克人来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文化是一股在清廷甲午战败以后,快速灌进赛德克部落的奔流,直到1930年发生冲突事件。事件以前,赛德克人和日本人相处得还算安好,甚被归类为亲日的“味方番”。莫那鲁道(Mona Rudo)也曾以马赫坡社头目参访东京和京都;事件中自杀的赛德克人花冈二郎(Dakis Nawi),更是殖民政府眼中接受日本教育的示范人物。
 日军总指挥官在雾社附近合影
日军总指挥官在雾社附近合影现今服务于雾社当地仁爱乡图书馆的蔡光吉(Bawan Nawi),五十二岁,赛德克人,是莫那鲁道的曾侄孙。关于八十年前的冲突事件,蔡光吉说,“那一直是部落父辈们不愿提起的悲惨往事。事件以后,他们被迫统一迁徙到川中岛,即今天的清流部落。由于日本殖民的高压政策,加上原有族人各部落的生活摩擦,出身马赫坡社的族人,怕再被迫害,从此断了根。亲历雾社事件的后人,移居川中岛后只剩老弱妇孺,心理上不愿再提起这件事,所以我们后人也了解的不多。虽然小时候曾听闻父亲提起,但再追问细节,他就不愿多说了,反而是出身春阳部落的母亲愿意讲得更多。”
蔡光吉称:“电影《赛德克-巴莱》的历史顾问郭明正(Dakis Pawan),是我的表哥,他找了我的姑妈及叔公进行口述历史,但是老人叙述的细节是否正确,我们却不得而知。电影终究只是电影,和历史事实毕竟有所出入,甚至夸张。”
 日军绘制的雾社战略地形图
日军绘制的雾社战略地形图邓相扬,埔里的客家人,是将赛德克人与日本殖民政府这段冲突进行历史再研究的重要民间学者,从小在埔里生活,多与原住民为邻,中台医专毕业,回到埔里经营医检所。在赛德克老人选择淡忘,政府也不鼓励地方文史研究的1980年代,邓相扬却对这段禁忌历史产生了很大兴趣。由于工作缘故,他接触的病人多是埔里或雾社当地的原住民朋友,直到事件中的重要人物花冈二郎的遗孀高山初子(Obin Tadao)前来看诊。
高裕明(Tado Nawi),三十一岁,高山初子的嫡孙,说起了这段祖母与邓医检师的相遇:“邓医检师的女儿和我是‘国小’的同学。和邓医检师的缘分,是源自我父亲(Awi Dakis,花冈初男,高光华)带我祖母去所做健康检查,他当时对于我祖母原住民的外表却带有日本人气质的举止感到好奇。在健康检查的过程中,邓医检师带着对原雾社事件的好奇,用日语大胆地询问起我祖母的身份,确知她是雾社事件的经历者。第一次的接触仅止于此,但医病关系的交流建立起更深刻的人情交往,才开始对我祖母进行雾社事件的访谈。邓医检师对于雾社事件的研究,多数相关资料都是从与我祖母的访谈中获知,并且开始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日军拍摄的雾社分室弹药仓库被抢场景
日军拍摄的雾社分室弹药仓库被抢场景和莫那鲁道后人蔡光吉(BawanNawi)一样,事件在高裕明家里,曾是不被提起的往事。“雾社事件这段历史在我们家是一段悲伤的故事,因为事件的残酷,加上事件以后被迫迁居到川中岛,必须重新再适应新的生活,原本的族人大量死去,许多活下来的族人也在迁移到川中岛后自杀了。在家里,长辈们不会主动跟我们说起这件事。离开雾社,多数人也不晓得这段惨烈的历史。记得我哥哥还曾闹过笑话,带着中学历史课本叙述黄花岗起义的内容,回家问我父亲‘爷爷是不是死在黄花岗?’因为家里从来不谈这件事,我们一无所知到以为‘黄花岗’和祖父的日本姓‘花冈’有关联。”
即使是亲历雾社事件历史的赛族后人,高裕明也和外界一样,通过外界数据才详细知道这段故事。“我也是通过外界对我祖母与父亲的访谈中,一点一滴去了解这段历史。我的祖母是当时春阳部落头目的女儿,祖父则是春阳部落某个较具势力的人的儿子,因为显赫背景,自然被日本人挑选来作为受日本教育的模范版本,和日本人想治理原住民先影响部落头目的政策有关。反倒是印象里,外界许多人常来家里找我祖母做访问,通过访问者寄来的书籍,才大概对这个历史事件有一个初步了解。到念高中,接触到历史课本里的雾社事件描写,才慢慢有更深入的了解,真正是到电影上映,才有更多人来询问。”
“记得外界对祖母进行访问时候,祖母诉说这些故事经常说到全身会发抖。当时她本人就在事件发生的公学校里,虽然穿着和服,可是族人知道她是高山初子,没有误杀她。可在现场她看到公学校校长被子弹打中脸,头部开花当场死亡的画面,对她来说是无法挥去的可怕画面。在她个人回忆录里写到第二次雾社事件,当时住在集中营的她,先接到日本人的提醒,要她前一晚不要在集中营过夜,祖母没有理会,又目睹了集中营被屠杀和火烧的事件,仓皇逃出被迫移居到川中岛后,生下我爸爸的过程中又遭受难产,后来确定我爸爸平安以后才感到一点平静,感觉没有辜负祖父花冈二郎的嘱咐,延续了下一代赛德克人的生命,而这也是她回忆录的结尾。”
浸入日本教育的高山初子,个人对殖民文化的先行融入,无法在族人与日本文化对遇的冲突过程中,提供有效的协调作用,她在事件后存活下来,但目睹冲突的发生,却成为心中一辈子的恐惧阴影。高裕明谈到祖母晚年接受日本学者采访,反而是后世的日本人有不同态度。“外界的人对祖母进行采访,一开始祖母也回绝,一方面是不愿再回想这个事件,另一方面是不认识采访者,对于外界想从她这里知道雾社事件始末的态度感到犹疑,甚至恐惧。记得后来的日本人在采访前都会先对我祖母说抱歉,表达以前的日本人让她有此人生遭遇的郑重歉意。”初子的赛德克身份渗入日本文化的结果,反而为自己在事件中带来困惑与无奈;同样有此遭遇的丈夫花冈二郎,也在身份认同和现实生活之间,面临囚徒般的两难,最后选择自杀为自己掷留下无声的响应。
 雾社公学校上课场景
雾社公学校上课场景赛德克人和日本殖民政府,双方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对遇过程中爆发血腥冲突,两边皆付出惨痛代价,众多曾经热爱生活的赛德克人,也许就此定格在人类学家森丑之助的镜头里。埔里镇上的邓相扬医检师对故事再找寻,唤起了赛族老人对此事的忆往;2011年的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令观众重新阅读这段发生在日治台湾时代的悲惨历史,理解赛德克人被迫在与异文化遭遇时,曾经面临的困惑与处境。
遭遇汉人
1945年夏天,日本在二次大战中承认战败,台湾重新回归中国。日本人前脚刚走,国民政府旋即而来,当赛德克人还来不及理解日本文化的时候,又再一次被动地以泰雅族的外名,遭遇国民政府的汉人政治文化。赛族的仁爱乡仁爱‘国小’孙秋雄(Basaw Boya)校长在谈及这段历史时说:“国民政府来了以后,直接给我们一个汉名,譬如我祖父姓孙,祖父的弟弟姓古,祖父的妹妹却姓张。这种情况导致下一代赛族人不知道自己的本源,甚至近亲结婚也不晓得。”
 赛德克妇女用特有的织布机织布
赛德克妇女用特有的织布机织布1980年代中期,台湾本土化意识抬头,这股浪潮也在台湾原住民身上激起涟漪,从恢复族名开始,要求台湾当局更重视原住民权益的声音四起。真正激发赛德克人进行正名运动,系因2003年7月时任台湾“行政院长”的游锡,在花莲县长补选为民进党候选人的造势场合上,竟以“行政院长”之姿允诺生活在花莲的德路固(道泽)(Sejiq Truku)以“太鲁阁”之名,获得法理上的独立名称。两个月后的9月,南投的赛德克人在埔里镇阿波罗大饭店成立“Tgdaya 、Toda 、Truku族名正名促进会”,是为赛德克正名运动的滥觞。2007年1月12日,埔里的赛德克族正名运动誓师大会上,汉语誓词代表的仁爱乡陈世光乡长,誓词表明“刻记我族起始源流,不因时代、社会及所处环境之变迁与转移,而所有遗忘与分歧。”2008年4月23日,赛德克人被台湾当局“承认”为第十四支台湾原住民。
 雾社地区施行“理番”,图为因“番通”政策改编的警察
雾社地区施行“理番”,图为因“番通”政策改编的警察纵使赛德克之名并不存在于日治学者伊能嘉矩的分类中,然则包含德路固(道泽)(Sejiq Truku)、德固达雅(Seediq Tgdaya)、都达(Sediq Toda)三大语群的赛德克人,在雾社生活超过三百年,是不争的事实。长久以来,赛德克人并不特别在意官方、法律、学术等方面对他们的分类,他们以自有的生活方式及习俗,认同这些共同生活习性的族人。赛族的孙秋雄校长认为“早期的赛德克人并没有什么族群的观念,‘族’有时候可能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侮称,例如台湾的布农族,本身也不是族的概念,也是人的概念,布农是指勇士之意。而我们赛德克人本身最重要的历史规范就是‘Gaya精神’,这是维系赛德克人的一个共同规范。另外,赛德克人重视分享,重视打猎,重视勇士的养成,成年的男孩子必须出部落去打猎,带猎物回部落跟族人分享,才能开始饮酒,没有完成打猎之前,不允许饮酒。这大概是赛德克人所谓共同的文化内涵。”赛族人在雾社事件以后,反遭日本殖民政府的武力报复,但赛德克人没有因此灭亡,赛德克人一直存在,一直以Gaya精神维系后来的赛德克人,一直以泰雅族的名字生活到21世纪。与汉人文化相遇以后的正名运动,毋宁说是一个去泰雅名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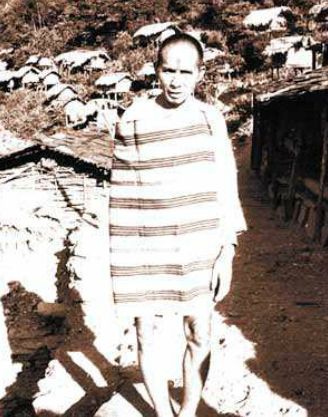 参与雾社事件人查任务的日本第八飞机所属的战斗机
参与雾社事件人查任务的日本第八飞机所属的战斗机蔡光吉称:“对于我的孩子,不会再细讲雾社事件,我只向他们传承一个血缘关系,我们家和莫那鲁道的血亲关系。雾社事件已经造成我们族人的几近灭亡,从我父亲那一代才开始重新萌芽,我们的使命是事件以后努力延续生命。事件的再提起,或许最严重者会造成革命,革命会造成再一次的灭族,那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国民政府以后,即使名称上称我们泰雅族,我们仍是教育孩子们,我们就是赛德克人,不管是名称上心灵上或认同上,我们就是赛德克人,始终存在。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和日本殖民文化的对遇,造成赛德克人几乎付出灭族的代价,事件以后,为了再生存,族人对血腥冲突的雾社事件选择淡忘。对他们来说,不忘记自己是赛德克人才是重要的。
 《赛德克》巴莱中的族人
《赛德克》巴莱中的族人重遇赛德克
早在2003年的正名运动以前,台北的政治大学民族系已于1997年开设赛德克语课,由Temi Nawi等赛德克人长期担任该课程教师。时至今日,赛德克语课仍挂在政大民族系的选修课表上,亦由赛人身份的Iban Nawi担当课程教学。随电影《赛德克-巴莱》热潮,赛德克语课明显受到政大学生的追捧,成为学校的热门选修课之一。
赛德克语被列入语言认证考试,早于赛德克之名获得法理上的地位。台湾官方以文化保存为宗旨,2001年实行“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旨在培养可具教学能力的原住民语言教师,也鼓励汉化了的原住民学习原住民语言。制度已有14族共42种原住民族语言的考试办法,赛德克语包含其中。
1996年开始,台湾小学生增加“乡土”课程,原住民语言及历史文化随乡土课程的排定,走入山区以原住民学童为主的小学教室。南投县仁爱乡春阳“国小”,即是目前全台湾唯一的赛德克语教学中心,学校规模不大,一个年级仅一班,全校一到六年级仅有六个班级,每班设有每周一堂40分钟的乡土课,进行赛德克语及赛德克文化的教学,赛德克牧师瓦旦-吉洛(Watan Diro),担当春阳“国小”全校乡土课程,他曾是推动赛德克正名运动的重要推手。春阳“国小”校长林取德,汉人,到春阳“国小”服务还不超过两年,校长名片印绘上赛德克图腾与樱花,表达这是一所赛德克人为主体的小学。林校长对于学校乡土课程充满期许:“春阳‘国小’全校都是赛德克小朋友,只有一位是汉人。所以全校是以赛德克族为教育主体,乡土课进行的是赛德克语教学,另外还有赛德克编织、赛德克歌谣的课程,课程授课教师都是赛德克人。据了解,多数小朋友们在家也已经没有说赛德克语的环境,族语教学的设置,希望从小培养赛德克小朋友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感。”
当代的赛德克小朋友,必须从学校教室里的乡土课程找回认同感。莫那鲁道纪念公园脚下的仁爱“国小”,是雾社另一所赛德克学童次多的部落小学。赛德克人的孙秋雄校长(Basaw Boya),回到雾社部落学校服务多年,赛德克人且长期从事小学教育工作的孙校长,对于赛德克学童的乡土课,有其看法:“我觉得在学校进行族语教学,不如把小孩子放回到小区或家庭里,母语就是从家庭开始养成。”
“当原住民孩子们,离开了山区,离开了部落,离开了家乡,去到汉人或客家人聚居的环境,来到以汉人或客家人为主体的学校求学,面对台湾学校的乡土课程,倘若校方没有聘请专门授课的原民语言教师,这些原住民孩子,必须服从多数学习闽南语或客家语,这是脱离原乡去到他乡的当代原住民孩子们,必须面临的现实求学情况。但身份永远存在,热淌的赛德克血缘不会突变,没有了赛德克语课,没有了系统性的课堂教学,赛德克的大人们如何在正名运动之后,让赛德克孩童再认识赛德克?赛德克孩童又怎么适应褪去泰雅外衣的赛德克身份?”
花冈二郎的嫡孙高裕明,一直在仁爱“国小”担任教师,目前是学校六年级的班主任,也是学校的教务组长。因为电影《赛德克-巴莱》,他的特殊身份再度被外界所好奇,雾社事件中历史人物的后人、赛德克人的“国小”教师,多重身份使高裕明老师对这部被台湾“广电总局”列为辅导级的电影,有自己的看法:他不避讳地说,“学校许多孩子已看过电影,也讨论过。未来若课程教学需要,他会利用课堂时间放映《赛德克-巴莱》做为教材,除了利用电影语言带领学童较快速进入历史事件的了解,其实也能借电影内容的优、缺点,建立赛德克学童们对历史事件的正确价值观,藉此提升赛德克孩童对身份的认同感。”
往日的赛德克人被迫日化、被迫汉化;正名后的赛德克人,在法理地位上改回名称,但新一代的赛德克人也面临新的文化认同问题。1896年以来的一百年间,赛德克人在政治身份上的几次转变,不断带给赛德克人文化“更替”的适应问题。82年前莫那鲁道与花冈二郎的处境,其实是台湾原住民和日本殖民政府共同面临的问题:日本殖民政府选择用人类学方式先行摸索;莫那鲁道与花冈二郎选择自我了结生命,将与日本殖民政府在文化遭遇的适应问题具体化。故事搬上大银幕,近日受到普遍关注与讨论,电影热潮也带给赛德克孩童自豪感。然而,其它也面临文化遭遇下适应问题的人呢?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下一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