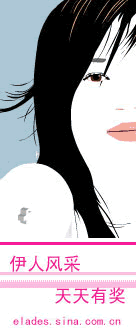《小武》剧照 《小武》剧照 作者:让·米歇尔·西蒙
译者:张献民
《小武》沿着一个边缘人足迹的当代中国之旅从一开始就显得非同寻常:画面有点脏,像是匆匆忙忙地偷拍下来的……然而很准确,也很别致。自从罗培尔托·布勒松的《扒手
》(Robert Bresson: Pickpocket 1960,这部中国导演的影片肯定部分地得益于这部作品)出现后,我们已经理知道:从一个陌生人的口袋里捞取钱财(不管是金币还是人民币)是一门精确细腻的手艺。从影片伊始,你就能感觉到在每一个镜头里都颤动着一种意外和变数的混合体,感觉到一种幽默——它照亮了这一整部虚构的纪实影片的忧伤调子。
小武,既是片名也是主人公的名字——是一个小偷,他回到了汾阳,这是中国北方山西省的一个小乡镇,街道单调,尘土飞扬……想来寻找异国情调的西方游客最好趁早离开:这里没有丝绸,没有小妾,也没有毛泽东时代的红色海洋——这里没有打着揭露的幌子来展览那些动人诱饵的任何东西。
小武故地重游——很可能是从某个管教场所刚刚回来,昔日的江湖同道现已金盆洗手,转而从事了更为有利可图的买卖——这个老朋友甚至不愿再见到小武,他成了阔佬,忙着为自己操办婚事,在当地电视台的摄像机的镜头前摆好了姿势——媒体机构对这个经济改革中蹿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的代表人物正竭尽吹捧之能事……
接下来是一段注定没有任何前途的爱遇,对象是一个在卡拉OK歌厅工作的风尘女子;然后是短暂地回到自己那个穷困的农民家庭,直至他被铐在了公安派出所的电视机前面——作为一个边缘人,小武的故事是一连串有关当下中国现状各种信息的曲折事件,是一次主人公的失望之旅,同时也是从边缘(既是社会的也是电影的)观察集体状况的精彩体现——但这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在这部影片里,浸透在每一场戏里的那种带笑的、温柔的,同时也是令人无法抗拒的情感张力。贾樟柯直到昨天还名不见经传,甚至不为那些既热爱中国又热爱电影的人们所知道,但他肯定是一个伟大的电影工作者,他的美学位置仿佛是介乎于皮亚接(Maurice Pialat)和早期的侯孝贤之间(这种组合有可能吗?):通过摄影机,他投向世界的目光像一束闪电,捕捉到了一种身体之间交流的气息——这种交流所讲述的与社会学和心理学表达同样关键却大相径庭。他的导演方法表面上看像粗糙的即兴报道,实际上却细致而有效:将主要角色包裹在不断贴近或疏离的运动关系中,充满活力地把人们最司空见惯的世俗情感戏剧化。
沮丧的内心矛盾或计时计费地在街头和发廊与歌厅小姐形影相随,或满怀柔情地看望病中的那个卖笑的女子——在令人不可思议的公共浴池里,小武实在的肉体在阴影中显现……声带中编织着各种街头的嘈杂声以及电视机或扩音器里发现的各类音响——各式各样缺乏品味的现代化次品充斥了我们的视觉和听觉(会演奏《致爱丽丝》的打火机大概能涵盖这种中国式的现代化),只能够以视听的彻底停顿和窒息来与之对位……一个个这样“无用”的细节最后构成了这一部有力感人、异乎寻常的影片。
高潮在最后的一场:警察(这个形象略带反讥:他左右为难,充满了沮丧的内心矛盾)把小武铐在街上让观众观看。360度的摇镜头将视角变为小武的——不仅仅是要把人物和影片从现实当中彻底解放出来,也不仅仅是要表明:调度效果的省略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并非由于无能——它产生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效果:过路人(即老百姓)在看小武,即在看我们(观众),当然实际上也就是在拍摄现场看着导演和摄影机——这个年轻的电影人用最简单的办法砸掉了任何艺术表现形式都难以逃脱的窥伺情结,就这么简单!——他扯下了烦人的面纱,揭开了导演深邃的奥秘,再没有人可以躲躲藏藏:权力暴露了出来,观众也暴露了出来。
关于《站台》的评价
《站台》是对中国十年激烈文化变革的一次深思。中国导演贾樟柯1998年在其成名作《小武》中所展现出来的天赋再次得到证实。肌理丰富的戏剧元素和各种文化景观的拼贴是《站台》的结构基础,再加上静止镜头内人物的从容调度可以看出贾樟柯具有老到的手法和收放自如地驾驭能力,并擅长诱导出演员们自然细腻的表演。这些特质极少能在只拍摄了两部影片的导演身上见到。
——David Rooney美国《综艺》
《站台》同一时间是含蓄的,又是狂放的,既铺张又出奇的简洁。
——Dennis Lim美国《村声》
准确的笔触,风格独特的创造,简洁以及纪录片式的精确,这部影片是一部真正的天才之作,它包含了如此丰富的信息,效果和充满激情的台词。
——Jean-Michel Frodon法国《世界报》
《站台》就好象那种厚厚的自传一样,在同一时间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自己周遭朋友的成长经历。《站台》是忧郁的但没有多愁善感,因为它简练的风格和长镜头内的各种鲜活的生活细节,没有让它如此多情。
——Louis Guichard法国《电视报》
《站台》
──漂流的中国青春
作者:Didier Peron法国《解放报》2001.8.29
译者:张献民今日中国导演贾樟柯的现象完全象昨日我们发现伊朗人阿巴斯·齐亚鲁斯塔米。二者都是边缘艺人,在电检高度敏感的体制中心工作,两者都尖锐而忧伤地关注其民族生存最日常的方面,拍摄乡村、外地,空间如织物抽丝后留下的缝隙,那里不象饱和的城市,在那里权力犹如苦涩走调的空洞。
《站台》,为何不如此下笔:这是部天才的影片。两个半小时不断让人吃惊,《小武》已然让我们惊讶,但里面的各元素在此俱皆延伸放大。结果是幅一整代坠落的全景、一小撮年轻人紧咬的牙关。时间是1979至1989。终点处,理想不在。
宣传《站台》的首场戏是文艺演出,“火车向着韶山跑”,毛泽东荣耀光环中的必备宣传节目。舞台上的演员排队坐在板凳上模仿穿越中国前进的火车头。剧团有少年人、青年人,当头的比他们也大不了多少,但具体体现着党的喉舌,宣告道德价值和文艺路线。明亮是个团里一员,沉默寡言,戴眼镜。小城汾阳地处山西,在北京的西南方向,并不先进,无事可做,但演出更落后于生活。明亮对演出不即不离。他周围的少男少女骚动、调情、灌酒,跟父母吵架、看电影、瞎逛、否定一切。
喇叭裤、烫头和流行音乐来到汾阳,明亮和他的同伴们好似捞到几根稻草,希望其中的世界应该比党规定的那个更广大一点。可是一觉醒来,党已经取消文艺团体的补贴,剧团私营化。承包的小团体更名为霹雳舞团,出发去巡演,直到内蒙古。他们本来以为是要挣脱无聊无谓的身边现实,却发现遥远的现实更加沉重,连舞台的光线也淹没泯灭。
很少有人能够如此清晰地在叙事和形式上展现完全被历史发展超越的懵懂人群。个人只是群体热情的一份子,而有一天这个群体经由脱离社会的孤独之后遭受可怕的封喉,连遮掩贫困的作用都丧失了。我们从不知道那些人物之所思所愿,或许因为人物自己对自己是陌生人。命运高高在上、起伏不定,它定下的法则,完全超越人物们的理解能力。他们向前逃,而又不断发现只是在原地打转。很象卡夫卡式的人物跑到中国去的遭遇。所有一切都来得太匆忙,而又太缓慢;模仿外来时尚脱不掉笨拙土气,古老城墙既新又旧,远足开的是拖拉机,演员坐在车斗里,以为要去快乐的远方,结果比如只是到警察那里呆会儿,就又回到出发点。儿女们跟父辈吵架还没吵够,自己就已经造出了1979年法律规定的独生子女。
荒诞堆砌在一起的有纪录片元素,风景,肖像,传闻,记忆。永远晕头转向地游弋于私人与历史两个空间。扔给观众一大堆人性,又展现体制绕梁三日、恐惧坚如磐石、荒诞挥之不去、信仰细过游丝。如同历史学家艾力克?豪伯斯邦在他的《极端时代》中所写的,“从根本上说,以前共产主义信仰的工具性在于现时的价值只存在于它是达到无限远未来的手段。”《站台》眺望无限远,直看到天尽头。
但该影片的力量仍跨越边界冲击我们的胸膛。那些年轻人由于摄影机总离他们不近而显得如此藐小,持续的低噪音在声道的纵横迷宫中挖掘地沟,尘土飞扬的国度中,玩具过剩而愿望失落,周六夜晚的狂热一到第二天就变成酸涩的调子,这一切于我们又何尝陌生?虽然原来并不知道,我们身上可能也有点中国味道……
 动感短信、闪烁图片,让您的手机个性飞扬! 动感短信、闪烁图片,让您的手机个性飞扬!
短信世界杯站:新闻、游戏、动感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