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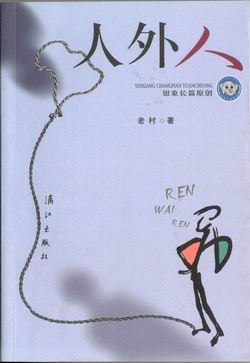 《人外人》封面 《人外人》封面
93年曾因出版《骚土》而被冠为“以写性见长的黄色作家”的老村,在9年后的今天,推出一部27万字的新书《人外人》。
十年前,从青海来到京城、36岁的陕西籍作家老村,带着他一部耗时3年多完成的小说,开始在北京出版界寻找主顾。其实早在90年冬天,他就开始委托在北京的亲戚,艰难地联系《骚土》的出版事宜。
为了这部凝结了20年心血的长篇处女作,也为了在陌生的城市推销自己。默默无闻、无依无靠的老村,在京城文学界所遭受的冷遇不难设想。或许他生不逢时,或许尚缺乏名气,小说出版最不景气年月里,老村徒劳地在凛冽的寒风中跑过六、七家大出版社,最终无功而返。
然而他没有气馁,经过三年的蹉跎后,一个书商出现了。书生气的老村乐观地将书稿交付给来人,但拿到印刷的《骚土》时,老村惊讶地发现:从不堪入目的封面设计到耸人听闻的广告用语,被残肢的《骚土》都已经沦为一个不入流的地摊文学。
当夜两点,老村逐字逐句地审读着《骚土》,彻底读完他发现:精心构思的章节和含蓄精彩的语言被颠覆和阉割,甚至被不顾及章节的连贯,删去近两万字,且错别字无数。二十年为之奋斗的理想,顿时灰飞烟灭。自己犹如被强暴的少女,欲哭无泪,只能在黑夜里默默吞咽着被作践后的耻辱。
正当自己蒙受羞辱、承受着巨大舆论压力的时候,街面的书摊上却有数十万册的盗版《骚土》在公开销售。不法书商和盗版者在一刀刀地剜着原作者的肉,他们用残缺本的缺陷,天天在往他委屈的脸上抹黑。
不过,老村一直都在理直气壮地申辩:我没有错。《骚土》既非淫书,也非格调不高。我写得非常严肃,非常真诚,为此,我敢正视一切评判。
此后的十年,尽管老村一直背着骂名,但没有间断艰苦的写作。并以每年一册的速度接连推出了《嫽人》、《鹫王》、《畸人》、《一个作家的德行》、《我歌我吻》、《生命的影子》等多部长篇作品。
老村原名蔡通海,陕西澄城人。务农期间驾农车、守磨坊、看西瓜、卖红薯,后来当过短期水利绘图员、工地战报编辑和生产队会计。17岁从军青海十载,从战士到打字员,后考入大学,毕业后回部队。转业后,在西宁市电视台做了7年的编导。
在部队当打字员那年的秋天,21岁的蔡通海在《青海湖》杂志发表第一篇小说《一片金黄》。几年后,在青海师专上大学时,又发表了第二篇小说《虫灾》。
毕业后回到部队,留在军区政治部文化处工作。但因一篇散文体的小说《月光是朦胧的》,却在极左思潮的年代里遭到批判。军区政治部主任拿着批判的文章在会上反问道:“这样的人怎能在政治部里工作?!”于是,他被赶出军区机关,发配到距西宁500公里外人烟稀少的祁连县武装部。
在海拔四千五百多米的冰封雪山中,一年之后,蔡通海才慢慢适应了单人独处的日子。终日茕茕孑立,只能用读书排解孤独。每逢星期天,都是他上街购书的日子。因为没有书架,书就靠着墙往上摞,后来足足占了大半堵墙。这些书伴陪着他度过了难忘的时光,有些名著读了不止一遍。
在祁连山的日子单调和苦涩,但也很充实。上午写作,下午读书。这是老村一生中读书重要的时期,两年多的苦读非常必要。在无人理会或无人可以理会的处境里,读书才开始品出了滋味。似乎自此他才学会了阅读,学会了真真切切地去感受书的内容,去品味作者的独到之处和微妙之处。
这时期他又开始写诗、读诗。比如艾略特的《荒原》、瓦雷里的《水仙辞》以及一些古典主义的诗人,比如泰戈尔、济慈、雪莱等等的作品,他还深深地喜爱法国作家加缪的小说《局外人》。有这些优秀的作品伴随,他感到“一种更深沉、更寂寥的陷入和畅想,在等待着我。”
对于一个欲以写作为业的人来说,相对一段时期的凄凄惨惨的孤独的生活体验是很有必要的。老村认为:当作家,是拿自己的整个生命来与上帝打赌,同时又经常会被时代虐待的一个职业。是与生俱来的苦役,是找不着码头的航行和没有伴侣的孤旅。
在大城市里生活的人总以为:人处在优美的自然里,能常与大自然交流是幸福的。可实际不然,两天后你就会感到压抑。特别是处在杳无人迹的环境里,与农家的田野或富人的花园里的感觉截然不同。所以,与原始、洪荒的自然对话,是需要一颗硕大的心和坚韧的神经。这个时候,蔡通海特别喜欢上法国的兰波和美国的塞林格,因为这也是两颗自我放逐的灵魂。
几乎每天傍晚,他会持一根木棍独自去山野或是河谷里散步,仰望着雪山林海,沿着河谷走得很远很远,年轻的士兵在行走的过程中,默诵着普希金或者莱蒙托夫的优美诗句。
两年后,回省军区教导队去报到。这时他蓦然发现:在山里真是孤陋寡闻,这几年里,前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南美大陆的马尔克斯以及美国的塞林格在文学界大为风行,整整影响了一代中青年作家!
92年,老村一家“很幸运的靠调动进了北京”。从西宁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又在北京必须忍受着诸如风来雨去以至于流离失所的苦日子。相当长的时间内,在老村的心里都无法与这个文化中心的首都产生共鸣。他看不惯京城那些“抬轿子文学和文人”,他也从心理拒斥那座“违反人类自由精神”、威严庞大的紫禁城。
贫瘠、遥远却生他养他的黄土地,一直在他心底里召唤。他的声音来自备受屈辱的黄土高原,时刻思念家乡,每每都会强烈地感受到土地的嘱托。真实地揭示出黄土地那种生存状态,用一种属于自己声音的真实来表达,将个人经历的历史原貌和真情实景还原给历史,将自己屈辱的人生经历融入到对多难民族的文学记述里。这就是他的使命。
进京两年多的艰难求职终归无望,老村最后选择了坐家卖文为生。假如当初不离开青海,现在很可能已经混个军队宣传处的处长或电视台的部门主任。但他没后悔,放弃世俗的累赘,他选择了有尊严地自由写作的道路。
虽然《骚土》被强暴或阉割,但其文学价值依然不能抹杀。更多客观地评论认为:“老村是用《骚土》完成了中国黄土地的文学抽象。”、“《骚土》的出现,标志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家们在叙述传承上没有失职。”、“没有《骚土》,中国一个世纪的文学将存在重大缺陷。”
而今天,老村的新作《人外人》则是对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农民进行一个全景式的艺术概括。多年来,这一作品仅限构思,一直没付诸笔端。一年前,老村回陕西老家,面对被旱魃苦苦折磨的父老乡亲,痛苦像锥子一样,刺透老村敏感而又善良的心。
他深深地愧疚,愧疚得恨不能给乡亲们下跪。这愧疚同时也唤起了他文人的勇气和良知。他带着这种愧疚回京,以巨大的悲悯心怀奋笔疾书。
一年后,《人外人》完成。27万字里,倾注了老村对土地的一腔挚爱和对历史和人生的深切领悟,他的爱和恨,他的宽厚和包容,全都融汇其中。《人外人》提示人们,经典的思想,必须体现对人类问题的终极关怀。主人公阿盛带给我们的正是如此,即关于活着的思考——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到底该怎样活着?这无疑具有永恒的意义。
仅从文学的角度上看,与昔日的《骚土》相比,《人外人》也显露了老村创作上跨越的足迹。他不仅洗掉了《骚土》让人似懂非懂的陕西土语,而且在流畅精确上显现了非同凡俗的功力。
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一部《人外人》,翻开了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崭新一页,让以往以直接记史叙事式的写作观念成为过去。它极大地调动起写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以更为抽象和夸张的方式直逼历史事件及其人物的精神内核,使写作者在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上真正实现了创造和超越的可能。
总之,《人外人》的文学成就,足以使老村彻底洗刷昔日蒙受的巨大羞辱。
老村目前居住在马甸桥南侧,熙熙攘攘的各种车辆川流不息。夏日倘若打开门窗,噪音轰鸣顿时倾泻进来。因此,他的起居作息时刻表就是每日凌晨3点即开始写作。拂晓6点关机休息。
虽然缺乏安静的创作环境,但老村心灵却感到愉快和轻松,因为现在终于能够有尊严地自由写作!而可以真实而自由地生活与工作,难道不是一个作家所追求的最理想的状态吗?(伊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