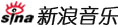|
|
罗大佑:人一定不能忘本 现在我想有个孩子
罗大佑: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会写中国字是很严重的,比西方人不会写ABC更严重。西方人只要认识26个字母,但中国字很多,象形文字嘛。你要是连象形文字都不会写,这个文化就很危险,就没有认同感了。我一直觉得认同感很重要的。日本的没落我相信跟这个国家的脱亚入欧有关系。日本到1980年代的时候,经济全世界第一,可是你看现在就不行了。虽然日本这个国家很干净,日本人做事情很有效率,可是你会觉得这个国家缺少了一个东西,少了一个根本,所以亚洲人都不喜欢日本,欧洲人也很奇怪,你日本人怎么会觉得自己是欧洲人呢?成了四不像了。所以说,人一定不能忘本。
人物周刊:你觉得对你这一代台湾人来说,你们的本是什么?
罗大佑:我觉得不管台湾人怎么样了,跟中国必定还是有关系的。就算是原住民,跟中国人在血缘上、地域上都是有关系的。你不能硬把它切开。在台湾做那些去中国化的事情,是很愚蠢的,你还是用筷子吃饭的嘛,除非你硬要训练所有人都用刀叉吃饭,但是这可能吗?
我觉得认同,不管是怎样的感觉,都是一种普世价值。人毕竟是情感的动物。我想我们认同的都是一种不具有大的破坏性的价值,一种有安全感的自由的价值,就像罗斯福讲的,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人的权利。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有很深的不安全感?
罗大佑:1985年非洲饥荒的时候,要求支援非洲的,全部都是艺术家。你看艺术,讲的都是人心里面追求的love,人类的爱、和平共处,所以他们最反对的就是破坏者。破坏者就是战争、饥荒、疾病、政治迫害等等。
琢磨上海,研究广州
人物周刊:后来你又去了上海,你觉得上海怎么样?
罗大佑:我觉得在北京、上海、香港和台北4个城市里,最相同的两个是上海跟香港,所以会有一个银行叫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嘛。(大笑)这两个城市太像了,汇聚了很多丰富的东西。大家都不啰嗦,追求利益,精打细算,然后,追求最update的一些东西,从fashion,到news,到information,到股市什么的,CNN最近播什么,YouTube里面最新流行的视频。大家都知道金钱的价值很重要,这是很现实的,金钱不是第一的,但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人物周刊:你不断地换地方生活,是为了体验,还是为了寻找一个对你来说比较有安定感的地方?
罗大佑:可能也是一种好奇心吧。1997之后,内地在很多方面帮到香港,同时香港也带给内地一些新的东西。短短10年之间,那种全球化的速度,让人感觉中国并没有在世界之外。这十几年里中国的变化,比从1997追溯到1901年的变化都大,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香港这个窗口是多么厉害。
还有广州,广州以前是扮演香港现在的地位。我去每个地方做演唱会之前,都会做一些study。我发现,广州有全中国第一个做枪炮的实验室,近代以来,很多最先进、最革命性的东西都是从这里开始。所以说,广州的开放要比上海悠久,上海开埠大概就两百年时间,广州大概600年前就开始了。我发现一些英文词汇的引进,是从粤语开始的,像我们把英语的John叫做约翰,用广州话来读,就很接近英语的发音,用国语的发音不像的。用国语将Peter读成彼得,Paul读成保罗,Mary读成玛丽,都是这样的。
新世纪来势汹汹
人物周刊: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你经常提到新世纪,现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已经快过去了,觉得新世纪有什么不同?
罗大佑:新世纪来势汹汹,来势汹汹啊。我觉得新世纪最不同的,是科技的泛滥。从1990年代,开始感觉到电脑的厉害,到21世纪,电脑更厉害,IT的普遍性更可怕,网络的普遍性更可怕,从google一直到YouTube再到facebook,越来越多,很多东西变得越来越空。
我觉得现在人类好像已经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共识会越来越多。所有的媒介和科技都在改变人的观感。以前查一个资料,要辛辛苦苦打很多电话,上图书馆才能查到,现在上网一输入关键词,哗啦啦都是信息,到了你看不完的地步。这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我们都面临一个太多的问题,而不是太少的问题,这很可怕。这是第一个共识。
第二个共识,每个人都觉得钱不够,但是又没有大问题出现。虽然金融危机来势汹汹,但媒体和科技的发达,快速有效地警告了所有人,大家也很有准备地慢慢调到相应的水准,不会像以前一样,一下子就跳楼的,一下子就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的。
现在看起来,姓“社”的想姓“资”,姓“资”的想姓“社”,美国现在就是特别想姓“社”的感觉嘛。这好像跟当初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特别吻合,很和谐嘛。所以说,现在在香港待得挺好的,香港不就是一个姓“资”又姓“社”的地方嘛,所以我们在这里都很幸福,很合乎世界潮流。(大笑)
人物周刊:你好像对科技的东西比较警惕。
罗大佑:我很小心科技,因为我做过香港第一个48轨录音室,我知道科技的力量大到什么地步,比如说速度越快的车,产生的车祸就越可怕。越是高科技的东西,出问题的时候,越严重。这种东西一定要小心。音乐方面,MIDI太强大了,很可怕。还是得回到人自身。
人物周刊:你有点反现代化吗?
罗大佑:我不是反现代化,我觉得现代化的东西要接触,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之后,就要回来,去寻找人跟科技之间的平衡。人跟科技跟大自然跟这个世界,要永远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里。
现在我想有个孩子
人物周刊:你是客家人,这样四处跑,跟你的客家人身份好像比较相符。
罗大佑:血缘大概是有点关系的,我父亲也是一样,从台北跑到苗栗又跑到高雄。
人物周刊:你的《昨日遗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小时候,全家人都不善于向彼此表达感情”,这对你有影响吗?
罗大佑:可能有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不太会表达,就要放到音乐里来表达。
人物周刊:你父亲的去世对你打击很大?
罗大佑:很大,非常大。不过另外一方面讲,我父亲去世后,我就变得越来越自己了,重新开始扮演自己。
人物周刊:你在《锵锵三人行》里说的第二人生,就是这个概念?
罗大佑:对对对,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人物周刊:第二人生是怎样的概念?
罗大佑:一般人来讲,从父母生你,到走进社会,到有了自己的家庭,第二人生就是有了小孩以后。但是我没有小孩子,我现在是想生个小孩子,以前觉得会束缚自己,可能是现在年纪大了。自从父亲过世以后,觉得好像是他的生命延续到我的生命里,我也想把我的生命再循环下去。
人物周刊 :《昨日遗书》里也说到母亲,“上学第一天在教室从头哭到尾,因为妈妈不见了”,“更想回到她的体内”,这算是一种恋母情结吧?
罗大佑:这个东西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你从生下来,一直到上学,都是妈妈在照顾,突然到了一个群居的地方叫学校,旁边都是你没看过的人,有个新的人叫老师,这个角色一时还没办法接受,哭了好几天。
人物周刊:后来你母亲中风了。
网友评论
更多关于 罗大佑 的新闻
- 罗大佑对纵贯线有信心:我们要老少通吃(图) 2009-03-12 05:11
- 罗大佑:建议歌词也学电影分级 2009-03-11 04:30
- 纵贯线出席研讨会 罗大佑聊过瘾张震岳犯困(图) 2009-03-10 10:24
- 罗大佑:经济危机是流行音乐的机遇(图) 2009-03-10 00:40
- 罗大佑放豪言:每次我发片,股市就变红(图) 2009-03-03 13:20
- 罗大佑携“纵贯线”5月来渝开唱 2009-02-10 10:35
- “纵贯线”抵京 罗大佑表示自己很紧张(图) 2009-01-25 09:47
- 李宗盛罗大佑组乐队 向张震岳请教追女招数(图) 2009-01-22 10:52
- 央视春晚再毙三节目 为周杰伦罗大佑让路(图) 2009-01-20 0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