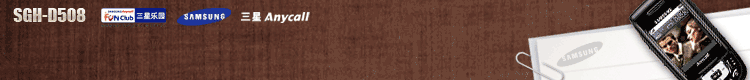这是一出残酷又温暖的奇异的都市爱情戏。
袁泉扮演的小优失去了心爱的男友,爱人的心脏被移植到刘烨扮演的高辕的体内。为着追寻爱人的心跳,小优慢慢接近花花公子似的高辕。尽管高辕的浪荡与玩世不恭与小优的爱人截然不同,但她还是为了听到爱人的心跳而爱上了高辕,于是上演了一个纯情而疯狂的少女折磨风流唐璜的、让人揪心的爱情故事。
话剧《琥珀》从香港演到上海,再回北京,这是导演孟京辉和廖一梅二次携手,它依然不改孟式“先锋”的面孔,更是拉着另一个票房招牌 刘烨和袁泉加盟主演。把先前只有文艺青年喜欢的“先锋”彻底大众化了。
似乎还只有戏剧能将人提到一个另类的维度。
《琥珀》应该是未来爱情的预演,一个老实人的心脏被植入到一个“唐璜”的身上,这是现代科技对爱情开的玩笑,一个纯情少女追随爱人的心跳扑到了唐璜的胸口上,她管这个叫“菊花之约”。这又是古典爱情对现代爱情开的玩笑。循规蹈矩的人会让花花公子的脾气性格由此改变吗?陌生胸膛的气息会否感染苦恋女孩,而使她移情别恋呢?
这样世俗的问题在一出标榜先锋的话剧里其实不需要明确的答案,编导却作了回答,但还是有许多人说看不懂,这就成了问题。
让唐璜来做身体写作的幕后策划人,使他连接起纯情少女小优和滥情少女姚的两个极端,可能是《琥珀》在戏剧结构上的得意之笔。然而其效果也正如剧中那句台词,“纯情和滥情一样都是故作姿态”。直到剧终,见袁泉趴在植物人刘烨身上唤醒了他,才看明白女性编剧着意于单纯的幻想 男人最终将被女人拯救,类似于现代的培尔·金特回到索尔维格身边。
但这样的企图却被嫁接到肮脏不堪的文坛和作秀高手的嚣张里。孟氏对畅销书流程的抨击我们是不必嗔怪的,在从前,凡是主流经典的玩意都逃不脱他的戏仿和揶揄,大众流行文化的热点后来成了他火力的重心,尤其是当《恋爱的犀牛》大受欢迎之后。
我所怀疑的是编剧廖一梅的态度,作为孟京辉的妻子,这位才女的力量是从丈夫的盛名之下渐渐浮出的,《犀牛》成就了他们的夫妻档,《犀牛》也是编剧的孟京辉和导演的孟京辉各自完成自我表达又渗透对方的作品,但是这种互渗在《琥珀》中现出断裂之迹,最明显的莫过于作为处在与美女作家同种生存空间,且创作文本在取材上难免相似的廖一梅,怎么去看待自己的同行藉文学对身体的表达呢?那些被是非之争所掩盖的情感,它们的真实鲜为人知,却是我们最想了解的,而且也许它最适合通过戏剧的方式来呈现,可惜廖一梅放弃了这钟努力。
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个经过美容处理后的年轻漂亮女孩为成名的欲望所驱使站到舞台中央,掀开裙裾企求男人给它方向,于是女作家姚小姐曝得大名就因为她拜会了一个风流倜傥的文坛男骗子被指点迷津而得,这无非再次印证了在男性为主体的社会里,女人的成功仍不过是用新的pose来赢得男人的欢心,只是这种pose 需要女人具备更多的才艺。应该说,美女作家为了成名不择任何手段这十分符合大众对她们的想象,孟京辉导演也是因为替大众代言而受拥戴,但这样的立场由廖一梅给出却不免太“酷”了。
相反的情况也发生了,廖一梅在剧终似乎对男权狠狠报复了一把,让袁泉收回了浪子刘烨的心,两人相拥而欲成眷属状。不管孟京辉如何处理,这样的景观依旧脱不了大团圆的俗套,放在我们所迷恋的“愤青”孟京辉之系列中就显得怪怪的。
然而,在中产阶级光顾的保利剧院里,这样的脉络和结局似乎又是一种必然。才华横溢的编剧和导演被观众首肯为黄金搭档,他们在被期待的同时将自己锻造为多元,小心维护影迷的心思,使他们的女偶像依然纯真而神秘;使男偶像一改往日情怀而大肆放纵却令人更加着迷。由此你不得不承认,大众的品位对于当代艺术实在是太具诱导性了。
以上这些也许可称为裂痕,但就《琥珀》来说依然是好看的。缀满空调外挂机的高楼缩影,城市青年绚丽而奔放的装束,姚妖妖的红色头发和丝质裙,袁泉“大而空洞到虚无的眼睛”,刘烨领带系得很松、围巾拖地的颓废做派,台湾音乐人的撼然心动的节奏,金星式的与椅子、床等缠绕在一起的暗示性舞蹈,这些感性张扬的形式构成了带重金属质感的舞台景观,是我们这个城市最有鲜活一隅的生态写照,当然也是我们所需要的高级精神快餐。(文/颜榴 作者为国家话剧院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