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五年祭:永远处在远景的观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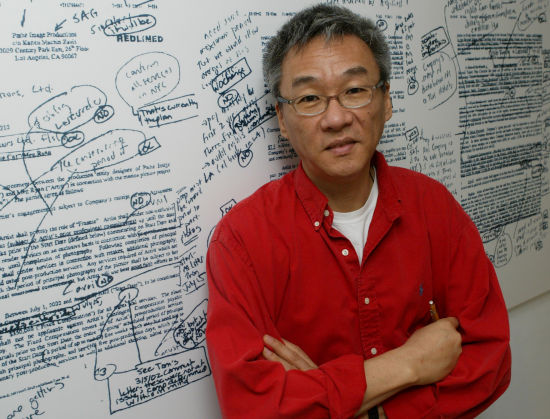 杨德昌
杨德昌
 年轻的杨德昌
年轻的杨德昌
早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当年杨德昌的电影伙伴、诗人兼导演鸿鸿,重温了杨德昌几部重要电影《恐怖分子》、《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下称《牯岭街》)、《独立时代》等作品的幕后故事。在走近杨德昌的电影世界,重新拼贴他的人格面貌的同时,也希望还原当年新电影运动那份最珍贵的哲思。
资料视频:网友自制短片纪念杨德昌 媒体来源:新浪播客 演员演得好的时候,他想跪下亲他的脚指头
东方早报:你当时在《恐怖分子》剧组担任什么角色?
鸿鸿:《恐怖分子》是“中影”制作的,但“中影”的人很不靠谱,导演组就必须出手去救火,道具组、美工组或制片组需要帮忙,我们就去打杂。我很多时候跟着制片组东奔西跑,找东西、找道具、勘景,甚至买便当。
东方早报:《恐怖分子》里有很多剧场的演员,听说当时杨德昌非常欣赏女主角缪骞人的表演,觉得自然而有层次,认为剧场演员的表演有一些过火。现在回头再来看他的判断是否准确?
鸿鸿:现在再看,觉得除顾宝明非常自然,其他两位都难免有点尴尬,尤其是男主角李立群(微博)。杨导对他的表现非常不满意,每天拍完都愁眉苦脸,甚至私下冷嘲热讽。剪辑时最大的乐趣就是拿他的表演开玩笑。我当时觉得(杨导)怎么那么刻薄,现在再看,觉得的确是有这个问题,他(李立群)无时无刻不在力求表现,但是这个电影的内敛和压抑决定你不能这样表现。有一场李立群坐在一边,镜头环绕着他,他要哭,又哭不出来,就点眼药水,杨导就很不高兴,觉得很假,情绪调动不起来。我觉得李立群也不太开心,认为导演不太跟他沟通,他摸不到门路,不知道导演要的是什么。杨导后来就有点怪罪赖声川(微博)介绍给他这些剧场的演员。
选择缪骞人是因为杨导以前看过她的电影,当时编导顾问陈国富专门料理她在台湾的生活起居、沟通表演。所以缪骞人的表现非常自然,她在片场讲的是广东话,国语是后来萧艾配的。
东方早报:他曾有一部戏拍了一半换演员的经历,如何能忍受一个演员整部戏的表演都不满意?为什么没有换掉他?
鸿鸿:因为没人可换。那时他认识的人也不多,这些新电影的导演都不想用电视演员和既有的电影演员,觉得他们的表演太机械化太刻板,所以他们就会从街上找素人演员,比如侯孝贤找了辛树芬。但是杨导对表演又有要求,这种街上找来的演员没法满足他的要求,他需要有一定技巧但又不僵硬的表演。这部戏他是听了赖声川的话用了剧场演员,他也一直在看剧场,他觉得这些人是可信的。
东方早报:他会赞美演员吗?
鸿鸿:会。他甚至和我说过,当一个演员演得很好时,他真想跪下来亲他/她的脚指头,很难想象吧。(笑)
《恐怖分子》有一场,李立群和缪骞人在桌前对话,现在看到的是缪骞人的独白,他其实拍了李立群的整个反应镜头,而且让缪骞人再演一遍专拍李立群。但后来李立群的部分完全没有用,因为他觉得就看这个女人从头讲到尾已经足够。这样的经历让他在以后拍片的时候喜欢一镜到底,不去打断。
曾经想要改拍《色·戒》
东方早报:在拍《恐怖分子》时期他有提出过要改拍《色·戒》吗?
鸿鸿:有,其实那几个计划一直在同时进行。杨导脑中有很多计划,他手头通常有两三个剧本。《恐怖分子》的时候他已经在计划《牯岭街》,在拍《牯岭街》的时候《想起了你》已经写好,后来变成了《独立时代》。我当时已经帮杨导写了一个完整的剧情大纲,叫《暗杀》(就是《色·戒》),他还让Tony Ryan把这个大纲翻成英文用来筹资,想找林青霞(微博)来演。当时他也找过张曼玉,我都已经帮他联系好了,但是后来因为沟通上的不愉快,没谈成。
东方早报:当时的大纲和后来李安拍的《色|戒》偏重点会不一样吗?
鸿鸿:杨导关心的是时代(背景),故事里有更多曲折。现在的《色|戒》我自己非常喜欢,但我觉得杨导肯定不喜欢,因为男女主角之间暧昧和挣扎的关系在杨导看来太简单了,他会觉得应该有更多转折。杨导的电影最重要的就是这些转折,每一场都会转,有时在场与场之间,在你没留意的地方转折已经发生了。他感兴趣的是人因为环境的影响会发生怎样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又会牵动其他的变化。
东方早报:李安版本的《色|戒》中的床戏引起过不小的话题,而原著小说里是没有这么具体的描写的,当时你和杨德昌的合作版本里面有大量的性爱描写吗?
鸿鸿:没有,杨导不爱拍床戏,可能是因为他个性比较腼腆(笑)。他所有的床戏都是空场带过,印象中他应该没拍过床戏。有拍过比较激情的戏比如《独立时代》里小明和molly在巷子里的一场戏,但是他镜头都吊得很远。
剧本创作 更关心人物的真实性
东方早报:听说杨德昌在拍《恐怖分子》时压力很大,常常半夜找小野出来看剧本。
鸿鸿:没错,小野之后我就充当了这个角色。《牯岭街》的时候他就找我看剧本,待了4个小时也没谈剧本,谈你最近看什么电影啊干什么啊,快要谈到剧本他又不谈了。《独立时代》的时候他养了一帮人在公司里,又不做相关工作。我觉得他是需要安全感,需要一群人在他身边。最终剧本都是他想出来的,他只是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对象进行对话。
东方早报:当时的合作模式是每人分场景写,还是一起写?
鸿鸿:我们都是坐在一起讨论。牯岭街我写的第一稿,即剧本架构弄好,人物设计好,然后去写对白。但其实所有的对白杨德昌后来都重新写过。杨导的习惯是一直到最后关头才会出手,不到最后他就一直在思考有没有更好的表现方式。这也是他的电影语言让观众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因为他不直接讲故事,总要迂回一下,让观众觉得更有意思,想得更多。
东方早报:《牯岭街》的剧本总共几稿?
鸿鸿:至少是三稿。第一稿是我写的,第二稿是堪完景杨导改的,第三稿是顺子(杨顺清)修改的。
比如最后台风夜报仇那场戏,第一稿的时候一开始没有台风夜,我写的时候只关注事件,没有考虑太多空间和时代因素。我第一稿写完以为是个非常明亮的电影,贴近演员的戏,表演的镜头都带到中近景,背景都是白的,情感非常强烈,真的就是一个“bright summer day”。但看完景之后杨导决定加入台风,很多场景都改变了。以至于我第一次看初剪的时候大跌眼镜,完全没想到会拍成这个样子。一是因为演员的表演(总是很难达到他的要求),而他又不能每场戏花太多时间磨表演,所以除了重要人物和重要段落之外,很多镜头他都调得很远。二是(我惊讶于)他对环境、明暗和空间的追求,但在写剧本的时候他没有跟我们谈过这些视觉上的因素。一般人在写剧本时就会想好那个画面,杨导写剧本的时候只关心人物,谈他们的心理背景、成长背景、遇到事情的反应,而不谈这场戏应该怎么拍。他关注的是创造事件的真实感和每一个人物的真实感,所以最后电影里这些人物才会像真实的人物一样呈现在我们眼前。他一般是在勘完场景才开始想怎么在视觉上实现,这对我的电影观有非常大的影响。
不喜欢文艺腔导演
东方早报:你有参与勘景吗?他好像找了很多老照片的资料做参考。
鸿鸿:有,我从《恐怖分子》开始跟着勘景。对于杨导来说,空间的质感很重要。他看一个空间是很感性的,不喜欢很单调的、一眼看到底的空间,而喜欢曲折迂回的。他需要非常多不同的构图诠释人物之间的关系。讲到这点,他其实蛮喜欢法斯宾德的电影,可能是法斯宾德电影里的场景设置和他的审美很相符。他其实不是很喜欢法国新浪潮,更喜欢德国电影。我当时最喜欢特吕弗,他觉得戈达尔比较厉害,但布列松最好。他还喜欢赫尔措格电影里生命的力量,还有法斯宾德对人性的观察和构图技巧。
台湾的影评人总是拿他跟安东尼奥尼比,包括付东那本新书里也会提到他和安东尼奥尼,但他从来都不和我们提安东尼奥尼。跟我们谈的都是雷乃啊,费里尼啊。他觉得安东尼奥尼的东西很简单、很浅。他也喜欢大卫·林奇。总之他喜欢有独创性的导演,不喜欢文艺腔的导演,他觉得基斯洛夫斯基晚期的《红》、《白》、《蓝》太装腔作势,也很不喜欢安哲洛普罗斯,不喜欢在电影里追求所谓诗意。他追求的是一个故事中人物必须要有可信度,把人物和环境的关系清楚地表达出来,环环相扣。他觉得所有事物都是关联起来的,他就是要挖掘这个关联,所以他很注重剧本。
他的电影都是拍给大银幕
东方早报:《牯岭街》怎么会落选戛纳?
鸿鸿:《牯岭街》最后剪完时,戛纳那边所有竞赛片的片单几乎已经选好了,只剩下一两部名额,当时法国有人穿针引线,所以愿意等他。当时去没法带所有拷贝(4小时版本),只带了头两本35mm给对方看个品质,其余的都是录像带。到现场后因为没字幕,导演又不能在场(解释),只能在当地找个大陆翻译,但我觉得那个翻译的品质肯定很差。最后他们拒绝的理由是今年有很多太长的电影了,杨导又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剪一个短的,所以就没有入围。但后来《牯岭街》在法国上片后影评界一致叫好,所以戛纳组委会显然有些后悔,第二年出现“牯岭街效应”,以后他每次参赛戛纳都能入围。我想如果第二年他拍了“牯岭街续集”,肯定就拿奖了,但他永远都想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东方早报:《牯岭街》没有配乐,但他对音乐其实是很有研究的。
鸿鸿:对啊,他不喜欢像王家卫、安哲洛普罗斯那种抽掉音乐魂就去了一半的影片。杨导个人很喜欢音乐,他会拿维瓦尔第配《风柜来的人》,可见他对古典乐很有研究。
东方早报:《牯岭街》有一段小马、小四带女朋友去看电影,后来在公园接吻的场景,是有意在表现年轻人想营造的浪漫感,但是因为故意没有配乐,那种人物间的尴尬情绪就被带出来了。
鸿鸿:没错。这个尴尬感是让很多观众觉得进入不了他电影的原因,因为杨导永远处在远景,一个观察者的位置,观众要看很久才会认同他的人物。在他所有的片子里,《恐怖分子》可能是拍人拍得最近的一部。
东方早报:听说牯岭街他自己会在现场画图给美术看,也会自己掌镜、打灯,在现场什么技术活儿都懂。
鸿鸿:是,我觉得绘画是帮助他思考的一种方式,有点像打坐,和听音乐是一样的。因为他跟老派的工作人员合不来,镜头的美学、打光的方式他完全不能接受。但找来的年轻人没有经验,做事又经常出状况,他就只能自己来解决每一个细节,比如那个灯应该挪到哪里,应该怎么打,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自己的要求,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专业技术人员。《恐怖分子》时他就会因为不满意镜头的运动而自己掌镜。
杨德昌心里一直认为自己拍的电影是为了在电影院放,而不是做成DVD。《牯岭街》就是一个例子,他敢拍那么暗,设置那么多细节,就是他默认必须在电影院放大银幕上看,才能看到环境的细节。
借电影做自我心理治疗
东方早报:《牯岭街》之后他想要改变风格,所以拍了《独立时代》。他喜欢伍迪·艾伦么?会不会和你们谈儒家思想?
鸿鸿:他很喜欢伍迪·艾伦。我们经常讨论《贤伉俪》,他觉得是心目中最好的电影之一。他也每天和我们谈儒家思想,谈朱熹。我当时心想你别开玩笑了,你那么西化的一个人,你还谈儒家思想?(笑)
他说过《独立时代》是青梅竹马的喜剧版,拍青梅竹马的时候太年轻了,所以用严肃的方式表达严肃的思考。但他觉得伍迪·艾伦的厉害之处是用轻松的方式表达严肃的思考,他试着朝这个方向做一次,所以做《独立时代》。
我个人觉得,他最诚实的一面都放在电影里了。现实生活中他其实很沙文主义,并不太在意别人的感受,但对电影里的角色却十分体贴。他会把自己的一些问题投射在电影角色上面,诚恳地去反省这些问题,我觉得他是在借电影做自我的心理治疗。
他在《独立时代》的书里引用过“能者作智,愚者守之(焉)”,这是儒家精神里比较进取的一部分,强调创造性、独创性,而不是因循。整个《独立时代》是对儒家的反省和嘲讽,他最痛恨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这样会消解人的抗争性、奋斗性、自主性。
东方早报:能否谈谈《独立时代》里面那个“1”的指天动作,他个人有解释过么?
鸿鸿:这个佛手的概念是他自己的概念。他觉得独立是最可贵的,但是人不可能独立。人渴望独立,又害怕孤独,这是杨德昌本人的困惑。一方面“一”代表独立,但同时带有指向性。他其实内心想比的是“中指”,但是显然“比中指”的反叛是不够的,所以他用中国绘画的方式设计了一个佛手,也符合他自己喜欢的一语多关的象征。早报记者 沈祎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