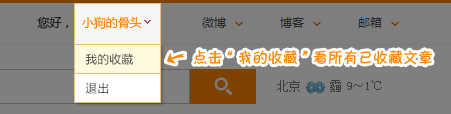艺术形式电影已死?未来将与商业共存!
 侯孝贤导演
侯孝贤导演
晨报记者 彭骥
昨日,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之“新浪潮”大师论坛揭开序幕,中国台湾导演侯孝贤、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微博]、法国影评人让·米歇尔·付东等把话题聚焦在艺术电影的尴尬现状及未知未来。在票房、市场、互联网、IP、大数据等的压倒性舆论下,电影本体的艺术性本身难得地登上讲台。侯孝贤爆出惊人一句:“现在还谈艺术电影?艺术电影早就死翘翘了,现在只留在电影学校和研究者身上。”但他也表示,艺术教育对电影很重要。岩井俊二、让·米歇尔·付东认可这一观点,但乐观表示艺术电影未来还会继续存活。
艺术教育对电影很重要
侯孝贤认为,真正的影像和文字一样,要有一定“深度”才行。他首先谈到胶片和数字的区别,“底片跟目前所谓的数位其实差异非常大,一个是物理的,一个则是化学的,底片需要化学变化,会有各种写实的颜色。”他透露,今后自己能否继续坚持胶片创作还不好说,因为胶片要多出很多花销。数字与胶片拍摄法则完全不同,需要一段时间来测试和适应。侯孝贤进一步谈到,导演一定要对其他艺术形式也有所了解和热爱,才能拍出电影的深度,艺术教育很重要,“有时候我们不自觉拍到(一些东西),它不是绝对性或机械性的,而是人文的。你要电影拍得好,坦白地讲你可能对小说也是非常钟爱,各种艺术的载体可能你都喜欢,都有一种了解的直觉,懂得欣赏,这个感觉需要从小培养。”岩井俊二则表示,日本也是娱乐性电影比较赚钱,而艺术电影不太挣钱,所以艺术电影的预算方面也是非常克扣,导演们也做得很辛苦,这个状况50年来基本都没有改变。不过,他还是对艺术电影持乐观态度,因为艺术性和娱乐性既然已经在艺术中共存了千年,未来也依然会很好地结合下去。
前《电影手册》总编让·米歇尔·付东称,十年前中国有贾樟柯[微博]、王兵[微博]等杰出的艺术电影导演涌现,但可惜近十年内,似乎没有太多的新发现,“中国电影经济在过去十年内迅猛发展,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但确实存在问题。我也赞同岩井的意见,把艺术和商业完全割裂是不对的。过去我们用毛笔、钢笔去书写,但是并不能让每个人都成为作家,现在的数码科技也是如此”。
互联网带来挑战与机遇
谈到创作艺术电影的具体困扰,侯孝贤表示,由于自己是单干户,自己投钱自己拍自己卖,所以尽管有很大资金压力,但还是可以存活下去的,“还死不了”。他更担忧的是播放系统的转变,以前都是电影院,现在各种各样迅捷的平台涌现,连小孙女都会用手机找视频看,很难想象未来会将影像引向什么方向,“我希望一个导演死后进棺材,每一百年起来一次——我最大的愿望是起来看一下当天的电影”。相比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十年磨一剑,岩井俊二的《花与爱丽丝》动画版同样在电影版问世后十年方才诞生。岩井俊二介绍,在日本,宣传费用可能比制作资金更多,《花与爱丽丝》电影版同样诞生不易。现在互联网急剧发展,创造了空前便利的交流环境,但不知会引领往好还是往坏的方面发展。
面对互联网生态下的艺术电影,付东介绍了法国的电影体系,法国之所以能成为艺术电影的良性土壤,是因为已经有一套运行了60年的成熟体系,能把不同的电影联系在一起。互联网让更多人能看到好的电影,加大了艺术电影的流传力度。
创作的秘诀是回归生活
怎么培养重视艺术性的电影人?岩井俊二介绍,日本政府的文化厅在电影制作费方面会给予10%的支持,给导演减轻一些压力。付东则以3D为例,指出可以运用新的形式来创新,3D不仅仅是商业大片的选择,艺术片同样也可以用3D拍摄。艺术电影应该更加努力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拍摄制作。而侯孝贤提出的意见相当实用,称电影影像创作的根本秘诀,就是把眼光放回日常生活里去,并以现场摄像媒体为例:“你们拍采访时都打着小灯,把我们像小饼一样烤着,不打灯会怎么样呢?打破惯例可能会更有意思。用手机也可以成为影像大师,你可以拍家庭、朋友、小孩,捕捉他们生活的形态,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很好的导演。不要拍理所当然的东西,你可以一部分捕捉真实的生活,另一部分可以自由安排,怎么安排是学问,你要有这方面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