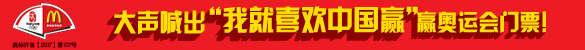|
不支持Flash
|
|
|
《士兵突击》主创聊天实录 主演讲述事业低谷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2月07日17:23 新浪娱乐
邢佳栋思考问题 曹克难表现投入 主创团聚畅聊 所以最后既然只能接受那就是一种心理感受了,如何把自己的心里对待这种困难或者说挫折,其实我说低谷,高谷也是一样,如何把自己的心理能够很正常地、很冷静地面对这些东西,最好不要有情绪,情绪最害人了我觉得(笑)无论是大喜还是大悲,非常害人。 何东:你有一点儿好像,你也不愿意求人,碰到难事。 邢佳栋:谁都不愿意碰着难事,但是很少张嘴求人。 何东:能自己解决就自己把它给消化掉了。 邢佳栋:对,打小就这样,打小连我爸爸跟我说,你到邻居家,咱们家钳子还是什么东西,原来是邻居家把我们家钳子借走,一直没还,你到邻居家把咱们家钳子要回来,我不去,这种事我不愿意去(笑)我跟我爸爸说,咱买一个去不就完了嘛,轴,这人就是轴(笑) 何东:我想问一下曹克难,你在这个剧里出现的跟这波并不一样,我对你有几个印象:老这么站着,不大看人,然后就发布命令,袁朗都得听你的,我觉得当时在部队里已经是很大的官了,好像就是发布指示,包括说许三多离开不离开,这人还留着干吗?然后袁朗赶紧跟你说着,他好像是跟老团长平级的意思,我就问你,你在生活里碰到的你年轻的时候最低谷的时候你会怎么应对这些东西?这是我一直看完戏就想问的问题。 曹克难:实际上从我的外型来看好像觉得挺文,或者是静的一种人,不是,我脾气非常暴躁,从小就是部队大院长大的,受的这种教育也是部队的军人作风,我遇到问题,遇到困难,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一定要把它发泄出来,从小就是,或者跟人吵,或者跟人打,或者找另外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把它发泄出来,自己比如说打一块玻璃,把那个什么桶摔烂,一定要把它发泄出来。 何东:齐桓也是,南瓜,南瓜,臭南瓜,我一听这是官儿的声音。另外我想问一下张谦老师,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很多经历很像许三多,那么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会怎么排解? 张谦:我这方面可能比他们更加那个什么,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比他们都早,而且我可以说生在山西,长在张家口,上学在天津,现在在北京,各种生活形态,生活环境都经历过,包括您说的当年知青的感受,我也体会特别深,当年我们考学也是好好读书,上学,工作以后遇到的事其实那时候比他们还要茫然,可以说你找不着任何说法,原来小时候信的那些突然发现都没了,新的东西还没到,而且那个时候也是处于各种想法其实比现在还多,后来参加工作以后我是国家分配,而且我跟他们还不一样,他们从小有父母的熏陶,我学的是工业经济,按道理我大学毕业应该是去深圳或者留在天津,到一个化工厂那些学工业企业管理这一块,后来去八一厂,那是作为我来说,虽然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但是没想到毕业以后去八一厂,我一想高考没有参军,大学毕业了还能参军,而且当时我们指导员给我做工作,好啊,部队97块钱一个月,我总觉得可以来北京了,另外父母又不希望我到深圳那么远的地方,结果我说行,那就来吧。围着八一厂六里桥转了几圈没找着八一厂,最后才知道是一排小围房。那时候在机关待了不到半年,我基本上全部在剧组,那时候真是有一点接不着,我找不着自己的地方,因为跟专业不一样,而且这个环境你又很陌生,而且文艺这个行当只是从文学爱好者小时候看《金光大道》培养出来的,很多事情你又看不惯,那时候确实比较茫然,那个茫然时期比他们估计都长。后来92年到98年6年的时间只干了一件事,既然干不了别的事,我爱人生小孩了,我就带小孩,带了6年孩子,小学基本上上了小学了。 慢慢的我觉得他们说的非常对,但是我当年最困惑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单位本身就不是一个正式编制单位,是八一厂的一个对外窗口,不是在部队序列里面的,但是我人是编之内的,几方面都是很边缘的时候我一个同学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你都熬了这么多年了,你再多熬个两年算什么?我一想就是啊,然后我又坚持了一年,情况变了,到98年整个情况就开始变了,到了2000年领导反复劝说我就搞电视剧了,搞上电视剧就下不来了,我可能走的时间更长一点,但是状态的东西我觉得他们说的我特别理解,大家都有这个过程。 何东:那么我想问张译一个问题,昨天我专门记在纸上了,因为《士兵突击》里边有一段戏我经常会拿过来看,有一段戏就是你领着许三多打锤子,这个是你在这个戏里很少的,爆发出来了,还有伍六一,你当时就说“你再这么干,离开的就是我了”。那么我想问你在实际生活中有没有这种时候? 张译:有,我觉得我生命当中有一位恩师叫彭鹏,他刚老师那个时候也就是二十七、八岁,比我现在还年轻,我现在想如果我再比现在年轻一岁,让我去带一些十八、九岁的孩子去教他们表演,教他们做人好像是挺难的一件事,但是我这个彭老师不但接了这个任务,而且特别是对我们这几个人特别负责。我在学员期后半期已经变成了一个调皮捣蛋的,而且触犯了一些条令条例,所以那个时候我这个老师一直顶着整个团里的压力保护我的工作,我现在想如果当年没有他对我的呵护我早已离开部队了,那样的话就意味着我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这个老师突然被宣布学习专业学校结束了,他们可能不再当老师了,而且我们那个队要求大家不能和老同志交流,所以我听了这个消息挺恐怖的,很长一段时间没见着他,突然有一天我们在给老同志搬家的时候我看见他散步,我就追上去,我当时就喊了一声“彭老师”,然后眼泪就在眼圈里了,觉得很长时间没见到救命的人了。事隔多少年他还说“你那眼泪声我永远记着”。其实当时已经是团里队里的很多领导对他已经有很大意见了,不过我想刚才就像您说的这些低谷什么的,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就像是水已经把我那个坑填了,我忽然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低谷,或者说我个人的历程,因为您说什么事值得发泄呢?可能是不平的事,或者对自己不公的,或者对别人不公,心里面看不下去的事,是容易让人发泄的,但是这种待遇问题,或者是生活给你的回馈,如果你觉得不知足,它应该不属于低谷,不属于一个事业或者生活的低谷,可能像刚才张谦老师,包括克难哥说的“迷茫”两个字恰恰是最可怕的低谷,可是如果你迷茫了你又冲谁发泄呢?发泄绝对不是解决迷茫的一个关键,有点跑题了。 何东:没跑题,非常好。 张谦:我觉得许三多实际上像在什么地方,当你什么希望都没有的时候你就把自己眼前事干好,这点很多大家都像许三多,因为你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事。 何东:段子我想问你,你在刚来北京落地的时候有没有人帮过你,虽然你不是一个轻易求人帮忙的人。 段奕宏:你说刚进北京是吗? 何东:对,你刚落地到这儿,你是从新疆来的。 段奕宏:其实你刚才所说的后半截,我也怕欠别人人情,其实可能别人无所谓,不求你有回报什么,但是我一定要让我的心理平衡,我必须得有所回报。刚来北京我觉得我庆幸的是我遇到很多贵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在最关键的时刻,比如说我的启蒙老师,他对我的一种鼓励,从精神上,因为我第二年考试的时候找到他们团里的一些辅导老师辅导我台词什么的,他们对我已经判了死刑了,不可能,从你的气质,从你的条件,怎么可能当一个演员?但是他跟我说不要去顾及别人,我当然骨子里面很无所谓,但是如果从中有一个人突然有不同的声音给你一种鼓励的话,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一种温暖和感动的东西。上了中戏前两年没考上,第三年之所以考上是因为我的黄老师收了我,因为我在考94班之前上了一个短期的培训班,6、7个月的,在这个班上我接触了很多专业老师,也是对我判定不可能,希望不大,没什么发展。第三年考了94班的时候,黄老师收了我,到我毕业赵有亮,杨宗进,他们对我最关键的几步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帮助,我觉得他们是对我来说帮助最大的。 何东:你会一直记着这件事吗? 段奕宏:当然会。 何东:现在五班说完了,我看电视剧看到钢七连的时候特有意思,前面许三多在这个剧里,编剧和导演让他修了一条路,并且用这件事显示了他一个人曾经从新兵排逐出去,修一条路,很牛,就是我是有本事的。其实在座的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渐渐找到了我自己的一种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并不一定马上就能做到整个社会对你的认可,比如我刚才跟李梦在底下说,我写的东西给长春那家杂志投稿,我记了270多篇稿子,怎么寄出去怎么寄回来,就急了,刚才邢佳栋讲的情绪这个东西,我现在得向在座的年轻的人学什么,我且过不去呢,所以我就跟那个杂志干上了,跟你突击上了,270篇稿子,还不敢告诉家里,因为你到了10多篇已经不行了,邮票又是8分钱,再重一点还得加邮票,就等着,到了你真快绝望的时候有一天回了一个薄的信封,我自己不敢拆,我跟那个邮递员说你能帮我打开吗?他一撕把里头的稿纸带破了,这下我特别痛苦,然后上面就是特别简单的一行字,邢佳栋,您的稿子预计要在哪个月发表。我天哪,我差点没倒立,还不会呢。那会儿给自己最大的奖赏是什么?买瓶汽水,连雪糕都没有,我记得我当时有意的坐一公共汽车坐了五站,走回家去,以表示我特牛。我今天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个人的能力被社会认可是一个过程,我觉得钢七连这个象征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你许三多不是修条路嘛,我告诉你,伍六一和高城还是不带你玩,他还得重新,等于钢七连是一个系统,许三多这个能力你必须在这个系统里得到验证,这个是我感觉社会和个人这种能力的关系始终,不但年轻,中年到老都会这样,大约是这么一个意思吧。 所以下边我就要问问佳栋了,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憋着,我以前问过张译,当你和张译,还有你们的兵跟着记者回到云南拍摄三班宿舍的时候,当时张译在那儿看着那个窗,你依然像是剧里的伍六一似的看着窗外,站了很久,我问你,你当时心里想什么呢? 邢佳栋:其实您这个问题在传媒大学的时候有学生问过我,我当时确实说的是真话,我就回答了他,我当时心理感受,我站那儿不像演戏那样笔直的站着,其实我还是半靠在墙上,我虽然看窗外,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张译在屋里面,我当时觉得真是时过境迁了,就这么恍惚一年就过去了,我当时想的东西跟《士兵突击》这个戏本身没有太多的关系,我只是在想这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也就在想这些。 何东:心里有什么情绪? 邢佳栋:当时很平静,怎么说呢?其实您刚才在问我这个问题之前不是说了那些吗,我一直在琢磨您之前说的那一大段话,就是个人能力跟这个社会的认可。 何东:两回事,有能力和被社会认可,我后来发现是两回事,270篇稿子不理我。 邢佳栋:还是接着您刚才说的当时有一种情绪,其实我刚才说完了上一段,回答您的问题之后,这个时候这段过程当中我也在想,其实我觉得对峙这个情绪,首先我想到的是这个情绪是不是我的,也跟您刚才说那个社会的认可,跟那个个人和社会的碰撞有关系,我在想您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这是个标准问题,包括许三多进入钢七连,连长和我,还有好多人都看不上他,其实是个标准问题。后来我发现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标准,然后只要是某一个人的标准跟这伙人的标准不同那个人就被摒弃了,所以我觉得钢七连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不是许三多的标准,不是一开始许三多的标准,也不是邢佳栋的标准,其实后来连长在宿舍楼之前跟许三多在那儿踹垃圾筒那场戏,那场戏我觉得他把钢七连,以至于我本人心底的一些标准能够说出来,社会的这个标准还是通过我们很小的时候受到的一些道德上的教育,还是各方面的教育,才在我们脑子里面应验出来这种标准,而这种标准是不是真的确实是我们自己的呢?不见得,情绪也是基于自己的标准,和这个标准不符,这就迷茫产生了,或者在没搞懂到底为什么迷茫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失落,要是完全契合,或者甚至于外面一个大于自己的东西,把自己捧到一个荧光灯下的时候,那个时候情绪又来了,满足,骄傲,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触动了一些可能咱们中国人说的,因为从小受的是儒家的教育,一些道德标准常识性的东西,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缺的不是诚实,缺的是那种可能是弹起来没什么用,就是说起来没什么实际效用的东西,是一种务虚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没有标准的,也可以说我自己的标准就是我的世界,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