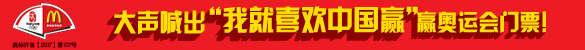|
不支持Flash
|
|
|
《士兵突击》主创聊天实录 聊段奕宏其他作品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2月07日17:23 新浪娱乐
张谦微笑 主持人何东 范雷与小浪人 段奕宏畅聊 何东(blog):说清楚了。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张译,在你年轻的时候你的理想和现实发生了碰撞,就是你每天都在不断的努力,但是我们被这个集体或者社会一点都不承认,那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张译:没有什么选择,还是该干吗干吗。 主持人: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我走错路了? 张译:我承认可能那个时候会有一点觉得自己是否走错路的想法,但是我还没有离开大的这条路,可能是这条路的辅路,也可能是这条路的主路,但是还是在这个上走。那个时候就觉得怎么就有劲使不出呢?就像刚才何老师说的和你的能力,和你得到这个社会的认可,我一听何老师说这个话我特别有同感,可能大家都是这样,比方说我写字,我当时比如说生活中很拮据的情况下,我写字怎么就不能养活我自己呢?太难了。何老师也是寄了二百多次。 何东:我插一句,你知道我第一份稿费多少钱?我第一次15。 张译:我还好,我第一次60(笑)那时候写一个短剧,团里不要,说你的题材和别人撞车了,实际上根本没撞车,就是不要你的,怎么办,当时想给自己写一个戏,给自己创造一个能上台的机会,团里不要你,那给谁呢?就给《剧本月刊》,他说挺好的,发了吧,给了60块钱,然后又花了200块钱卖给我们司令部业余演出队了,觉得挺好的。后来慢慢的觉得演戏也能被社会认可了,写字也能被社会认可的,回头想想那段日子难熬,但是挺有味道,反而现在被认可了,反而有一种彷徨,有一种新的迷茫,就像我刚才说我那个彭老师,我有一次迷茫了,然后我们俩晚上溜山上,在八大处山脚下溜弯,他说每个人都经常会迷茫,很像是一个周期又一个周期,但是因为你的目标不断更替所以你的迷茫也会在变,当你完成一个目标之后你会迷茫,赶紧调整,调整完之后做下一个目标,做完下一个之后你还会迷茫,走着瞧吧。 何东:我想问一下范雷,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有没有像马班长那样,你复原了,那个镜头很感伤,五班的人把你送到那儿,史今领着所有的人,王宝强(blog)嘻嘻哈哈,所有人就一个敬礼对你。你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被一个集体彻底淘汰出局的一个经历? 范雷:淘汰出局? 何东:嗯,不带你玩儿了,或者像春节晚会那样的。 范雷:典型的例子(笑)其实换一种说法吧,这种经历我有过,不见得淘汰出局。 何东:被闪了。 范雷:我是89年,我家也是北大荒的,我当时在佳木斯,我们家从佳木斯搬到山东,整个家搬过去,我爸在那儿生活40年了,我所有亲戚都在那边,当时火车站送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有大概七、八十人送我们家,然后我们三口人上火车,当时好多人在哭,亲戚,我表弟表妹都在哭,我说你们哭什么啊?有什么可哭的,又不是上前线,结果乐呵,挺高兴,一上上火车,一踏上那个踏板,眼泪一下就下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俩小时,就止不住,自己最热爱的地方,最喜欢的地方,最喜欢的人。 何东:我从北京牵到你们黑龙江,就跟你说的情况一模一样,开始觉得出城玩去了,一到火车站一上了火车,我真要走了啊?就开始了,我妈买了两根雪糕,也不知道吃,我哭,那个雪糕也哭,滴滴答,就仨人在那儿,你接着说。 范雷:这种经历很多,我上完学之后去当兵了,然后在山东的时候我妈没送我,她怕忍不住,让我爸去送,出租车也停了,我妈在阳台那儿看着我,我也是,也是那种,又一次的爆发,挺好的,可是一进出租车往那儿一坐,又下来了,然后就是一直抽泣。你经历了这段事情之后又要经历另一段事情,我知道我要告别过去,我这段很美好的回忆要过去了,要面对另一个东西了。 主持人:下面问马帅,如果你在生活当中碰到特别大的打击,或者说特别严重的困难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化解自己? 马帅:我现在来说还是乐观对待,因为经过的挫折太多了,从生理上,不是那个生理,不要理解错误(笑)身体上遇到很多挫折,因为之前是搞舞蹈的,有的学校不重视翻跟头,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必须得练,那基本上一进学校,我们副校长就是一个京剧演猴儿的,就是武行出身,他告诉家长你们尽量不要来看了,看了你们带好纸,不要哭,送进来折胳膊折腿正常的,我能保证你不死,说的有点过分。这都是挫折,我现在这个胳膊没折过,其他哪儿都折过,当时也是自己要强,想着不能失败,自己保持一个乐观心态,主动去迎接这些困难,但是自己从那儿开始总结出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那时候别人都出去玩了我自己练,第一个开的大跟头,就上去了,然后就窝在那儿,跟鸡一样,最后一查脊椎三节,两节压缩性骨折,一节霹了,当时一分钟上不来气,谁也不能动,当时我们老师上来看,你干吗呢?我说练功呢,他说挺好,然后说来,来一个,我就过去了,结果他说再来一个,你就差一个胆量,再翻一个,已经那样了,咬着牙又过去了。像这种挫折多了之后自己渐渐也就知道要爱惜自己,但是还要迎击这些困难,无论你人生当中碰到多大的事,其实都是你该经历的,我说生离死别多了,家里从小亲人的故去这些,打击其实挺大的,慢慢在你成长当中但是都是你的财富,没有那些困难痛苦的话,不可能有今天,让你更加坚定一个信念,是人都要有一个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除非天生有一些疾病。 何东:像我这样的(笑) 马帅:没有没有(笑)天生除非有一些,其实人活着最大的一个幸福就是被社会,被大众认可,我生下来不是一个饭桶,我是对社会有用的。就像我们做完这个戏感觉很自豪,感觉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给社会填补了一个精神上的空缺,正好是社会的一个缺失,《士兵突击》(blog)的精神是社会的缺失,是人最需要的。有的迷茫,还有一个就是坚持,像许三多那样坚持,像李梦那样坚持,总有一天能出来,不要灰心,不要信命,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说随缘,随缘,佛法还讲究你要结缘呢,你要主动迎击这个困难。 何东:我为什么会让姜鸥问你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她21岁,老说我老了,我说那我该死吗?我留言(笑)然后你摁他一下,他过两天又开始了,我郁闷,我最近很郁闷,那么我今天想让哥哥们,或者叔叔们告诉你,你的事就不叫事,你接着来。 主持人:(笑)下一个问问高峰,你在老A的部队里面外号叫屠夫,特别凶残的一个人,你在现实当中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进到钢七连这样一个非常严厉的团队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做?你会很快让自己融入进去吗? 高峰:你觉得老A不严厉是吗? 何东:我知道她什么意思,钢七连在《士兵突击》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团队,以至于袁朗对他经常保持高度尊重,因为我觉得他也是一个人生阶段,你不是狂嘛,把你全给灭了,再把你重新搭上一个人,她要问的是这个意思,我接她一句话,你在那个哪儿出来的时候,你那“南瓜”,声音都是明星腔,特别高,袁朗在后边问你,你就呼来唤去的,如果你要被压挤到最基层部队的时候你会怎么应对? 高峰:如果齐桓到钢七连的话,我觉得齐桓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觉得会比伍六一还要拧的。 主持人:要强? 高峰:不是,都要强,还要拧,他是一个战士,因为我想钢七连可能就是老A的前身,应该是这样。 何东:对,所以我说它是一个事。 高峰:他肯定是已经经历过比钢七连还要硬的连队,锤炼,像许三多一样,像成才一样,也通过这样的训练,也许我也俘虏过袁朗什么的,所以我们俩的关系默契在哪儿,有一句台词,我说这次队长,你又要得罪人了,那肯定是他得罪过我,我怎么进去的,也是同样这样一波一波的淘汰,优胜劣汰进去的,但是恰恰这个戏写了两个士官进去的,这两个士官属于一种奇怪的现象,但是我觉得部队不在于你军衔的高低,在于你的军事素质,军事本领,你能不能胜任国家和老百姓赋予你的使命,就是这个。 接着何老师的问题,人说到挫折什么的,我特有感悟在哪儿呢?实际上有时候人被认可以,被社会认可了,恰恰社会在很大一段时间里面不给予你一些东西,就像我是演员,我在2002年拍完戏以后认可了,突然又没有戏拍了,这就在找为什么,一年,两年,而且最难受的是当你有戏拍的时候不让你去,这就难受死了,因为团里有工作,不让你去,那么好的戏都定你了,都谈好了,待遇什么都谈好了,不行,不能去,在团里待着,哎呀,这是最难受的。我只有三种方法,第一,我说表演嘛,有台词,功底什么的,有一个续气练习,我每天一憋气,先让我的气通一下,第二,写日记,把所有的不平,所有的不满写了满篇,完了把那个字写得怎么难看,怎么谁也认不出来,只有自己心里知道,第三,弄个游戏机就打,打游戏有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情节你得想办法过关,我就把这个故事一直打完了,每次我打一个故事将近一个月或者二十天,有时候我过去以后再回到前面一关,我换一个方法从这边能不能过去,我是这样的,当我几个方法都试了都能通过,一直打到完结篇,胜利了,我心里就坦然了。这可能就是关口,过去就没事了。 何东:段奕宏(blog)同志,《刑警本色》里演一个杀手,然后你的话剧代表作好像网友不太知道,《纪念碑》,我看了三遍,就是在首都剧场(blog),因为我们家门口,然后我就看你在里头演一个人格分裂的儿子。 段奕宏:人格分裂的战犯。 何东:然后你的我看过的几个角色,除了这回的《士兵突击》以外,你的角色的表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挣扎,而你一遇到比较挣扎的角色的时候你的爆发就是空前的,就是会把观众带的跟你完全进入个情绪,这是不是你面对类似像钢七连的这种环境的时候,你特有的一种表达方式?假如你碰到这种当你的个人能力和社会发生激烈碰撞的时候,你这人是挣扎能力极强的一个人,演戏也是,一到这个份儿,你那个本能就会出来,包括《刑警本色》,已经被判死刑了还不服呢,所以我就想问你被压挤到一个社会系统里的时候,你的状态是什么,是那种挣扎吗? 段奕宏:如果这样去设想的话,我对我自己的了解和认知,我觉得挺可怕的,应该是一个很可怕的,刚才我们在讲当你遇到这种困境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从考中戏到现在,我觉得每个人所经历的事情都是或多或少学会了做自己的心理医生,如果我做不好我自己的疏通渠道,我的思维,我的观念,我可能一旦受到挤压的时候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就是我对我自己了解,我这个人从零度到一百度可能没有过程,就是说我的挤压,我的受压,或者说我的痛苦我会让人看不见,但是一旦爆发的时候,别人会“疯了吧,他,怎么回事?”,他其实看不到我这个过程,当我堵塞已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膨胀的时候那个威力很大。所以如果说我受到这么大的挤压,好在我学会了安抚自己,好在我有排解这种东西的渠道和能力,因为我必须得学会,但是我们要学会,我们找到进入角色的一种能力或者一种手段方式,但是必须得学会如何走出这个角色,否则我们生活和我们身心简直是太受折磨了。之前压根儿不知道,还庆幸,还享受着,太棒了这种感觉,但是你睡不好觉,你的头发也在掉,整个你的生理紊乱,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缺乏的是如何走出这种角色的能力,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太投入了,太体验派了,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不能说二,我觉得那是一个必须得经过的过程,现在我们随着年龄,随着我们的能力增加之后,你必须得学会怎么走出来。 回到刚才那个话题,我们遇到任何挫折,任何困难,首先要学会自己做自己的心理医生,我们现在学会转换一种态度,一件事情发生之后你如何去转换对这个事情的态度,变成一种积极的,就像我们这次在云南拍七个半月的电影,我们坐两个小时的车到这个地方,还得徒步走五十分钟到山顶,很多人很疲惫,因为我们已经拍了四个月了,但是我在跟自己说你必须经过这个,你必须走,但是你走这个心态是什么样子,我就把它当成一个运动,因为我喜欢运动,我找到一个我的兴趣点,太棒的一个森林氧吧,你带着这种心态去走这条路,那不是五十分钟,可能二十分钟就到了。 何东:接着问,没说完呢,你说了半天,我采访兰小龙和康洪雷的时候,他们一致向我报告一个信息,对所有《士兵突击》里的角色,他们作为导演和编剧都有所把握,惟独袁朗没有,然后就把这个问题交给了段奕宏同志,您爱怎么着怎么着。据说你在云南就很严酷了,你就变成刚才你说的那种压缩饼干,因为这种新式的军人,他们俩很直白地跟我说不知道,这种时候听说你在那儿用尽了脑筋,甚至很难受,兰小龙告诉我在那儿折磨自己进入进去,最后你是怎么从里头出来的?
【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