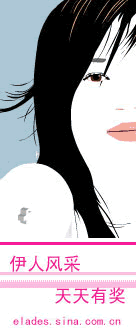对话
章明:电影陪我度过漫漫长夜
对话者:章明
程青松 黄鸥
程:一个人的创作和他的出生以及经历都是分不开的,你是出生在重庆东部的巫山吗?
章:不,我出生在一个更穷的地方,城口。我的父母很革命,他们师范毕业以后特别有理想、特别热血,觉得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们家四个孩子都是在那边生的。长大以后一直想回去看,年年想去。我对城口没有印象。父母调到巫山的时候我一岁多,有一点点印象是从城口到巫山,父亲挑着箩筐,箩筐里一边是我,一边是我哥,走了一百多公里才会有车。途中下暴雨,一家人找个地方躲雨。我总是能回忆起双手抓着箩筐的绳子,在里面一颠一颠的情景。还有一个印象很深的是,我在巫山上幼儿园,老师在上面讲,我在下面画画,老师批评了我。后来过年的时候老师到我家去玩,和我父母聊天,我妈妈搂着我,不知为什么,我上去打了老师一巴掌。为此,我父亲用鸡毛掸子打了我一顿。到十几岁,碰到那个老师,他还要提这件事。说我小时候有点儿怪。
程:"文革"期间你的学习有没有中断过?
章:小时候,有几年我和我妈妈住在巫山河对面的农村小学里,她是老师嘛。我记得那个小学校在庙里面。学校五个年轻的女教师,只有校长是个男的。当时我五岁。我上学很早。那是个夏天,她们穿了很少的衣服,坐在院子里聊天,突然她们都进屋子去穿得很整齐,我一看,是校长来了。我印象中校长很少说话。有一天,突然听说有人自杀了,大家去看,是校长。很久以后才知道,那时是"文革"初期,他很恐惧,因为出身不好,恐惧成为历史反革命。校长的尸体停在庙后面一个像祠堂的地方,晚上女老师让我去把那个小门关上,因为只有我一个男人了。她们比我恐惧。
黄:你不害怕?
章:不怕。我记得煤油灯的灯光照在校长尸体上,那是我儿时印象极其深刻的为数不多的画面。也许后来想拍恐怖片和这个有关。
程:你的《巫山云雨》和《秘语拾柒小时》都有长江对岸的故事,是不是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章:是下意识的吧。
黄:在《巫山云雨》里,你让那个叫丽丽的女孩儿朝着大轮船挥手。
章:我记得小时候住的房子的窗户很高,我每天踩着东西扶着窗子向外看,窗子就像个电影画面,方方的。外面就是长江,有时候会有船经过,要看到一艘船需要长时间的等待,客船三天才有一班,客船更有意思,有人站在上面,觉得它像一个城市就那么缓缓地流过去了。
 外面就是长江,有时候会有船经过,要看到一艘船需要长时间的等待 外面就是长江,有时候会有船经过,要看到一艘船需要长时间的等待
程:你妈妈是老师,你读书很早吧?
章:我在上学前就写毛笔字了,但那些字我都不认识。
黄:你父亲呢?跟你妈妈不在一个学校吗?
章:九岁之前我对父亲的印象都不深,他在对岸的城里,跟我奶奶、我哥他们在一起。我和我妈妈在乡下的小学校。很奇怪,那时候,我父母他们并不是经常见面,其实只隔了一条江。我朦朦胧胧地记得有天夜里我父亲坐竹筏子过来,第二天一早又走了。
程:后来回到城里是什么感觉?
章:九岁回到城里,很不适应。在乡下和乡下的孩子玩得很好,用泥巴做枪,钻山洞呀,去河沟里洗澡,还差点被淹死。有些场景特别像鲁迅写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石头缝里面真是有无穷的奥秘,像蛇下的蛋和小虫子,我都去看。山上还有很多坟地……
程:你不害怕吗?
章:不害怕。刚才说到,小学校长死后,女教师下了课,要去家访,黄昏出发,回来时肯定天黑了,她们都带着我去,壮胆,路上还要经过坟地。有次我记得看到坟地的鬼火,就是磷火,她们吓得抱成一团。进城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惟一值得得意的是有些女同学请我替她们完成画画作业。我心里挺得意,但是也不表露出来。那个时候,班上有县委书记、武装部长的女儿,感觉自己和她们的差距很大。
程:你在乡下打了绘画的基础。乡下有书看吗?
章:在乡下的时候,有户农民家的窗子上摆了很多的小说,《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和赵树理的小说,放在木格子中间,我每次都去换一本。大概八岁吧,认的字足够用了。
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和当时看到的别的小说完全不一样,是说两个人要结婚,男的带女的去买家具,是三十年代南方的故事,可能是《三家巷》。
程:隐约意识到这个世界还有别的事情。
章:应该是这样。《水浒传》和《西游记》是进城后听我的一个伯伯讲的,他是"右派","文革"期间我们家不敢和他来往,他靠每天挑石灰和搓麻绳生存。因为他,我初中时要求入团都入不了。只是当时我负责全校的黑板报,女孩子才对我刮目相看。加上我的作文好,经常会拿到全班、全年级念,就这两项是我觉得做人能做下去的理由,否则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打架的话,我身体瘦弱打不过人家的。
黄:你的数学怎么样?
章:我的数学一直不好,但是几何不错,是全班最好的,我图形画得好。初中的物理、化学挺好,但到了高中,它们和数学结合紧密了,我马上就不行了。当时的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文革"期间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我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像一部电影,像《现代启示录》。九岁之前的一个暑假,我们比较穷的一帮孩子在河边玩,我说的比较穷就是指人家下雨能打伞我们只能戴斗笠,那时的地位是很卑微的,和打伞的没法儿比。我姐姐当时十三四岁,我记得父母为了给她买一件涤卡布料的衬衣,商量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终于决定给她买了那件衣服。因此我们这些穷孩子就到河边挑小石头卖钱,一天大约可以挣一毛钱。有一天在河边,突然飞来一架直升飞机,飞得很低,军绿色的,哇,从来没见过飞机,全城人都涌向河边。就像我现在要是看到飞碟的感觉。突然飞机上的人把门打开,往下发红色的传单,大家抢着去拣,一看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这是"文革"中期的事情,刚才说的校长死是"文革"初期。我对武斗的印象也很深,有一天来了几百个穿着整齐的青壮年农民驻进学校,学校立刻就停课了。三天后的清晨,我被巨大的嘈杂声吵醒,所有农民都在砸桌椅,只要桌子腿,然后就都冲去出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十几天后,又一帮人扎着红袖标,扛着重机枪,排队游行,打着标语"保卫巫山"。后来口号又换了,要打云阳,全城欢送这些文攻武卫的人。
程:我家就在云阳,要打我们家那里?
章:全城的人都到河边送他们去打云阳。过了几个月,还是半年,那些人死的死,伤的伤,就回来了。
黄:你上大学之前,几乎没有离开过巫山吗?
章:我母亲的家在万县,当时去趟万县,比现在出国还兴奋。万县是我见到的最大的城市,那里有教堂。万县的二马路简直就是纽约或者东京。
黄:从巫山过去要多少时间?
章:当时我母亲要赚好几年的钱才能到万县看我外婆,我很小是免票,我姐姐是半票。一个是万县的教堂,一个是吃豆腐脑儿,给我印象最深。十四岁我初中毕业,假期打工,我爸爸介绍我到一个学校的工地当小工,帮砌墙的师傅搬石头。我干了整整一个假期,赚了十几块钱,就够去万县来回的船票了,我就和妈妈一起去了万县。
程:你高中记忆最深的是什么?是想考大学?
章:高中就是1979年以后了,我觉得乏善可陈。初中更有意思,不怎么上学,学农嘛。
黄:摘蓖麻。
程:全国都摘蓖麻,我们南方摘蓖麻,你们北方也摘蓖麻,真是大一统啊。
章:还有间苗、送肥料。到山上开荒,挑粪。你想那个粪得值多少钱?我们挑几十里路啊,附近都是荒地。我记得1976年夏天,我们正往山上送肥料,高音喇叭里放哀乐,黄昏从山上下来,得知是毛泽东去世了。本来很疲惫的,一下子觉得更沉重了,中国出了件大事。回到城里,看到很多人红肿着眼睛,开始布置纪念的地方,有些人已经戴上了白花和黑纱。全城的气氛一下子变了。
程:我对1976年也有很深的印象。后来一想,其实是感觉一个时代要结束了。我还记得很快就恢复高考了,那时你也上高中了。
章:高中真是没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学习。相比起来,初中有件事情我现在都还记得。当时班里搞帮派,打架行的才是孩子王,写字画画好没用,我是很孤立的,只有两个孩子和我玩。到了快毕业的时候,那些孩子全部"叛变"到我这边来了,因为我写了个剧本《南海歼敌》。学校离城里远,中午都不回家,我组织他们排练,当时不和女孩子玩,男女划清界限,我写的角色全部是男生。那个时候连海的照片都没有见过,特别想见见大海,所以写《南海歼敌》。当时学校很时兴演戏,文工团也在演样板戏,像《红色娘子军》这种。文艺轻骑队是当时的一种时尚。我组织我们班同学每天中午玩这种东西,到农民的晒坝上排练,我设计了很多武打和空翻的东西。刚好学校有了个新的礼堂,我们决定在礼堂演出。礼堂没有幕布,可我设计了很多场景的转换,没有幕布是不行的。老师让同学们回家凑布票,凑不出那么多,最后没有演成,流产了。
程:就像《巫山云雨》没有公演。
章:我后来一直想把这个剧本找出来看,但是找不到了。我爱好电影就是那个年龄的延续。
程:是对叙事的渴望?
章:只是觉得好玩。因为学习没有乐趣,当时还有一个乐趣就是扎针灸。上学学扎针灸,我发现针从虎口这个地方刺下去,一直刺穿手掌,一点儿都不疼,很有意思,这也成为考验每一个男孩有没有勇气的方式。
程:当时有电影看吗?
章:很少,只有样板戏。
黄:你看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
章:纪录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纪录片,每天都去看。看了十几遍,印象最深的是那些人把防护衣脱下来,翻过来倒汗水,衣服里的汗水足足倒了一脸盆。第一个故事片看的应该是《红灯记》。
黄:看的是露天电影吗?
章:不是,是电影院里,全城的人都围在电影院门口,为了搞到一张电影票。当时我有一张下半夜的《红灯记》的票,是24小时轮放。我抱着非常大的期望去看,但普通话真的是听不太懂,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后来朝鲜电影、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多了,《多瑙河之波》是最好的。这都是初中时候的事,高中印象最深的两件事,一件是毛泽东去世,另一件是我同学的哥哥被判死刑的事情。我同学的哥哥和他的朋友们偷偷地研究托尔斯泰的小说,成立了托尔斯泰研究小组。其实还包括研究其他的苏联小说,自己觉得很神圣。他们几个人不在一个城市住,经常写信,谈论到小说中的很多事情和现实生活的关联,结果这些信都被公安机关截获了。我同学的哥哥是组织者,被公安机关说成是反革命小组的头儿。当时反革命的首犯都是要被枪毙的,每年巫山都会枪毙这样的人。他就被关起来了,等着秋立决。和他关在一起的另一个人是鸡奸犯,当时不懂,后来才知道就是同性恋。那个鸡奸犯判得很轻,但我同学的哥哥判的是死刑。没想到赶上1975年邓小平上台,政策又变了,说就是研究文学嘛,没什么。但是抓他的人正好是我们班一个女同学的父亲,是武装部的。这件事情让我心里很矛盾,我同学的哥哥是我很崇敬的人,但这个女孩又是我很喜欢的。我很迷惑,正义到底在哪边,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情感问题。
程:我知道,你发生混乱了。需要判断,需要选择。
章:那是一个很迷茫的年代。我同学的哥哥十年之后才给他平反,但他这一辈子因为这件事情就完蛋了。他再也不愿意提这件事情,找了个重庆的老婆,调到重庆去了。我的那个同学当时是理科学得最好的,经过了他哥哥的事情,后来他精神不正常了。
黄:你和那个女孩后来有什么发展吗?
 我很迷惑,正义到底在哪边,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情感问题。 我很迷惑,正义到底在哪边,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情感问题。
章:没有,我都没跟她正面说过话,我一直是这样的,到大学都如此。我恋爱谈得比较晚,大约在23岁吧。可我明白这些事情很早,五六岁就明白了。看来是明白这些事情太早,想象得太多,心里障碍就越大。
程:我知道你考的是美术系,你上大学时的兴趣也都在绘画上吗?
章: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就写过电影。因为这个事情,父母和我闹翻,班主任和我闹翻。
程:写的什么?
章:当时巫山城里有很多弃婴,有一些女人去刮娃娃,就是到医院去做流产。如果你从医院出来,全城人都会对你另眼相看。当时巫山的"一枝花",她父亲陪她去刮娃娃,出来后全城的人都夹道相迎,那个场面……
程:触目惊心啊。
章:当时的人们没有新闻,可想而知人们的生活是多么贫乏,有一点儿事情就会满城风雨。她爸爸就那么背着她,从全城人的面前走回家。我去年回家过年还看到那个女孩,现在大概四十多岁了吧,开了一个发廊。我当时写的电影剧本,写一个外地的男青年拣到了一个被遗弃的小孩,他带着小孩上了船,遇到一个好心的女青年帮他照顾孩子。他们两个人带着这个小孩一路旅行。我拿这个剧本到处去投稿,所有的电影杂志都给我回信说,你这个不能拍。我写的东西被父母发现了,他们非常为我担心,因为我哥哥姐姐都被耽误了,弟弟又小,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怕我考不上大学。但是,肯定我还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数学老师发现我在数学书上画得乱七八糟,告诉了班主任,我被当成坏典型,在全校名誉扫地。当时是讲"科学的春天",我等于是不尊重数学老师,不学数理化。
程:那么到大学以后,你对电影的兴趣就公开了?
章:我从巫山考到重庆,才17岁。轮船上的风很大,面向未来,那是一段愉快的航程。到了大学,图书馆里电影类型的书并不多,只找到四到五本,都是苏联的,还有一些电影杂志。第一个看的电影方面的书是一本小册子《墨西哥万岁》,那些剧照让我一下子就改变了对电影的想法。我后来又写了一个剧本,关于越战的,还有科幻的东西,我在里面发明了一种阅报机,打开来可以看到当天的报纸。
黄:挺像现在电脑上网。
章:在大学里我很活跃,写理论文章,和一些社团办地下刊物,办画展,差点儿被开除。我们还组织选举,搞这种风起云涌的事情。主要是看到美国总统的选举,里根当总统的那几年,中国也开始搞选举。我们终于可以自己选学生会主席了,觉得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干得轰轰烈烈的。当时还不够开放,我们学油画的要求画人体,就被学校打入黑名单,七八级的是最坏的一帮人嘛。(笑)
程:你毕业后又被分回了巫山?
章:对。我的父母和亲戚们听到这个消息受到很大打击,他们觉得从小地方到了大城市,结果又回来了,一切还是没有改变,那真是命运。我在巫山又当了五六年的老师。我的一个同学被分到自贡电视台,我常过去玩,给他们免费帮忙。
程:你是哪一年考上电影学院研究生的?
章:八八年。八六年我没法考,因为外语一塌糊涂,后来的两年一直在搞外语。
程:你的父母还管你吗?
章:其实他们一直都管不住我。
程:你在研究生的三年中学习如何?
章:到电影学院之前,电影的观念已经形成了,到电影学院只是解决操作的问题。我记得我的导师王心语对我很担心,因为我很内向。我们每个星期在一起看一部片子,看完之后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但我感觉他就像一个父亲一样。他觉得我应该到一个电影的环境里去,他通过关系让我到潇湘厂的剧组做前期的准备,我很不习惯副导演的那种生活。剧组的整个状态和我的感觉风马牛不相及,我想拍电影如果是这个样子,就不要做这件事情了。但我知道我自己肯定不会像他们这么做的。我就离开了这个剧组。
 轮船上的风很大,面向未来,那是一段愉快的航程 轮船上的风很大,面向未来,那是一段愉快的航程
程:你第一次正式做导演是什么时候?
章:九○年,跟我老师拍单本剧,他让我做导演,其实都是他在控制,他确实想把我培养出来。拍戏的时候,我和他住一个房间,他每天回去得比较早,都会帮我放好洗澡水。
程:这次拍戏对你有什么意义?
章:我知道了现场是怎么一回事。最重要的一件事,中间有一场戏公安人员抓赌搏的人,老师让我想该怎么拍,并让我晚上看他怎么拍。导师让演赌徒的人顺墙站一排,公安人员逐一从上到下搜身,我忽然明白了,这就是场面调度。这就让我对时空的想像和实际操作联系起来了。那一刻明白了电影是怎么一回事情,让我很振奋。九一年毕业之后,我觉得不能靠老师了,要靠自己干些什么事情。我和几个同学有一天翻《中国青年报》,看到一个报道,有个青年得白血病去世了,他的事情让我觉得可以拍。
程:就是你后来拍的《为了聚会的告别》。
章:我写了剧本,然后和两个同学每天骑着自行车去中科院谈合作。我还请了文学系的马修雯老师帮忙,马老师是个很容易和别人熟悉起来的人。我们就一起去中科院和中央电视台影视部,他们也认为这个剧本很好,后来就拍了,拿了飞天奖。
程:你拍《巫山云雨》是个偶然还是必然。
章: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从海南做生意回来,其实好久都没有联系了。我对电影的痴迷在大学时是非常有名的。当时我们一起看谢飞的《火娃》,他们都中途退场了,只有我坚持把它看完,就落了个外号叫"火娃"。
程:是先找到投资再确定内容的吗?
章:我的那个同学对我说:"你现在想做导演,我有那个能力。"他并不管我拍什么。后来我请过刘恒和余华,我想给投资方一个保证,让老板对这个事下决心。我从小学到大学都非常关注小说,这几年淡了一些。后来老板说你只要找一个和你感觉相投的作家就行了。我看过朱文的小说,觉得他的感觉很好,我通过韩东找到了朱文,朱文很有兴趣。然后我们一起去了巫山。九五年春节朱文在我家过的年,我们一直在谈。当时我看到一个小册子《在期待之中》,我和朱文讲我们就是要搞这个东西。我给朱文讲信号台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主人公麦强。陈青这个角色是朱文一个小说里的人物,但已经没有什么关联了,但感觉还是那样的感觉,麦强和陈青是江两岸遥相呼应的两个人物。
程:那个警察是怎么出现的?
章:我回到巫山,母亲送给我一枚金戒指,我戴在手上,和朱文到处找当地人聊天。在奉节路过一个金铺,一位老师傅问我要不要打戒指,告诉我们戒指怎么打。后来影片中的人物就是请他演的,对白也都是他的原话。这让我们感觉应该有个人来打戒指,就是那个警察,他一出场就是要结婚。因为麦强是一个很抽象的人物,他离现实生活比较远,影片中需要一个距现实生活很近的人。麦强和警察是社会生活之外与之内的递进,就像一个梦境里的东西和现实里的东西。在我的新片《秘语拾柒小时》里也有类似的氛围。我们差不多做了一个月的谈话,后来我借了巫山县城里惟一的一台电脑给朱文,是PC286。一个月后,我们带剧本回北京。本子被青年电影制片厂否定了。后来到了北影,正好田壮壮在负责剧本,他说没有问题。我担心夜长梦多,有一天看电影碰到了张献民,我说你来演吧,一个星期后我们就出发了,出发前一天我在北太平庄碰到了钟萍,我们站在大街上决定了她来演陈青。
章:我是一个有双重性格的人,双子座的。我的电影也是这样的。
程:思想家伯林说过他就喜欢生活在生活的表层,但实际上他又是一个思想很深邃的人。
章:我喜欢那种没有世故的肤浅,或者非常难懂的东西,比如大学时看海德格尔的书。程:我看那种非常肤浅的电影或很深邃的电影都不会睡着,就怕看那种中庸的影片。
章:我喜欢两个极端。前些时候又看了几遍费穆的《小城之春》,发现里面有很肤浅的东西,同时也有让你说不出来的很深奥的东西,这两方面完全相反,但我都很喜欢。作品跟个人的性格很有关系。
程:《巫山云雨》真的有点奇怪,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不太接受它,时间久了,反而喜欢它、议论它的人多起来了,影片也是越琢磨越有味道。里面的人物,如同你所说的,在生活之中的,或者游离在生活之外的,这些在今天看起来更有意义。当时你是想到这些么?
章:这样拍《巫山云雨》,只是觉得电影不应该像以前那么拍。它应该是个人的理想,把它当成理想那么拍。但因为我双重性格的原因,给我的片子带来许多好的方面,也造成很多缺憾。
程:1995年夏天,参加完高考之后,我去巫山,探望正在那里拍摄《巫山云雨》的张献民(饰麦强)和你。当天晚上,我在巫山电影院观看了从北京带回来的部分洗印好的样片,由于不知道影片要讲述什么样的故事,也没有对白,我看得一头雾水。半年之后,我在电影学院看到了完整的《巫山云雨》,我当即就被这部具有魔幻色彩而又异常真实的影片给震撼了,我身边的好多同学却都看得稀里糊涂。时间过去这么多年了,曾经让我激动不已的《巫山云雨》,通过民间的传播,看到的人在逐渐增加,当时不能理解这部影片的观众也开始全面地接受它。
章:也许他们看之前没有心理准备,影片超出了他们的审美经验。片子违反了一些电影常规,在初审的时候就被骂了一通,好像他们被愚弄了似的,说男女主角在电影结尾才见面怎么能说得过去呢?
程:《巫山云雨》的结构很新颖,三个段落,似乎各不相干,其实又有联系。
章: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1995年,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的、不同地区的新导演,三十多岁的,拍出一批都是这样分几段的影片。实际上他们互不认识,从来也没有沟通过。但结构似乎都采用这样一种方式。
程:这很值得研究。1996年获金狮奖的《暴雨将至》也是三段式。还有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原来也是三段式的。《堕落天使》是其中的一部分,太长,变成了两部影片。
章: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原因使大家都在关注一些共同的东西。这个背后,我觉得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原因。主要原因是这个世界不太像过去的世界了。在以前,大家可以关注同一个事情。中国比较明显,一部小说出来全国人民都看一部小说,一部电影出来大家都看这部电影,谈论这部电影。实际上,这几年这种情况已不再重复了。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人们越来越分成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类别,他们关心的事情越来越不一样了。所以这些导演想要表现这样一种状态,即某种多元化的社会格局。也许他不一定是很理智的,可能是下意识地去表现。社会确实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越来越厉害。随着多媒体的介入,会越来越厉害。因为今后我不用出门,就可由我自己选择来看什么。不用电视台为我选,为我提供什么节目。我专选我要看的东西。我可以只看这一类电影,就选一类,别的我可以不接受,也不去想它。可能人在这种非常先进、高科技的情况下,相对越来越平面化。这个东西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整个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化,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我想对中国的电影会有很深的影响。
 1986年在巫山,没想到10年后在同一地点拍摄了《巫山云雨》 1986年在巫山,没想到10年后在同一地点拍摄了《巫山云雨》
 《巫山云雨》参加电影节时,章明和男主演张献民在柏林墙留影 《巫山云雨》参加电影节时,章明和男主演张献民在柏林墙留影
黄:《巫山云雨》里有一个警察吴刚,你认为他跟《民警故事》的警察是一样的吗?
章:我觉得《民警故事》跟我的影片完全不一样。我这个比它主观多了。吴刚作为一个警察并不重要,麦强作为一个航道工也不重要,陈青作为一个旅馆服务员也不重要。他们的身份并不重要,关键是他们的生命状态,这是我们惟一强调的。这个身份代表很多人,是最重要的。然后你光有这个题材、这个想法还是很浅的东西。关键是你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表达方式。电影很多年来一直在变的就是表达方式。
黄:你认为怎么说更重要?
章:电影形态的变化,包括表达和被表达的东西在里面,不存在纯粹的形式。表达方式的重要是指创作者站在什么角度,想表现什么。这个影片超出了形式的范畴,还是作为一种形态出现。形态本身带有美学的含义在里边。美学的含义在于它对生活有一种观照。生活本身给你回馈了什么,这些因素都在里边,所以绝对不是个形式、结构的问题。这个东西本身包含着一种观点。而观点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生活给你的触动。
程:麦强和陈青最后才同时出现。其实很可能两个人一直都是不知道的,或者说见过,但是并不相识。只是因为某一个原因才有了相遇的可能。
 他们的身份并不重要,关键是他们的生命状态,这是我们惟一强调的。 他们的身份并不重要,关键是他们的生命状态,这是我们惟一强调的。
章:对。我觉得这里面还同时包含着巨大的悲哀。也许跟我们很相似的人或者有共同愿望的人就是这样隔着一层纸,生活了一辈子大家也没有交流。生活本身好像是越来越各不相干,但实际上我们的命运是一样的。
程:这很可怕,人们变得越来越不相干。
章:但这只是概括这一点。生活本身要比这个纷乱、复杂很多。因为每部电影都要对生活有所概括,一概括你就在找那个东西。你看安东尼奥尼的《奇遇》,当时正统的电影,主流的电影故事都是完整的,但《奇遇》没有那样去做。比如说麦总是梦见一个女人。陈青老觉得有人在叫她,也没有说明谁在叫她。你要说明了就没有意思,你就感觉到我在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我觉得这个应该超乎直觉之外的意思,要由你在拍摄的时候完成。有些东西写剧本的时候不能去规定它。
程:《巫山云雨》的故事刚好发生在一个即将淹没的地方,使这个故事本身具有一种压力。
 生活本身好像是越来越各不相干,但实际上我们的命运是一样的。 生活本身好像是越来越各不相干,但实际上我们的命运是一样的。
章:对。这个是电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整个电影被控制在这样一个状态下,这个地方要消失了,不存在了,强调这一点,通过一些电影的手段。
程:并不是想去表现什么三峡工程。
章:对,这个跟三峡工程本身是没有什么联系的。这是一个前提。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大的前提,对理解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非常有帮助。
黄:你的电影才华得到了国际影坛的肯定也得到了国内影坛的冷淡。大家都在说,你在拍完这部处女作后六年来就销声匿迹了。
章:这几年东跑西跑的,拍了一些电视。为电影频道拍了几部电视电影,其中有程青松编剧的《晚安·重庆》,拍了12天。
黄:为什么没有拍电影?
章:其实我一直在做电影剧本,也一直在等待。
程:好像让大家等得太久了。你说说《秘语拾柒小时》吧。
 《秘语拾柒小时》剧照 《秘语拾柒小时》剧照
章:《秘语拾柒小时》开始的想法完全是不一样的,我是想拍成很宽广的环境,人物小小的那种,象《韩熙载夜宴图》,我还和摄影徐伟聊过,但开拍前这个想法完全消失了。现在看片子,景别小,动作很具体,其实这些具体的东西我原来认为都不重要,我不知道原意怎么都遗失掉了!
程:你认为是什么造成的?
章:我的性格。可能是剧组肤浅的生活,大家玩在一起了。(笑)拍摄期间河水经常涨落,搞得我们狼狈不堪也是原因之一。还有光线、背景和船的声音,拍摄现场总是担心这些技术的东西!在没有看到样片之前,会特别担心,怕戏不连接。
程:你本来是想拍一部恐怖片的,剧本没通过,改成了现在这样的一部所谓的爱情片,有没有受到伤害的地方?
章:影片原来重要的一条线,就是警察带"枪"的戏被完全剪掉了,那张让大家互相猜忌的纸条就变得突出了。其实,人死不死没多大关系,死是很抽象的。人活着不是跟死人一样么,你是想像自己活着。这些意思现在看来在影片中很隐晦。纸条是河边玩的人无所事事搞出来的,对警察来讲,这些来旅游的人,他们那种无所事事代表一种自由的生活,和他们在一起他很愉快,回家反而不愉快。这就是你的不愉快可以成为别人的快乐。这是个很肤浅的问题,但我觉得是个很有深意的问题。不知道观众看不看得出来,这得使劲看。可谁也没有办法让观众使劲看它。
黄:很多人都是带着对《巫山云雨》的期待来看的。
章:还有一个问题,看之前问是不是恐怖片?是。于是,大家就延着这个思路看下去,就会觉得不对。其实重心从看之前就完全偏移了,变成风马牛不相及了。
黄:做宣传的时候不能打恐怖片的牌子。这个片子和《巫山云雨》间隔时间太长了。
章:六年,真是一个漫长的等待。
 动感短信、闪烁图片,让您的手机个性飞扬! 动感短信、闪烁图片,让您的手机个性飞扬!
短信世界杯站:新闻、游戏、动感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