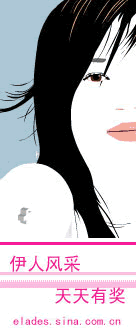对话者:王超
程青松
程:你对60年代的记忆是什么呢?
王:我是64年生的,我的少年时代赶上了一点"文革"的尾巴。
程:对电影的记忆呢?
王:你是要问我最初的电影印象是什么?不是世界名片,是《青松岭》。那条路有个关口,马一到那儿就惊,看到那样的场面,简直是震惊。还有《金光大道》,找孩子的那一段,那个很空旷的全景。你让我回忆阿巴斯,老实说我得努力回忆是什么时候看的。而最初的电影印象真是这些电影,我甚至认为最让我激动的是《创业》,看到里边的场面我就流下眼泪,当然那是小时候。
程:是因为里面的英雄情怀还是……
王:不是英雄情怀。我脑瓜里面可能没有多少英雄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那可能是一种人类情怀,人是可以这样的,是可以激动的。
程:即使是像那样的影片,它还是要流露人的情感。
王:对,影片就是这样的。
程:就是高大全,就是石油工人一声吼,在那个影片里你还能看到人类的那种……
王:因为孩子是全然看不懂他说的什么东西,也全然看不懂他渲染的什么东西,看到的是一些人,一些人的面孔,一些人的情绪,一些片断。这些就是电影给我最初的冲击。
程:这些人跟你后来拍摄的影片中的人状况是一样的吗?
王: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因为我不是把它们当做一个电影来看,而是当做一个片断,当做一个在梦幻般银幕里面人的脸、人的情绪。
程:人的片断。
王:对,让我感觉到看见我们自己。1978年以后,大量的文学名著开禁,一些50年代的外国电影也进来了。
程:当年你已经上初中了。
王:看见很多外国名著改编的一些电影,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即80年代初的很多日本电影,还有日本电视剧,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是对少年的我的一个启蒙,你在书里面得到人文的启蒙是一回事儿,在一个影视里面,在一个正常的影像里面,在一个正常的"还原人类"情绪的影像里面,它对你的启蒙和冲击也是挺重要的。
程:我也看过那些电影。
王:像《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
程:《蒲田进行曲》、《W的悲剧》。
王:尤其是《W的悲剧》给我的冲击很大。这些日本电影在人的状况上它是正常的,我相信我的少年时代影响最大的一方面是欧美名著,一方面是日本的电影。
程:小时候是一个比较乖的,还是属于比较反叛一些的?
王:没有明确意识的反叛,只有孤独。我从小身体不好,支气管扩张。
程:是父母的关系?
王:我父亲的遗传。支气管扩张尽管不是大病,但是很吓人。隔一两年复发,然后吐血,大口大口地吐血,呼吸很困难。
程:有死亡的恐惧吗?
王:我差不多十三四岁的时候开始第一次发作,然后每隔两年就发作一次。这个发作期有七八年的样子,在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转换的阶段我其实一直有病,我很庆幸有这种病,它没有真实的危险,但是它给你一个死亡的幻觉,你真是大口的吐血,然后你窒息,然后觉得不行了。我现在是很不怕血的,我太知道血是什么东西了,一痰盂一痰盂的吐。那会儿就很孤独,我大学没考上,就看书,也不管功课。
程:那你有没有复读?
王:没考上我也没有复读。我跟一般孩子的成长是不一样的,一般少年的成长就是好好的上学,然后考大学,我完全是很任性的,就是读自己该看的书。
程:因为身体有病的原因。
王:家里面也宽容我,也不太逼着我说一定要考大学,这孩子在家里看书,不给我捣蛋已经是很不错了。然后就是你可以找分工作吧,其实这种宽容,以及我自己的病痛,像给我自己建造了一个房子,一个很自我、很个性的房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活得很健康,从小因为病痛,因为宽容,我活的很健康。
程:那个时候跟外界、跟世界、跟人群、跟别的人的接触是一个什么样的。
王:我又比其他的同龄人更早的接触社会,17岁我没考上大学,我就去我爸的工厂做做临时工。
程:什么样的工作?
王:汽车厂。
程:你做什么?
王:油漆工。程:那油漆对你身体有影响吗?
王:还是有影响的。我们是第三梯队的,在工厂里面最受歧视。尤其是家长觉得没面子。
程:签合同吗?
王:签什么合同!我就是劳动服务公司的临时工,比民工好一点,什么都干。有时候是油漆,工厂里面别人不干的活,我们也干。
程:工厂里面有没有业余活动?
王:没有,没有业余活动。只是跟着别人上班,上班跟那些同事也没什么太多的来往,回来就是看书。看书写诗,我最早的文学实践就是写诗。
程:你以前说你看一些《世界电影》。
王:我大概高一的时候订的《世界电影》,在我妈工厂里订的,很多人都不知道。
程:那个时代文学是很多人主要的一个精神生活,80年代,喜欢文学的特别多。
王:可是像我,写诗,做文学,顺理成章应该成为一个编剧,但最终还是成为导演,这是一开始就决定了的,我当时隐隐约约感觉到我最终的创作是要靠影像和视听来做。我当时在写诗,写诗写到大概两三年以后,我遇到了一个坎儿,能不能写下去的坎儿。北岛曾经在《上海文学》写了一首诗,然后他写了一个诗的主张,在那里面他提到蒙太奇,他说他写诗就是蒙太奇。当时我很绝望,我觉得我写诗怎么那么不蒙太奇,而他特别会用那种组合,意向的组合,意向的对穿,内部的这种互动,我觉得我怎么那么不会。一个苹果在那儿,我就只会写苹果,我不会通过苹果浮想联翩,以及这个苹果的各种角度,然后用一些淡淡的情节来围绕着苹果,然后又走掉,我怀疑我还能不能写诗。比较苦恼的时候我看到了巴赞,我在《世界电影》上看到了巴赞。这种东西比蒙太奇厉害,就是长镜头,这是现象学的一种东西。那会儿,我还是接触了一些文学的东西,现象学的东西,胡赛尔的东西。我也想确定一种自信,因为这种东西别人都没这么写过,大家都学北岛,当时的诗都是那样的,意向的组合,很少有对一个东西的特别安静的一个专注。后来我就撒开的说,这是我能做的东西,这是我的方法。
程:然后你决定要来学电影。
王:那会儿我相信真分不清楚是以诗来写诗,还是以诗来完成我头脑里面对电影的幻想,我觉得我早期的诗歌里面,或者我所有的诗歌里面,都是在通过一个诗的形式来完成一个我未能达到的电影的梦想,我相信把它结集出版会很有意思。
程:那个时候你怎么样转过来,想到北京电影学院来。属于机缘吗?
王:大概八一年的时候,我是在街头上看到一本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但是看了对我没印象,看了就看到了,因为我是很封闭的,我有我自己的世界,对外界什么电影学院的东西我只是看了一下。
程:后来你考的夜大,还是考的别的?
王:我是直接考本科,90届电影学院老师胡滨那一届,我就来考,当然还有一个机缘在这儿,就是跟陈凯歌他们家的机缘,凯歌他们家在南京有一个亲戚,他的一个姨跟我母亲在一个工厂里面,是那种非常好的朋友。这对我也是一个激励。
程:那你当时考试找他了吗?
王:我当时一直是通过他姨,跟陈怀皑伯伯,就是陈凯歌的父亲接触上,然后我就开始写影评。我们靠通信联系,我看了《孩子王》,看了《黄土地》,就写影评。我记得看完《孩子王》出来以后,太阳很好,我都能记得那天的太阳,真的,很刺眼的阳光,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一部杰作,我当时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程:你想改变当时的工作环境吗?
王:很难讲,对一个独处的青年来讲,他没有那么明确的目的,因为那会儿我更加的孤绝,我的孤绝就是说,我跟原来的工厂也闹矛盾。后来我正式进入一家工厂,那个工厂造电视机里面的磁芯材料,成天三班倒,无论白天黑夜全是三班倒。那会儿我考过一次电大,新闻专业。因为要上课,是上电大,还是上班,我跟车间领导闹矛盾。我觉得不是我的错,然后车间领导要让我承认这个错误,承认这个错误然后大家就好办了,也就是我要给车间领导一个台阶,当时,我就是想从工厂出来,找不到台阶,只要不承认错误,正好给我离开工厂找到一个好的借口,同时觉得我不应该承认错误是对的,我就索性闹到底了,这样就离开了工厂。你要知道离开了工厂以后我还必须工作,生存,我再次沦落到一个更底层的街道工厂。
程:在那儿做什么?
王:那真是刷油漆了,因为是街道工厂。工厂把废旧的铁管子买进来,然后我要把它擦得锃亮,擦成新管子的样子,就能把旧管子变成新的暖气管道,做完以后再刷油漆,我就砂那个很锈的铁管子。
程:用铁砂纸。
王:就是铁砂纸,把它擦得锃亮,然后弯起来,然后切割,就是手工切割的那种东西,然后再刷油漆。
程:那种体力活你能承担吗?
王:我那时候有个习惯性的动作,很累的时候我习惯性的吐一口痰,吐在手上,看它有没有血丝。在街道工厂里面每次干很重的活我都会吐一口痰。这时候我接触了一些很底层的人,劳教过来的,社会混子,什么人都有,聚集在街道工厂里面,打牌,打麻将,是在一条小街道边上,很市井味儿。那段经历给我印象很深,一身穿得很邋遢,凉鞋上全是油漆。我们这个街道的上级是研究所,那些刚分到研究所的漂亮的女大学生就从我们面前走过。我当时也带一副眼镜,眼镜上还有点儿油漆。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大学生,每次从那儿走,我就在路边刷油漆,真是像电影,你真的是不敢抬头,有的时候也坐同一辆公共汽车。
程: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年?
王:有一年多。我在劳动服务公司呆了有两年多的样子,然后到一家正式工厂里面,呆了也有两年多。然后街道工厂里面呆了有一年多,总共6年多的样子。
程:那后面?
王:后面又是生病,就不工作了,真的生病了。
程:都是谁照顾你?
王:家里人。我是87年生病,然后我八八年有一次出走。
程:是什么原因?
王:我受不了啦。我觉得是一个负担,家里人不说这些,但是我感觉到是个负担了。
程:去哪儿了。
王:我去了广州。
程:拿了谁的钱?
王:借我一个朋友的钱,没有多少,那会儿三四百块钱就可以出去了。
程:我也出走过,高三的时候,我偷偷拿着妈妈柜子里的钱跑到武汉去考电影学院了。
王:那时候出走很有意思,可能那次的出走决定我将来是搞电影的了。我从两本《世界电影》里面,把安东尼奥尼的剧本撕下来,把费里尼的《道路》的剧本撕下来,然后把那些我认为重要的电影理论文章撕下来。身上带的东西我想带少一点,我真的没带书,我身上所带的东西,就是我认为要看的东西。我居然带的都是这些,然后自己写了一大堆诗,我其实是想到那边去写诗。那会儿到处都是诗歌组织。
程:1987年深圳搞了个"崛起的诗群"。
王:广州那会儿也有一拨。
程:你找到他们了吗?
王:找到他们了,中山大学的紫荆诗社。在中山大学混了一段时间,我那天跟崔卫平还在聊这个事情呢。
程:怎么混的?
王:那会儿是个夏天,我住在院子里面。
王:88年,那会儿真是很多毕业生,我先是在亭子里过夜。我一个人就睡到那儿了,我住在亭子里面的时候,有很多大学生,很青春的要毕业的大学生,一对一对的抱着哭。我在那儿睡觉,枕头底下还有刀,尽管我知道我不会使刀,但是你住在外面肯定要有一把水果刀什么的。我就听他们说话,抱着哭的一些情侣要去远方,毕业的情侣,那才是人生啊,我觉得真好,很有意思。后来觉得冷,我就开始到他们的自习教室去。
程:不害怕被认出来吗?
王:我也带着眼镜啊。我先跟他们一样进去,之后就开始看书,我就带着那点东西看,真正的看了几个电影理论。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样子,没东西看了,就在那儿胡思乱想。到了教室还必须装着看书,可我身上仅有的东西就是几章破纸。自习时间结束铃声一响,大家下楼的时候我就开始躲进厕所了。基本上等大门锁起来,我才从厕所里面出来,然后到教室。我真的睡在那儿了,大概睡到第五天,还是第六天,一道灯光唰的一下就照过来。我说宿舍太热了,这儿凉快,我在这儿睡。
程:他不知道你不是本校的学生?
王:他相信我是本校的学生,因为太容易相信了,我长得就像学生的样子,他说不行,你得回宿舍去。(笑声)我出走的原因是当时我自认为我身体不好,为什么呢?有很烦燥的东西,一个是身体不好,还有一个可能是烦燥,然后你肚子里不舒服,可能是因为神经性的那种胃痉挛,肠胃很不好,好像还带点儿血。
程:我感觉你可能还是隐隐觉得未来要变化,自己要到另外的地方去。
王:对。我回到家就是1989年。
程:上班了,上班了吗?
王:我这么跟你讲,我从来都没有立过志,老实说是很奇怪的,你要知道那会儿已经25岁了。我立志要做个作家或立志要做个什么工程师吗?我在这之前都没有设计过,就在底层,底层里面的一个小书生。到了1989年以后,我觉得要努力了,就是说要提起劲来了。
程:老大徒伤悲了。
王:真是。1989年以后我觉得该努力了,该提起劲儿来了,该找到一个方向了,然后开始立志,立志电影,因为文学成不了志向。老实说那会儿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文学梦想,写写就行了没有必要发表,我就仅仅是立志于做电影,但是那会儿还没有立志做导演,只是说立志要跟电影有关系。
程:进入这个行业。
王:对,进入这个行业要跟电影有关系。我从1979年开始就看《世界电影》,那些西方的电影我已经大量地在纸上看到,我说我要到某个地方看看他们的胶片,不能只是读了。1990年去考,我专业课都过了。然后又去凯歌他们家,见到了陈怀皑伯伯,我也见到过凯歌,那会儿他还没有拍《霸王别姬》,聊了聊。回来以后我经常给陈伯伯写信,我记得1990年那会儿陈凯歌还在拍《边走边唱》,我跟陈伯伯通信的时候,二十几页的纸,写对《黄土地》的认识,对《孩子王》的认识,尤其对《孩子王》我特别喜欢。我那会儿26岁了,再收拾文化课是不可能的。我到北京来了一次以后,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到北京来,只要我跟电影有关系。
程:1991年你上的夜大。
王:对,1991年我就考进来了,那是很容易的。
程:夜大上几年?
王:3年,我其实在电影学院呆了4年。1995年还在电影学院晃。
程:那几年学习,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王:我终于逮了个地方看电影。
程:拍东西吗?
王:不拍东西,那会儿不拍东西,你知道我那会儿学的是编剧。
程:就是想当一个好编剧。
王:也没有想,我搞不清楚。没有明确的目的说要当一个编剧。我要当编剧那会儿就写剧本去了。
程:写小说?
王:小说我也没有专门去做。95年,我当时在陈凯歌的工作室。写了《南方》。就觉得有一种张力,总感觉自己要拍电影了,然后我就开始写故事。片名,演职员名单,然后是导演阐述,什么都有。写故事觉得也找不到钱拍,再写,把故事写好就写成了小说,写的小说发表了。讲一个南方民工到这儿来盖房子,一个寡妇带一个小女儿卖烟,卖烟的时候偶尔也卖一点南方的槟榔,他是个南方的民工,看看有槟榔就认识了。讲这么两个人,一个北方的寡妇和一个南方的民工,他们在北京的一个生活中的故事。
程:电影的志向终于确立了。
王:对,95年开始我就立志拍电影,一直到2000年,这五年当中给陈凯歌做了三年半的助手。
程:做助手之前做什么?
王:承包电影学院的一个办公室,干了几个活。
程:干些什么?
王:给《东方时空》做节目,做比较大型的节目。
程:什么节目?
王:真事再现,讲到自己真正的职业生涯,我第一次拍片用的是两台机器。武汉那边10年前有一个"英雄"曾经跳下水救过小孩,哪知道跳下去以后,这个小孩是在水里面玩,故意喊救命救命,然后这个人就受伤了,瘫痪了。10年以后大家重提这个事,他到底是不是英雄。要把当时跳水救孩子那一段拍下来,我是去拍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拍电影的一段。看到一个孩子跟妹妹玩耍,他故意跟他妹妹说要沉入水了,然后上面3个青年工人看见了,一个工人是直接跳下去的,两个工人是趟水下去的,直接跳下去的瘫痪了十年,我拍这个场面。
程:那会儿你生活基本无忧了。
王:对,都是几万块钱的活,然后我还接配音的活,一个晚上挣三四千,那会儿还行。郝建的办公室在斜对过,我俩那时候老在一起聊天。那会儿挣到一笔钱,觉得这笔钱能让我过三四个月,我就不去接活了。我读了一个夏天的书,郝建知道,我是用他的借书证借的,重读一些世界名著,我预感到我得有个动作了,这段时间真是读了很多的书。
程:两三年前就开始做这个电影?
王:对,然后在电影学院承包的时候有一个机会我就到凯歌那儿了。
程:你给他做助手。你自己的事情怎么做?
王:挤时间。做后期还是比较轻松的,晚上的时间是自己的。《荆轲刺秦王》我们拍了3年,准备工作两年,两年全是筹备期,这个筹备期晚上的时间是我自己的。白天再进入一个电影的非常严格的操作空间,你知道我们在设计巩俐的耳环时,那个耳环因为有一个特写,我们讨论了3个小时。包括一个勺子,能讨论两三个小时,关于它的形状。
程:他做影片很认真。
王:拍一部当代的戏,服装、道具,它的色调,它的形状不会考虑那么细,但是这个古装戏里面,它的调子,色调的搭配,各种的形状,就非常的细。我相信我在电影学院只是学看电影,那么到凯歌这里是学做电影,非常扎实地做电影。
程:你自己把它当成对你的训练。
王:我觉得是学习。是电影元素的训练。
程:这个片子出来的效果没有达到他想要的那个东西,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王:我觉得这反而是陈凯歌真诚的一面,体现他的真诚与直爽。
程:他做东西是很认真,但是做出来之后反响远没有那么理想。
王:对于一个创作人来讲那是另一回事。
程:那你呢,你有失落感吗?
王:失落感肯定是有,说实话那么辛苦,那么认真地做这个东西,然后它的反响不一,我觉得我真的是有一种失落感。但是同时我又觉得,你大凡想做一种艺术的话,那么这种失落感也是包括其中的。
程:你会不会拍这么大的东西?
王:我其实心里面一直期待有一个古典主义的复归。我少年时候常沉溺在一些古典文学里面,我原来期望中国真正的古典主义的东西、古典主义的核心在第五代导演身上能够复兴,但是我似乎能感觉到这个复兴没有在他们身上发生,我希望我能找到这样的复归感。
程:你觉得那种古典的复兴可能性有多大?
王: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来讲他所谓的复兴,无非就是对中国的古典的东西,对古典的人文状态,对古典的生存状态,以及它的美学状态的关注。
程:你的古典是针对现在这个时代来说,还是指一个美学概念?
王:不能分开的。
程:我觉得可以分开,包括《三国》,包括《水浒》,包括中国的古典文学。而古典美学我觉得和古典作品不完全一样,就像现在的文学现象,现代文学里面的张爱玲其实是跟同一期的作家不一样的,她有很多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感觉。
王:我觉得那肯定是基于一个,基于你现在所处的位置对古典的一个重新创造。
程:所以我比较相信陈山老师说的,艺术不是一个进化论的东西,就是说它不是从古典到现代这样线性发展的。那时候非常好的东西它能够贯穿下来,但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糟粕,现代也是同样的,现代也有好东西,也有很多垃圾。
王: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讲,他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真正的目的不是拍一个东西,拍一个近的东西,拍一个远的东西,真正的目的是你可以拍一个近的东西来印证你现在的自我,拍一个远的东西来印证对你作为人的重新的认识。你可以拿我一半的童年的往事来印证我现在的人格,我的立足点在什么地方,那就是说我想拍古典的。可能我意识到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情怀,更深广的情怀,那么可能不是剪一段我的童年往事,剪一段我的现实遭遇,就能够把这种东西满足了。古典也好,古典的复兴也好,都是在满足,在推动你现在的自我。但是我觉得现在人的可贵,或者说伟大就在这一点,他比上一个世纪的人更伟大,他已经确认上个世纪没有上帝,上帝在上个世纪就死掉了,但是你还在这里。
程:第一次看《安阳婴儿》是在郝老师家,还有张献民、崔卫平,大家都沉默了很久,我同样如此,这部影片所展现的在日常生活中的中国人的生存现实(而不是状态)就这样与我们面对面地呈现出来。它最重要的部分不再仅仅是它的结构、它的影像、它的机位。
王:我希望这是一份独特的中国底层社会人民生活的影像文献,构思和拍摄这部影片我都希望建立在我对他们现实生存状态之上的精神压力的触摸。是关于他们"当下处境"的速写;是关于他们"活下去"、或"死去"的诗;是他们扭曲而顽强的"存在";是绝望与希望的名字。《安阳婴儿》是我对中国,对中国现实的体认。我记得创作《安阳婴儿》之前,我在搞一个"香格里拉"题材的电影,我的一次成都之行,因缘际会孕育出了《安阳婴儿》。我听朋友讲到当地的下岗工人和自己的老婆一起卖淫,妻子在家里接客,丈夫负责收钱,在这里边,震撼我的部分是他们对这种扭曲生活的理所当然的接受。我开始构思《安阳婴儿》。
程:跟我当初知道一位朋友在夜总会跳艳舞,她的老公每天都去接她时的惊愕一样,很多年以来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东西一瞬间就坍塌了。你的故事中的中国现实跟《小武》中的中国现实已经不一样了。《小武》是中国人面临一个大变化时期的徘徊,是"怎么办"的彷徨和疑惑。而《安阳婴儿》中,小武所面对的一切正在成为"日常中国"的一部分。小姐、下岗工人、黑社会老大,他们不再是边缘人物。
王:这些人成了我的镜头所驻足凝视的全部。影片里有两层救赎,一个是个人的救赎,一个是世界的救赎。
程:救赎是需要途径的,当我们作为人的部分被不断取消之后,我们就变成了"无",也无从救赎;而你的人物似乎并不想自己的生活被完全取消。他们因此而顽强地活着。
王:所以我最终没有采用剧中任何一个人的视点来结构这部影片。
程:影片中有很多长镜头,我感觉得到你在凝视他们,你的镜头没有拒绝他们,而是在接近他们,抚摸他们受伤的内心。有些东西真是很宿命,于大岗为了留住这个孩子,动手杀了黑社会老大,可他并不知道身患绝症的老大已经活不了几天。而还有一种妥协的态度就是,无钱无女人的于大岗完全可以放弃这个跟他无任何血缘关系的婴儿。也就是说只要他让自己变成一个被取消一切的"无",他就不会被判死刑。
王:《安阳婴儿》是一部悲剧,不只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悲痛的故事。
程:我相信每个作家,每个导演,不管他们如何掩盖自己,他们的作品都是文如其人。
王:"导演双周"的选片人克利斯汀认为《安阳婴儿》是特别诚恳的电影。
程:不像有些中国电影,那些电影中的那些人、那些事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你始终是在场的。可是你的现实主义态度又跟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有很大的不同。
王:应当说,这是一部作者电影,它以几乎(除了影片结尾处的肩扛镜头之外)完全静止的镜头,冷静地"凝视"古城里无奈地生活着的人们,中国平民社会生活的多种因素聚集在这里:下岗工人、警察、妓女、黑社会、弃婴、监狱等。这里有的只是这些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我只是想展示一种生存状态的存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就像萨特说的那样。
程:当你的摄影机长久地凝视这些底层的人的时候,他们苦难的心灵就会飞扬起来。
王:影片的结尾,我不想让他们淹没在无边的黑暗之中,女主人公去监狱探望被判死刑的于大岗,于大岗惟一的嘱咐就是要把孩子养大。冯艳丽去第一次和于大岗见面的饭馆吃了一大碗面条,她多要了一碗,那是给于大岗的。回到于大岗的住处,冯艳丽自己也因为卖淫而被警察追捕。这场戏,是摄影机第一次运动起来,非常的悲伤,她无路可逃,抱着接连失去生父、养父的婴儿四处逃窜,随手把婴儿给了一个路人。可最后她还是被蹲候多时的便衣警察抓住,紧接着她被装上囚车。火车进入黑暗隧道的时候,奇迹发生了。那是摄影机第一次运动起来,悲伤而激越。这时,观众看到冯艳丽逃跑时,接过婴儿的是于大岗!
程:于大岗不是即将临刑吗?是什么力量让于大岗挣脱叙事的可能而将自己的救赎之手伸向那从一出生就没有得到过呵护的安阳婴儿呢?我想,你的影片对人性尊严的肯定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最高点。你对日常中国这些普遍存在的关怀贯穿影片的始终。可以说,从《小武》到《安阳婴儿》是中国独立电影的一个飞跃。
王:我需要表达,表达我的认识和一种体认,我对中国的认识实际上是个自我的体认,不能说认识了中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拍了一部电影,无非是说,上帝让我有了一点拍电影的技能,我通过拍电影的技能,传达出我心里的东西。因为几个小说写出来以后,我觉得小说的力量实在是太微薄。
程:你的影片很有力量,尤其是结尾,由于有了那样的结尾,整部影片都飞扬起来了。很多影片容易懈,包括不错的影片,可你的影片一直在往上冲。
王:达到苦难的顶点。戛纳的观众将影片最后抱过婴儿的那双手称为"上帝之手"。
程:苦难成了剧中人的救赎,痛苦本身拯救了他们。
王:在悲剧中体验快感。这是一个悲剧,这是他们给我的评价,而不是一部情节剧。有一个记者问,你用简单的方式来拍悲剧,矛盾吗?我说真正伟大的悲剧就是简单。
程:中国就很少有悲剧。
王:中国很难产生悲剧,只有悲伤的故事。是否是悲剧,要看你在体验你的悲痛的时候,有没有升华的东西。
程: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最大的悲剧是,每个人都在退让,都在放弃,把你所有作为人的全部东西,我也不要,你也不要,他也不让你要。直到你退到"无"。但是《安阳婴儿》不是这样,他们都在"要",要回自己应该有的东西。是在真正面对现实。
王:我觉得我跟你讨论的话题不仅仅是电影。我的小说和电影中都潜藏着这个涵义。面对自己后走出去,还得还原到一个土地上。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恢复真实和面对真实以及在现实中升华的问题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创作过程。以前我们谈的是一个恢复真实的过程,今天我们涉及到在现实中升华的问题,使现实有了一个悲剧感,中国的影视真到了恢复我们真正的视觉和听觉的时候了,这个在中国的意义要比在西方的意义大。
程:我们从小就被蒙住了眼睛,塞住了耳朵。
王:其实要恢复的东西是一个很平常的力量,不难,但是这个平常的力量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敢去获得的,它很平常,你安下心来,坐在这儿,说,只相信你自己,我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然后确认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这个意义在中国远远大于很多知识分子提出的重建人文,以及革命,以及变革,以及理想,以及王朔是个东西,调侃是个东西,黑色幽默是个东西,远远大于这些东西,一定要安静,一定要有耐心,你看到了什么,自己告诉自己,并且确认,这是最重要的。
程:所以你看到了《安阳婴儿》。
王:我必须在这里驻足观望。我是一个意识到这个地方的人,我必须在这儿,我必须长时间的绷着,我的摄影有时都绷不住了,说你太长了,我说长也要绷啊,并且我告诉你我还得重拍一个,下一个机位就是影片结尾的那个机位还是这个位置,一样的驻足观望,两次驻足中间,我们在体现它的变化发展,它的重复和发展、它的恢复和面对。我相信戛纳那边的观众之所以能感动,不是基于人类真正的本真意义上的沟通方式的话,他不会被你一个普通故事感动。说故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建立起来的真正确立在人本立场上的联系,才会让人读懂你的故事,才会跟你一样去静静地看和听。我一直在通过这样的一种凝视,探讨一个日常中国在哪里,中国生命的本象我们从来没有揭露过,我想用最简单的方式,面对中国真正的日常生活,以及在这个日常中间流露出的悲剧感。
程:这也是《安阳婴儿》最纯粹的地方。
王:以电影的手段来述说中国的现实意义很大,因为中国的文字被侵染了很多杂质在里面,一个知识分子铺开纸写文章的时候,哪怕是一个很前卫的知识分子,他的文字也被侵染了很多,用汉语来进行中国现实转述,它的不真实方面来源于文字本身,而这点是很多知识分子没法意识到的。
程:电影的视听也要清洗,电影也同样被侵害得很厉害。一些导演一不留神拍的电影,就让你想到童年时看的"文革"电影。为什么我会在这些电影里看见童年时看到的视象?但是你的《安阳婴儿》却如此的独立,没有被侵犯,也因为独立,而如此幸运地维护了自身的完整。
王:如果上帝赋予了我面对真实的能力,那我觉得应该把这个能力持续下去。
程:《安阳婴儿》在戛纳得到的认同是什么样的呢?
王:戛纳的第三场是在普通剧场为普通观众上映的,他们是买票进去的(真正的影迷到戛纳来他们拿不到那种观摩票,包括当地的居民)。那是一个稍微偏远的影院,不在海滩。戛纳双周的主席要我去跟观众见面。在车上的时候,我有点忐忑不安,因为前两场一个为记者,一个为专业人士放映,他们对这样的艺术电影至少是能接受的,能通过你的艺术通道接受你的艺术思想。但是面对普通观众,你的思想是普通的,内容是普通的,能不能接受,我没底。我们进去的时候影片还有半小时就要结束。我说我能不能进去看看坐了多少人,他说已经坐满了,两个通道都坐满了人,我不相信,我进去看了看,真的坐满了,地上也坐满了。那一瞬间真是感动。放完之后我们进去,跟别的不一样,我们不是站在台上,而是坐在台沿上,跟观众交流,非常好的交流,普通的交流,甚至一个小孩问我,你们花了多少时间拍这个电影,我说21天,他们不相信,他们还关心那个冯艳丽的命运,说这样一个妓女的命运,在中国是否普遍。问了很多的问题,我觉得那次跟普通观众的交流也是我在戛纳感动的一次经验。我后来就在想,法国是一个很优越很舒适的国家,每天那些人都好像在度假,对来自东方一个国家的这种苦难,他们怎么能有那么深切的理解和认同。当我回来之前,在巴黎,戛纳双周的主席特意到酒店来看我,他说现在的电影二十几个镜头说不了一件事,你的一个镜头说了50件事,他们特别能够知道,你真的用心没用心,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
程:没有得到金摄影机奖,有遗憾吗?
王:没有遗憾。我心里很充实,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作者电影,作者立场,作为一部纪实电影,尽管是我用一年完成的,从写剧本开始,但我相信这一年的底下是我十几年的积淀,我把它表露出来,它对我的回报不是说拍了部电影,就成功了,一点没有这个意思。我表达的不是个人的东西,真的,我表达的是中国的普遍。
程:是要吐露东西。
王:是的,在拍《安阳婴儿》之前我是有机会去拍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包括写剧本什么的。很多人都认为应该有一个战胜困难的姿态,我没有,我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战胜困难的姿态。我觉得我的选择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的,像我的呼吸一样,要不然就不拍电影了。我选择了这样的生活,这种生活本身就包括表达这样的东西以及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拍你的电影,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程:不害怕非主流电影腔这样的评论?
王:你不能说一个东西,不是这样子的,就是那样子的,在我的逻辑里面没有。我只在我自己这儿,我自己在什么地方不在你的视野之内,你拿你的视野说我是非主流腔,你凭什么说我在你们的对面?我不在他的对立面,我觉得他看不到人。我的创作是很自我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不在你以为我在的地方,我只是在做我自己的事情而已。
程:你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王:对。做这样的电影,真的要考虑的东西,要感觉的东西很多,你的路是那么的多,那么的长,这已经让你足够了,我不会在意很多东西,就像一个做苦力的人,他不会在意一个喝茶的人,因为每天有那么多的苦活要做,这个苦活可能在于你更多的苦苦的思想,我觉得拍电影真的是一个苦力。
程:我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张献民说这个电影是"左翼"电影,你怎么理解?
王:他这个"左翼"是什么概念?
程:我觉得它的"左翼"是针对现实来说的。
王: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起源,其理论背景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但是作为我来讲,我没有抱着"左翼"的立场和观点来拍东西。我相信我青年时差不多二十多岁的时候,也一度对马尔库塞的东西非常欣赏,很仔细地读过他的东西,但是从1995年以后,我开始接触基督教,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的真》真是给我很大的影响。1995年之前,如果我要拍这个片子的话,我可能跟你说,这可能是"左翼"的冲动什么的,我相信1995年以后,2001年以后更多的是跟上帝的接触有关,跟耶稣有关,跟受难、以及受难的人类,以及悲悯有关。
程:你还是想去救他们。我说的拯救不是说你去解救他于水火之中,而是在道义上,在情感上表达出来的这种爱。
王:我相信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激情,我相信它是一个宽恕,一个容纳。我觉得不要装扮成在为他们去呐喊,他们不需要你这一声呐喊,你这一声呐喊对他们没有什么作用,我觉得做得最好的一点就是我与他们同在。可能我现在说的不太多,我觉得30岁以前我是很能说的一个人。
程:就是说行动最重要?
王:也谈不上重要,我不知道什么是重要。其实我是跟摄影机一道去认识很多事情的。摄影机架在那儿的时候,我真是不敢轻举妄动。
程:我很佩服《安阳婴儿》里的冯艳丽,她用身体去生存,别人用职称、学历等等很多冠冕堂皇的东西去装扮,而她是直接用身体去跟别人交换,她最直接。
王:对。她们最柔弱同时也是最坚强的。你看现在这些小姐,她们真的是最柔弱,她们仅剩自己的肉体。夜总会里面都是些什么人?各种面目、各种强势的人,这些小姐就只有肉体。然后你到民间看那些下岗的人,他们原来还是工人,现在自谋生路,我觉得真是到了底限,是他最苦难的深渊,但他不觉得,他觉得这个是我能忍受的,他只要不死,他觉得就能忍受,我能过,一点一点的,这种力量是可尊敬的,真的。
程:必须靠自己。
王:对。所谓的真实。中国真正的属于土地的那个力量是很感人的。也说不上是感人,用感人都觉得小,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去学这些东西。我喜欢到底层去,我是从底层来的。
程:这个原始的气,你感觉到那种力量,它很博大,很厚,你在那儿吸取你的东西。
王:《安阳婴儿》为什么有力量,是我有幸。安阳整个的节奏,它整个的质感、质地,是有东西的,你能够感觉到在中国的底层有一股场,这股场是"悲怆",但它是有力量的。
程:有韧劲。
王:有韧劲的,在那儿,黄河边,一个城市,一道城墙,这些人就这么活,你不能说他们没有快乐,他们自然也有痛苦,但他们更有的是一个力量。我拍《安阳婴儿》的时候每每被这种力量感动,我带着摄影机到那儿的时候,就觉得我在被一种东西折服。真的是这样的,你凭什么进去?你凭什么给他安排情节?你凭什么给他安排对话?你凭什么说你的主题是拯救他们?
程:他们不需要。
王:你又凭什么说你的立场是道义的?我觉得不是,对他们的认识,对这种力量的认识是你要做的,你要学习的,从艺术意义上,是对这种现象的认识。
程:你准备的新片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王:有关底层的工人生活。
程:什么样的工人?
王:矿工。现在还在故事阶段,我还不好去多说它。我特别在意拍一部片子的时候,你一开始跟它的距离,我在找跟它的距离,这个挺重要的。跟它的距离就是态度,这个比拍的时候要重要。这种东西比找一个故事要难得多,它需要你很安定很稳固。
 动感短信、闪烁图片,让您的手机个性飞扬! 动感短信、闪烁图片,让您的手机个性飞扬!
短信世界杯站:新闻、游戏、动感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