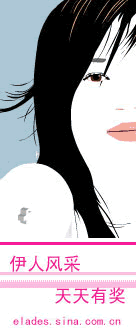|
贾樟柯:在"站台"上等待
对话者:贾樟柯
程青松 黄鸥
程:《小武》和《站台》你更喜欢哪个?
贾:(沉默,考虑中)
黄:我喜欢《站台》。
程:你觉得从《小武》到《站台》有什么改变?
贾:没变化,接着拍,《站台》这个剧本大概是在1995年或者1996年开始的,那时刚刚开始拍短片。实际上《站台》应该是我的处女作。我想着拍电影,我将来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站台》。从1990年以后我从家乡汾阳到了太原,也就20岁,学画,离开原来那个封闭的环境,到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里头以后,慢慢地开始,汾阳的那些人和事变得比原来要清晰很多。后来1993年又到了电影学院,1995年写剧本的时候第一个想拍的就是80年代汾阳的生活。因为这10年是从1980到1990年,正好是我自己从10岁到20岁的过程,这个过程我觉得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成长,开始懂事,开始有自己的生活,开始有自己的选择,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正好是一个自己成长里头最重要的阶段。我不管别人对80年代印象怎么样,我自己觉得80年代对我来说是非常动荡的,是非常激动的10年,为什么说它动荡,因为很多信息,很多人和事情都非常迅速地变化。比如说,县城里的摩托原来只有邮局送信的有,邻居几个孩子经常站在马路上聊天,有个比我大一点的哥哥,看着就非常羡慕,说要是我能买上个摩托,那我就满足了。然后他这个话没说几年,他就买上了。可能就三四年后,说明经济发展非常之快。比如电视机,就像《站台》里面一样,大家都是排队到单位里去看,公路局啊,公安局啊,税务局啊,畜牧局啊,只有这种机关的办公室有,但是很快就家家户户都有了,你每天在街上都能看到有人在房顶上插天线,变化非常之快,你真的能经历一个日新月异的生活。那时思想也慢慢在打开,我觉得在《站台》里面有两个角色,一个是4个年轻人成长的过程,另一个就是文化。
程:你拍完《站台》后好像又回去拍过好多的镜头?
贾:补拍了一次。结构上的东西,因为我剪接的时候,废掉了原来的结构,重新来。
程:原来是个什么结构?
贾:就是很自然的那种叙事,后来我找到了那个进城出城的结构,就去补拍那个镜头。
程:这样的结构使得《站台》很具有史诗的格局。它跟80年代是血脉相连的。你在《站台》里用了很多80年代流行的歌,还有80年代演的那些电视剧和电影片段。你为什么把你的这些人物放到80年代的"站台"上,他们在翘首盼望什么的到来?
贾:《站台》里面开场的歌《火车向着韶山跑》,那是我姐姐最擅长的一个节目。那个时候她是学校宣传队的宣传员,拉小提琴,我第一次见她演出,她一个人站在那儿拉,别的人坐在木头板凳上表演。后来很多节目都是这样的,包括电影也是这样的,革命文艺嘛,非常封闭的状态,然后慢慢开始有通俗文化。最早听到这种音乐的,就是街上的那些混混,他们有了录音机,就在街上放,录音带也是走私进来的,刘文正啊,邓丽君啊,张帝啊,都是那个时候的,慢慢大众文化传到汾阳这样的地方以后,你就觉得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它没那么简单,不单是一个歌的问题,是一种新的生活,对我们来说,有很多东西,所有这些东西变成一个经验以后,我就想去做一部电影。一开始我就想拍这个东西,当我剧本写完之后,我就找这种拍电影的机会,最初我只找到30万,有一个公司,叫做"胡同制作",他们能出到差不多十几、二十万,山西我又找到一部分钱,这个条件我远远没有办法拍《站台》,我就拍了《小武》。规模非常小,成本非常低,很灵活,也就是用16毫米拍。《小武》完了之后,制片环境对我来说突然变了,很多投资人在我后边追。后来《站台》的剧本在釜山拿了首届PPP电影计划的那个奖。我的摄影师余力为懂法文,又拿到了法国的南方基金。这个时候外部投资环境对我来说相当好,大大小小的公司,包括法国百代这样的大公司也特别有兴趣。也包括一些很小的公司,后来我就选择了日本的北野武最新成立的公司。我选择他,一方面是认为一个导演他那么成功之后,还有兴趣投资给年轻人,另一方面他公司里找我的那个制片人,监制了侯孝贤的3部电影,包括《南国,再见南国》、《好男好女》和《海上花》,我热爱侯孝贤的电影,既然他能够长期跟侯孝贤合作,肯定是一个很可靠的人,最起码是喜欢这种电影的制片。然后我们就开始合作,我觉得我在电影这个行业里是很幸运的,从拍短片到想拍长片,到拍了长片再到拍《站台》,基本上没有什么挫折。相对来说是非常幸运的,没用那么多时间去找钱、筹钱,还有我的幸运就是我的两个制片人,香港"胡同"的李杰明和日本的矢川尚三,他们给了我完全自由的创作,《站台》我原来在合同里签的是2小时40分的电影,最后我的导演版本是3小时10分,多了40分钟,他们看了我最后完成的剧本之后,已经知道不可能是2小时40分的电影,大家都没说什么。我记得日本制片说得特别好,他说既然导演觉得有必要用3个多小时来展开他的故事,那么就尊重他吧。因为我非常清楚,这样的长度等于说你拒绝了商业,放弃了商业上成功的可能性。不是说完全不可以放,但是绝对不会收得好,因为这个长度你让一个普通观众坐在影院去看你生命经验的过程,西方的观众、国外的观众是不是有这个兴趣,耗费这么长的时间来了解你的电影。这完全是一个挑战。
程:拍摄好像也消耗了很长的时间。
贾:我自己是完全疯掉了,越拍越长,很多东西都在现场改、现场加。我们拍了3期,第1期为了抢秋天的景,只拍了3天,那3天很快乐,很轻松。以后真正拍摄是到1999年的冬天,那个冬天非常痛苦,刚开始是沙尘暴,我们因为沙尘暴停了一个星期。有一天我看景的时候,就看风把那个电线吹到一起短路以后,一个火龙沿在电线在跑,吓坏了,怕触电,根本没法工作。工作人员差不多有六十几个,大家呆在旅馆里头,一星期就那么耗着,这对摄制组来说,简直是一个灾难,人心惶惶的。沙尘暴过去以后,是我们电影里头要求有一些雪景,老怕不下雪,因为1998年的时候汾阳一年没下雪,结果是一场接一场,除了雪景没得拍,因为你不接戏,然后所有能改成雪景的都拍了。然后大家坐在那儿等啊,等雪停了融化了再接着拍,这些困难让我觉得拍摄特别漫长,实际上整个用了60天的时间,但是感觉过了半年一样,所有的人都觉得太漫长了。在这么漫长的一个创作期间,不停地改,改的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原来剧本里面的人情世故都介绍得非常清楚,比如说尹瑞娟这个女孩,她后来干嘛了,为什么变成一个税务员,前因后果都有。但在实拍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我不想拍了,我觉得叙事有问题,我就停掉。我觉得应该改,因为一个县城里的女孩子,不管是女孩子也好,男孩子也好,她生命过程里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那些事情,谁都知道,而且也没必要交代,那些不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人和人的相互了解,你又能了解多少?我家在宿舍区,我们后面的一排楼里有个女孩,有一天我突然看她该上学的时间不上学了,觉得很奇怪,又过了几天,她穿了一个邮递员的衣服。我就明白了,原来她是不念书了,当邮递员了。她到邮局工作,她为什么不上学,为什么不上学之后没去当售货员,而是当了邮递员?你也不知道。但你觉得一个人的命运就这样在变化,生命的过程就是如此。所以我一下就觉得应该这样拍,我不管因果,我不去说她为什么要这样,我都去掉了,就变成了电影中的人和事都在发生,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也永远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们都接受这样的后果,接受这样的生活,这是整个在拍摄过程中改变最大的一个方向。《站台》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不单是因为它搬走了心里的一个石头,那个年代,真的有段时间我觉得不把这个片子拍了,我没有办法去想象别的片子,觉得总是个事儿,不办完它我没法开始新的事情。这个对我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还有,它使我真的在一个工业机制里面去工作,以前我拍《小武》的时候都是好朋友,15个人,睡起来就拍,拍累了就睡,什么压力都没有,运转非常灵活的一个摄制组。到《站台》的时候最多有100个人,怎么管理这100个人?而且我拍《小武》的时候没有服装,没有道具,很多部门都没有,突然多了这么多部门,你怎么控制这些部门,怎么来跟这些部门沟通?人多了事情也多,你怎么样来保证精力集中在创作上,你怎么样信赖你的制片,这些事情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都是一个挑战,我自己也是通过《站台》学了很多东西。因为我从来没有跟过一个摄制组,从来没有给人家当过助手,一上来就当导演,真的是边拍边学。以前我是很恐惧工业的,我觉得工业对你的改变,还有工业里头人的工作方法,他们的审美,包括他们对电影的认同,我对这些都有一种恐惧。经过《站台》之后,只要你相信你自己的电影,相信你自己的剧本,那么工业里头的人,自有他的好处,他们会帮助你完成很多事情。比如说,《站台》的道具量很大,要在短时间内收集这么多道具,是很难想象的。但我的道具师非常专业,他也在慢慢了解我,比如说我是一个凑合事的导演,他就完全会用凑合事的工作方法来工作,但他后来发现我对这部电影这么有感情、这么用心、这么愿意拍这个片子,他也觉得需要相应的工作态度来支持我。有一次我特别感动,有一场戏是大家抢着上公共汽车,我觉得气氛不太好,我说你去给我找几只羊,让旅客抱着,吱吱哇哇的,有点混乱的感觉。道具师回来了,找了一只小羊,一只大羊,我就有点懵,我说你为什么不找两只大羊,要找一只大一只小?他说,一只小的可以让一个人抱着往上走,那羊肯定会挣扎嘛,另一只牵着。我立刻觉得这个事说明他开始投入创作了,他开始琢磨这个道具怎样给这个电影增添气氛。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里,一个导演的能力也是一个经验性的工作,怎么样能够在工业的环境里面来保持自己,你自己要有一个技巧使你能保证你的创作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像《站台》这种有年代感的影片,如果都没有经验,大家都凭着热情,懵懵懂懂去拍,可能没有现在这个样子。对于现在这个电影的规模来说,我们的资金是非常有限的,能完成到今天这个状态,我觉得对我来说意义最大的是,搬走了心头的一个东西,还有就是学会了在工业里面怎么工作,因为你不可能永远在一个业余的状态里面工作。有很多题材是需要工业支持的,《小武》可以完全脱离工业,但是《站台》就需要工业支持。我觉得一个有能力的导演应该学会这些,而不是惧怕它,躲避它。所以这个过程我特别愉快。
程:我觉得《站台》里的服装都非常好。
贾:对,非常好,服装和发型,在《站台》里面你有非常多的叙事上的选择。我最早拍的时候有一个方向这么拍,年代非常明确,让人家一看,哦,70年代了,到80年代了,到90年代了。找一些非常有标志性的东西,比如说服装呀,发型呀,但我后来想,在那个变化过程里,在那么封闭的一个县城,它不可能是截然变化的,也不会突然全体都改变了,有的人还在穿中山装,有的人穿西服,永远是暧昧的、混合的,永远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后来我们的发型、服装和道具都是这个方向。我觉得我的服装师非常聪明,我跟他讲我要那种暧昧的东西,我不要一眼就能看出现在是什么时代。他说他很担忧,他说怕人家接受不到你的信息。我告诉他应该不会,我们来实验一次。他同意这个方案,并且事实证明做得非常好。比如说崔明亮,他的衣服永远慢半拍,张军永远是快半拍,钟萍是最时髦的,尹瑞娟是谨小慎微的,一点点地变化。其实跟工作人员沟通并不难,只要是你生命经验里准确的东西,他会认同,他会随你一起想象。如果有很大冲突,我觉得导演也应该反省,可能是你的想法没法让人家相信。
程:很多人,包括国外的评论都说你非常会指导演员,从《小武》到《站台》。
贾:这个事情换到表演上也一样,《站台》里面除了杨天乙之外都是非职业演员。我觉得除了你学会怎么跟非职业演员相处,最主要的就是你说的事情,他要相信,如果你说的事情,你描绘的这些感受,他不相信,他觉得是假的,他心里没有一个依据,他绝对演不好。
黄:你给他们说戏吗?现场说吗?
贾:我从《小武》开始,工作方法就是,正式拍摄之前,花一段时间跟演员在一起,真是住在一起,每天聊天,一起吃饭。《站台》我们大概用了半个月时间,因为里面有很多歌舞,一边排练一边聊天,每个人讲自己的生活,讲自己的经历,然后我慢慢讲剧本的一个东西,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拍这样一个东西。比如尹瑞娟那个女演员,1977年出生的,80年代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她懂事了,已经是90年代了。你就去跟她讲,慢慢讲她就明白了,你说尹瑞娟这个女孩子,她为什么没有离开这个地方,为什么那么长时间还没结婚,最后为什么又回头找崔明亮。其实她不是没有梦想,但她有很多实际的东西,可能父亲一个人在县城生活,可能父亲有病,甚至她早就觉得你们这样出去转一圈最后还得回来,她可能是一个先知先觉,她一直在生活里长大、寻找,最后没等到。到她二十七八岁的时候,还没等到一个男人,不停的错过,不停的犹犹豫豫,错过了很多人,到最后她还是再回头。讲这样的一些感受给演员,她就完全明白了。因为不单是那个年代的女孩子是这样的,现在的女孩子也是这样的。每一代人里都有这样的人,都有那样的人,在她的生活中也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她就能明白这个事情。还有就是怎么样让演员来相信这个电影的价值。因为你要人家用两三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把人家的本职工作扔掉,跟你到这个地方,跟原来的生活完全没关系的干事情,跟做梦一样。怎么样保证他在60天的时间里,总是充满好奇、新奇、激动,因为他不像职业演员那样知道演员所承担的责任,他们不懂的。他觉得不好玩,他就想走,他不觉得这个有什么损失。
黄:有过这样的吗?
贾:有过。
程:章明的《秘语拾柒小时》中的女演员第一次拍戏,就是觉得不好玩就走了。
贾:拍两天就不干了。他不知道他走会带来什么损失,这不能怪他。但你怎么保证他这样子坚持下来,就是一定要让他信任导演信任摄制组信任大家。而且我觉得拍摄绝对是一个剥削性的东西,演员绝对是非常被动的,你去剥削人家的形体、语言、形象来塑造你的人物。我自己也演,在这里面演那个矿主旁边的那个黑脸的,我自己站在那儿也有点慌,就不要说人家,原来是教师,天天上课,突然拉到这儿要干这个。这个里面就是一定要让人家相信你,有很多技巧在里头,还有很多原则性的东西。
黄:你怎么会想到要上电影学院呢?
贾:因为我中学成绩特别差。你知道县城里面,像我这样的孩子,出路只有三条:当兵,回来分配一个工作;顶替父母的班;还有就是考大学。顶替父母,我父母还很年轻啊,我顶替什么?我不能让他们提前退啊,有时候也有,很极端的。还有一种就是当兵,当兵肯定受欺负。而且我这么矮,那些障碍物,我爬也爬不过去,翻也翻不过去。那我只有考大学,考大学我成绩又很差。然后人家说,考艺术院校。分低。真的是为了一个出路,为了一口饭。
黄:根本就不是为了喜欢电影吗?
贾:我喜欢文学啊。我从上中学就开始写诗啊。
程:80年代文学青年多。
贾:我一直写诗,但是没有一个写诗的学校能够降低分啊。那就去画画,当然画画我也喜欢一点了。在学画的过程中不务正业,我就很生自己的气。我一定要来考学,要找一个出路,那个时候年纪挺大了,25岁,还天天写小说。那个时候是懵懂啊,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动力就是要写小说。也发表了一些。
程:没有一直写下去?
贾:后来就有一次,在我住的地方旁边有一个电影院,那个电影院叫公路电影院,山西省公路局就在那里,是公路局的一个俱乐部。有一天我真的实在是没事干了,赶上放电影,放《黄土地》,已经1991年了吧,进去看,根本就不知道《黄土地》是什么,导演是什么,几毛钱一张的票。电影看完之后,我就改变了,我要拍电影,我要当导演。因为我没想到电影还能这样拍,完全没有,在此之前,我看到的所谓的新电影就是《红高粱》。《红高粱》没有给我这样的改变,是《黄土地》让我决定要当导演,我突然觉得这个最适合自己,然后就开始考电影学院,要搞电影。到现在我才明白我为什么在学画的时候要写小说,因为绘画它满足不了我的那种叙事的需要,所以我要写小说啊。因为你从小到大,县城里面那个生存环境很粗糙、很恶劣,甚至包括我自己看到过很多死亡。这种生命经验它逼着你要去讲你自己的故事,我有这个需要,有这个叙事的欲望。电影就是让我觉得找到了一个比小说还要好的叙事方法。你看我的两部电影拍来拍去在叙事上都是比较传统的,不是完全没有叙事,跑到非常实验的那个方向上去,就是因为叙事的确是我自己的一个需要,那些经历过的事情真的想讲出来。你知道汾阳是个多大的县城吗?从东到西,从北到南,有一个十字交叉的大道,从东跑到西,从北跑到南,每条路,骑车超不过10分钟,穿出去就是田野。这些经历使我觉得要改变,很多东西需要慢慢改变,一个人当你面对很多文化上的选择时,很需要你有一个理性的方法。
程:你怎样选择和处理呢?
贾:比如说怎么样面对汾阳这样一个县城背景。我接触过很多跟我差不多也是从县城来的,就有两种表现,有一种人就说我的家乡什么都好,不容忍有任何诋毁,家乡就是天堂;另一种人不愿意承认他的县城经历,你是哪儿的,我是太原的,其实他是汾阳的。我觉得两种表现都是懦弱的,也不是懦弱,特别奇怪,就是说,是不自然、不正常的一种表现。你看像汾阳那个地方,它就是封闭,就是落后,比哪儿都慢一拍两拍,然后人际关系里头有很多麻烦的事情,每天就那样。那种生活你让我回去过,我能过吗?我肯定不能。但是另一方面,那里面又有非常多的我自己的经历,温暖我的东西。友情啊,亲情啊,包括你能跟自然那样亲近,我现在在北京可能一个月都看不见一次田野和山,但我那时候真的下午黄昏的时候经常去田里头玩,骑自行车,特别高兴,觉得内心世界特别广阔,看云,晚上夜特别黑,你能看到星星。你在这儿能看到什么吗?什么都看不到。
程:除了自然,汾阳肯定还有很多影响了你的人和事。
贾:就是这个背景。在那么一个小的环境里面,满街的熟人,每天闲到什么程度?就是站在街上,突然车站里面打起来,跑过去看,已经走了。或者在街边走,哗,一个自行车冲过来了,后面一个人满头是血,坐在后面,就往医院那个方向跑,大伙骑自行车跟着,跟着跑到那儿去看包扎,一边看人家包扎,一边听人家讲刚才是怎么回事。就到了这个程度,你生命力这么旺盛,就这样度过。每个小孩都是坏小子,我自己也是,上小学的时候,特别流行拜把子兄弟,我们二十几个兄弟,其实大家的年龄就差一天、差一个月。我排行老二,属于承上启下的,就不好好上学。小学到初中是一个坎儿,一到初中很多人都不念书了。我第一次有朋友去世,记忆很深。他是我的拜把子兄弟之一,不上学了,就跟他爸修自行车。那个时候开始有嘉陵摩托,但是很稀罕,有个顾客的摩托坏了,放在他爸那儿修,车刚修完,他就骑了出去,没想到没开出多远就坏了,他就这么没了。突然之间成天在一起玩的朋友就这样简单地死了,你觉得特别震惊。又过了一段时间,有的朋友当兵走了。又过了一阵,我骑着自行车在大马路上碰到一个朋友,他借我的自行车,说要去杏花村酒厂,找朋友玩,那要骑一个多小时,酒厂在城外30里地。到晚上他没还我车,我挺纳闷。第二天下午,人家跟我说,他喝多了,喝死了。我自己跑到酒厂把那辆车骑回来,一路走,一路难受,特别难受。这些事情呀,让自己觉得……突然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生活总是变幻莫测。
程:一些年轻的生命没有了,一起成长的伙伴消失了。
贾:性格慢慢有了一些变化。我小时候特别外向,现在也外向。
程:现在的外向跟小时候还是有区别的。
贾:可在那之前,心是空的,什么都留不住,你天天很快乐。这些事情过去后,你觉得生命不是空的了,变成沉甸甸的感觉。那时候,我有很多朋友,不上学了也没法就业,很多就当小偷啊,当流氓啊,"严打"的时候,一批批地进去。有一次我回老家,那时我已经在太原学画画了,走在街上,遇到刚判死刑的人游街,一看,车上就是我的同学。我一直觉得,他看见我了,我不能肯定,但是心里面感觉他在冲我笑。他后来被枪毙了。还有,拍《小武》的时候,演靳小勇旁边的那个人,小武在玩苹果,他把苹果抢过去跑掉的那个男孩,也是过去的朋友,我拍完《小武》没几天他就被抓了。为什么被抓呢?他放高利贷。借他高利贷的人还不上他的钱,抢劫被抓了,交待出为什么要抢劫,把我的那个朋友给供了出来。那时我还在做后期呢,别人打电话告诉我说他进去了。这些事情,我不愿意做一个道德上的评判,只是觉得让我能感觉到命运,命运是个什么东西,不同的人不同的命运在这个秩序里面发生,这些经验对我都是很珍贵的。
程:在小县城有很多被人们看作流氓的人其实很受年轻人的崇拜,我以前在电影院工作的时候,天天都能看见打架的,经常在电影院门口看见一滩血,然后听说有人打架了,动刀子了,高中女学生很喜欢那样的人,跟着他们上舞厅是很荣耀的事情。
贾: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最敢开风气之先的。拎个录音机满街走啊什么的,而且他们也经常到处跑,就像那个流窜犯,流窜时间能够看各个地方的事情,回来之后他就是很有生命体验的那种人,他就跟你讲太原是什么样子,电车是什么样子。那时候,汾阳最著名的一个流氓,他也是小偷,他外号叫四毛六,就是他带着四毛六分钱从北京回来,走了一圈。我们当时都特崇拜他,你想四毛六分钱,这么长的一个旅行,你都无法想象他是怎么完成了,你觉得没法像他那样生存下来,崇拜极了。
程:还是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一个问题,他就愿意这样子,不纯粹、不完全是社会的原因。
黄:你就没想过拍跟山西没关系的东西吗?
贾:现在还没想,以后肯定会拍吧。现在我才拍了两部电影,山西的那种生活经验给我的影响我一下还没讲完,好多东西就特别急着要说。
程:可以这样说,这些经验之外的东西,至少目前还不是你需要表达的。
贾:很多人采访时问我什么时候拍一个山西之外的,什么时候你离开汾阳,拍一个北京啊,广东啊。我觉得,心里头郁积下来的东西,让我暂时还没有办法离开自己生命的经验去拍别的东西。甚至包括镜头的运用,以及纪实的风格,因为我觉得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不愿意用那种商业的方法,或者说风格化的方法来讲这个故事,我会老老实实地讲,然后在这个纪实的方法上来把它做到最好,这些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比如说《站台》和《小武》,你完全可以把它做成另外一个模式,但我不愿意那样讲,讲这些事情,我不愿意油腔滑调的,我就愿意好好说,正儿八经把这些事儿讲清楚。包括为什么不动,老是站在那儿看,包括为什么镜头跟着人在那慢慢摇,这种电影的方法都是一个我自己对待往事对待事实的态度,包括我很排斥前后运动,我希望在一个距离里面来了解对方,这些形式上的运用都是跟自己的经验有关。
程:就是说你的形式,你和人物的距离,实际上包含着你的世界观,也就是你跟世界的关系。
贾:我觉得它还是跟我的县城经历有关系。小时候的生活完全是体制之外、系统之外的,有时候去打架啊、去闹事啊,一直就是一个制度之外的生活方法。我记得在太原的时候,人年轻嘛,有一年元旦我特别难受,说起来很可笑,就是想自己将来考上又怎么样,毕业后分到一个单位,每天有人管着我,每天都是8点钟去上班,5点钟回家,想着想着就难受了,觉得我怎么能这样,我为什么要在这样的生活里面生活,就包括这些东西都是县城经验给我的,甚至包括对体制、对工业的抵触和恐惧,总觉得他们是一个系统,我是系统之外,我们不能融合,总有这种心态。
程:有人对你提出的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到来欢呼,也有人认为你在否定电影学院的教学,你能讲讲你提出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到来的这个命题的前后思考吗?
贾:我觉得做这一行,总要保持一个理性,文化选择上的理性。包括看人看事,尽量少的因为你生命经验中的一些挫折,而对待事物失去一个比较客观比较公正的看法。我觉得这是自己想坚持的一个方向,包括观察电影本身,这种价值观也很重要。比如说DV这个东西,差不多在1998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再次到来》。后来很多人谈起这篇文章,甚至真的有人看了那篇文章很激动,然后也想用影像来表达自己。但是后来慢慢我发现这个概念啊,其实被很多人误解,并不是说业余电影就是瞎拍,我有机器就行,我什么都不管。很简单的东西,焦点,你好好练三天,就弄好了,然后你照度不够,你换个灯泡,就弄好了。不能无心来面对这些技术上的东西,就像我无心来面对工业一样,反正我们是业余的,就随便拍吧。甚至我觉得还有一个很不好的说法,就是一个人的电影。我觉得这是跟电影这个制作方法、规律不符的东西。电影就是一个群体性的工作,没有人是通才,你摄影很好,录音也很好,制片也很厉害,而且你还有精力同时照顾这三件事情,甚至你剪接也很厉害,一个人就包办一部电影?电影它永远是一个群体性的合作,即使你有这个能力,你也没有这个精力啊。即使你这个能力和精力都有,那我也不相信。这些概念就是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其实我所说的这个业余性就是一种精神,针对那种僵化的、所谓专业的、制片厂制度里的导演,不学习,不思上进,视野很窄,然后在僵化的运作机制里不停的复制垃圾的那些导演。我觉得面对他们,我们就是业余的,我们的业余有一种新鲜的血液,有一种新鲜的创造力,有新的对世界的看法,有新的电影方法,那就是我们的业余。我想,这种业余性,包括制片方法,实际上就是先锋性,就是前卫性,而不是降低我们对电影的标准。所以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你要处处小心,一不留神,你就站到了你自己的对面。从人生经验到电影经验,任何事情都要琢磨,可能不是那么回事。比如说一个人的电影很诱惑人,因为它有一种反叛性,有一种宣言性,有一种挑战性,很痛快。但它究竟对不对,是不是这么回事,应该好好想一想。创作永远不能停留在一个人的电影上,也不能永远停留在所谓的口号性的阶段。比如说新浪潮,每一年有七八十部处女作拍出来,非常轰轰烈烈的,那个运动过去后,要留下真正的作者,像戈达尔,像特吕弗。真正的作者要出现,你不能说热热闹闹,大家打家劫舍一样,干完之后,电影是一片空白,没有一部站得住脚的影片,没有一个能有连续性工作的导演。如果那样的话这个运动是失败的。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
黄:一个人的电影,具有这种观念的人不少。
贾:一个人是很可怕的,不跟大家一起做。(笑声)其实这种心态在工业里面也有,比如说有的导演认为其他的摄影师录音师只是他的一个工具,他不愿意承认那个人是一个鲜活的有创造力的人,他这样说,是因为他觉得那个杰作是他自己的东西。很幼稚的一个想法,非常幼稚的想法。开放的心态是挺重要的。在电影这个行业里不要冒充孤胆英雄,没有孤胆英雄,你的背后肯定是一个集体在帮助你,特别是一部艺术电影,导演是获利最多的。我的两部片子没有人看,王宏伟演得再好,谁知道他?人家没法衡量他的票房价值;摄影师再好,人家看的是录像,回头跟我说,嘿,你那个是用家用录像机拍的吧。这个挺内疚的,面对这些事情,这个时候你再去抹杀他们的创造力,这真的有点残忍。
程:拍《站台》的时候,《小武》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已经获得了世界的承认,它会给你带来怎样的影响?
贾:没有干扰。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制作电影。我觉得一个导演他拍第二部电影的时候,怎么样来面对你的上一部电影,这个问题是没有人能回避的。那么你怎么样来处理两个电影之间的关系,你是有一个延续性,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原来成功的方法是不是要接着拷贝到新的这个电影里面?创作者永远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你要面对你过去的作品,另外就是你怎样面对舆论。以前你不知道你的工作成果是这样的,《小武》之后,评论铺天盖地的,也乐在其中,这个时候你怎样来面对评论对你的期待,很多这样的问题。如果在你实际拍摄之前,这可能是纠缠你的一个问题,到最后,实际上导演你根本没有精力去想这些事情,因为你自己内心的冲动、讲述的欲望,那是能够战胜一切的东西。你根本不可能想到,我拍这个女孩现在跳舞人家会怎么看,而是我真正需要,我想要她来跳舞,至于人家怎么看,我不知道。它又变回到一个原始意义的创作状态里边。
还有电影的形式,这种寻找,也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内心活动,跟战争一样。你谈论的事情有你的经验,有你的想法,这些东西很具体,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对每个导演也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来讲这些事情,用什么样的方法,我觉得那永远是导演的一场战争。我不相信那种顺利的创作,看起来非常从容,非常顺利,没有反反复复,没有斗争的创作,我觉得都是有问题的创作。你肯定是在一个惯性里面工作,自己给自己提出挑战,自己跟自己来探讨一些问题,这个创作你有时会觉得自己是那么的优柔寡断,有时你觉得自己是那样的患得患失,那这个状态我觉得是对的,因为你在寻找自己的一个新出路,而不是沿着老路跑来跑去。在创作里面的熟手是很可怕的,所谓工匠就是熟手。你要面对的事情太多了,你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太多了,你怎么有精力去想别人呢,而且那个别人是一个假设的东西,是只言片语,我看还是回到自己的叙事里面寻找新的出路。
程:中国的独立电影获得世界的肯定之后,国内的一些并不了解这些影片的人出现了很多无端的指责,还有很多人认为你和其他的一些青年导演是在"预估成功",为西方拍电影。你怎么看待这种处于猜测中的评论?
贾:评论永远不可能引导我的创作。你不可能改变评论,而是你要怎样面对评论。我的电影大家都看不到,他怎么说你都可以。比如看《小武》这个故事,他可能会觉得,哦,小偷,三陪小姐,这都是元素啊,他看不到你透露在叙事里的情感,透露在你的方法当中的情感。这些评论都是很正常的,关键是你自己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处理你的故事。
黄:你好像说过自己是电影民工,但我感觉你是越来越像知识分子了。
贾:是他说的,1996年,程青松说的。我觉得跟民工有同质性,同样的质感。还有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银幕真的不关心这样的人,完全没有。我去拍《小武》也是因为觉得自己有种不满,有一种生命经验,非常多的人的生活状况被遮蔽掉了,若干年后想想大多数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如果你从当时的银幕上寻找,全是假的,全是谎话。这样看来,我觉得电影真的是一个记忆的方法。
黄:据我所知,很多人是出于一种好奇,而并不是真的觉得你贾樟柯的电影说了一些什么,对他有什么触动,只不过是听说以后,去关注你。
贾:现在这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个东西,电影本身下滑到一个人们永远不关心你在谈什么,也不关心你用什么方法在谈这些事情,而关心的是围绕着这个电影的传闻,没有人关心你的文本,以及实质的东西。现在的人没有六七十年代那样的思考习惯,大部分人都停止了思考,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习惯,消费时代嘛,大家都喜欢畸形的消费,精神活动变得非常的少,变成了一种不习惯。
黄:最近要去法国参加电影节?
贾:要去。
黄:刚看见你的一张明信片上写着,花花世界真好。巴黎真好,我也喜欢巴黎。
贾:我就喜欢它传统保持得很好。我想象有一个孩子从小在那个城市长大,他所有记忆的东西都丢不了,他真的很幸福。你要让我回了汾阳,现在什么都找不见了,都拆了。
程:这是我们最难受的一点,你要回到你少年、童年成长的地方,什么都变了,什么都没了。
贾:人们往往觉得一个庙才是文物,才是珍贵的,别的都不是。其实保持传统不等于是保持庙。汾阳的那种街道当然住的也很痛苦,上下水都没有,可是它是记忆。那种毁灭性的拆除很让人痛心。你看有一个邮局和一个百货公司都拆了,我小时侯,那是一个中心,邮局对面就是百货公司,每天都蹲那儿聊天,和朋友打扑克,这个中心没有了之后,你茫然。它不单是一个百货公司,一个邮局的事情,它是一个记忆。你看巴黎的一家老店,从一八多少年、一七多少年就在,那个东西挺好的。
黄:维护,保养。
贾:对,维护。不要破坏。
程:你看北京也是啊,变化多大,我住的地方已经变了无数个样子了。
贾:等于是每个人到这儿都变成无家的人了。自己的家,样子都变了。黄:我每次出差或者出国回来,只有一个感觉,是熟悉,而没有喜欢,有一个家在这里而已,回来方便点。
贾:我有一个变化,前几次去巴黎,都是朋友带着,稀里糊涂的,你觉得对这个城市挺陌生的。但是后来,去年的时候,威尼斯电影节之前,有一个很长时间的间隙,但又不值得回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在威尼斯住着,自己学会坐地铁,会找站,会看地图,什么都能找见了。你就觉得开始对这个地方有感情了,去哪儿都很方便,公共汽车都会坐了。你就觉得你能掌握这个城市,慢慢了解就更深入了,慢慢你真的能感觉这个城市的魅力,比如说有个什么展览,一查,稀里糊涂就去了,嗨,真找着了,然后就看,你就觉得这个城市真的博大精深,开始能接触它。以前不是,人家说下地铁吧,就跟着下,出站,就跟着出。
(电话铃声响起,贾樟柯去接电话。电视机里同时还播放着《站台》,电影中的文工团员们唱着"成,成吉思汗,有多少美丽的少女都想嫁给他呀",大家忍不住笑了起来。贾樟柯接完电话,谈话继续。)
贾:自己也能找着去看电影,感觉自己能够享受这个城市。
黄:你现在多长时间回山西一趟?
贾:一年两次。差不多,平均,夏天回去一次。春节我是一定要回家过,外面有什么事情我都不管。我可以初二就走,但是必须回家过除夕,有几次柏林电影节都是大年初一大年初二,我都没去。年是一定要过。
程:《站台》里的古城墙汾阳有吗?
贾:有,都拆了。是土城。片子里的是砖城,平遥古城。都是砖的,有一些破败的地方是黄土的。
黄:可以上去散步。
贾:对,很多人爱上那儿转。
程:《小城之春》走在城墙上。《站台》讲的也是小城里边春心荡漾的一群年轻人的故事。他们或许会走出去,或许走不出去。
 动感短信、闪烁图片,让您的手机个性飞扬! 动感短信、闪烁图片,让您的手机个性飞扬!
短信世界杯站:新闻、游戏、动感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