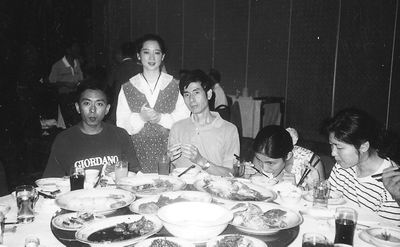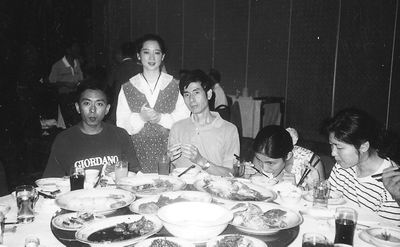 王小宁与我没有俩人的合影,尽管我们俩人经常合作。(左一为王小宁) 王小宁与我没有俩人的合影,尽管我们俩人经常合作。(左一为王小宁) 时代只相信“成功”二字
王小宁
当年我在一家出版社做图书销售的时候,结识了一位年龄相仿的青年——魏珉。他常
来买我们的书法碑帖,久而久之成了朋友,后来我搞了摄影,他则成了一家刊物的主编——难以置信的年轻主编。大约是1991年上半年,一次闲谈之后,魏珉为我引荐了一位刚刚辞去公职而投身于自由写作的朋友——陈子堃,并有一个朗朗上口的笔名“伊夫”。
我当时颇为吃惊,他人近中年居然敢甩掉铁饭碗。魏珉解释:原因只有一个,他所处的环境限制了他所钟爱的写作,制约了他的发展和他天性中追求自由的强烈愿望。但我更感慨于他竟然“异想天开”地打算“以文谋生”。以文谋生,今天看来已不足为奇,但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只知道国外有自由撰稿人、自由摄影师等等,活得潇洒自在且收入颇丰,社会地位也并不低。而在国内,别的不论,单说那微薄的稿费和尚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便足以令人望而却步,更不敢奢望能解决生计问题。改革开放后,谁是最早做自由撰稿人的,我没去考证,我所知道这一行的第一人就是陈子堃。
对于今天的子堃,仁者智者各有说法,但无可争议的是他已经是当今跨文艺、新闻两界的一个人物,至少我这么认为,因为我目击了他起步和发展的历程。
圈内的朋友都知道,现在的子堃有一张无形的大网,全国各地数百家报刊乃至国外一些媒体都尽收网底。不难想象,建立起这一张网络,最初要有多么的困难,需要勤奋、能力、诚恳和信誉去一点点编织。起步初期,他的生存状态是怎样呢?什么顶风冒雨、披星戴月、笔耕不辍、自强不息,自是不在话下。
我记忆中的一件小事便可见一斑。一日,他在一家纺织厂的浴池洗澡,发现更衣柜里遗弃一张旧报纸——《中国纺织报》(该报朋友别怒,大多数报纸是如此下场)。子堃没放过这个可能发稿的机会,便按图索骥找到了这个周末版的编辑王茁,他们第一次见面就谈得很热烈,后来,子堃竟成为该报长期的一个作者。
那些年双方真诚的合作使他俩成为了好朋友,当时的版面编辑、南开大学毕业不久的潇洒小生王茁,现已做了知名的《中国服装》的总编,今天,只要王茁要稿,子堃就有求必应,先放下其他报刊的约稿。只因为“王茁他们报纸没有歧视和偏见,是最早一批用我稿件的报社”这一条。
做一件事与做好一件事,是两个概念。而于相对短的时间里做得有声有色,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客观地说,子堃之所以成为自由撰稿人中的佼佼者,在当今演艺圈和文艺类媒体中有相当的知名度和一定的影响力,其实是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由于周末版大规模的兴起和影视艺术走入市场带来的新变化,自由撰稿人就必然会历史地出现。子堃可谓应运而生,前面是一片一马平川的旷野。机会来了,他牢牢地把握住了时机,这是偶然性。
当各报刊从被动等稿变成主动出击抢稿时,子堃以其旺盛的精力、敏锐的反应、独特的视角开始逐步扩大他占据市场的份额。由于他几乎疯狂的敬业精神和高效率的一路疾驶,更由于他没有招牌可打而必须尽快打出自己的旗号,他顽强的意志、不馁的韧性则是他走向成功的桥和路。
小时候听说鲁迅在别人喝咖啡的时候去干这干那,觉得鲁迅太伟大,常人难以为之。长大后发现生活中这样的常人其实很多很多,子堃当属其中。不止一次,他都是边吃边采访,饭未吃完,采访却已毕。带着满满的几页记录,他就匆匆告辞,采访下一个对象或回家打稿,我们则继续吃喝歌舞至深夜。次日中午,酒尚未醒,子堃昨晚两个采访的稿件竟都已通过传真发往了各地。勤奋使他成绩斐然,这就是必然性。
当他还默默无闻,某导演得知他不是《××日报》的记者便收起笑容送客时,一个人的自尊心该有多大才能抗得住?当他声誉鹊起后,又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流言诽谤和恶语中伤时,一个人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宽容才能保持心理平衡?我想,当不断有剧组和“明星”要起诉他、匿名电话威胁他时,他定会有过彷徨和孤独,哪怕是片刻的。然而,他最终一个人自信、坚韧地穿过内心和外部的狂涛骇浪,让所有爱他和恨他的人都不得不面对他。成功难道不该属于这样的人吗?!
有人叫他“B-52”,以此来形容他在传媒上地毯式“轰炸”效果;还有人说他是“伊夫通讯社”,比喻其发稿的辐射范围;当然也有些人以“皇家”、“嫡传”的自我感觉来点评子堃的“不正宗、非专业”。但有什么法子呢?机遇对大家是平等的,如果你想当“B-52”,没人拦你,实际上也拦不住你;成不了“张通社”或“王通社”,也没人讥笑你不成器。看着别人风光心里不是滋味,说来也是人之常情。没办法,这个时代只相信两个字——成功!
 世界杯新闻订阅:精彩进球,一个不容错过! 世界杯新闻订阅:精彩进球,一个不容错过!
短信世界杯站:新闻、游戏、动感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