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良家妇女

几乎所有传奇与传记,都津津乐道林徽因与徐志摩的故事。而在徐失事后,林徽因写过一篇《悼志摩》,自称是比徐“年轻许多的一个小朋友”。这“年轻许多”不只是说在年龄上她比徐小八岁,更强调徐志摩与她父亲是好朋友。这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声明,直接把徐奉到父执辈份上,同时暗示了自己当年的不谙于世事。徐志摩可以迷沉爱河,她却并不必随之深陷。梁从诫说过:“母亲(林徽因)当然知道徐在追求自己,尊重他所表露的爱情”,但是“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也就是说,对徐志摩,林徽因说喜爱也好,敬佩也好,却不能说恋情。人家没爱上你,你就是天大的才子又当如何?后世戏文硬编出的缠绵悱恻情爱,是从来不曾有过的。
而我一直更感兴趣的是另一个影子一样的主角,梁思成,他守着这样一个惹人的妻子,是如何克服嫉妒与危机感,从而达成内心平衡的?史家一般而言,徐志摩与张幼仪因性格及思想差异离异是必然的,但林徽因的出现大大加速了这种必然。梁思成与徐志摩,居然还是朋友,从未听过两人为林闹过恶言恶语,甚至徐死后,梁还飞赴济南为其操办后事。梁思成的肚子里,到底有几条船?这还不算,据说,林徽因还拥有着一个为了她终生不娶的爱慕者,哲学家金岳霖,就住在梁家小院的旁边。梁氏夫妇的起居室有一扇小门,通向金岳霖的房子。通过这扇门,金常常被喊来参加梁家的聚会。梁思成如此自信,凭的又是什么?
梁思成是一名建筑学家,他身上有许多引人注目的东西,例如他在建筑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建筑保护方面付出的努力以及在历史传承主张上招致的批判……此外,拥有声名显赫的父亲也加深了人们对他的注目程度。像老舍与鲁迅的儿子后来没有成为大作家一样,梁启超竭力用父亲和学者的双重权威影响着梁思成,使得在清华就读时即显露出政治头脑的梁思成最终选择了潜心于建筑的道路。这些都是“公众注意度”,那么,曾牢牢吸引了林徽因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林徽因的美丽与梁思成的才华珠联璧合,他们一个活泼,一个沉稳,在性格属于超稳定的互补结构。他们不仅有相似的成长背景,同样深厚的东西方文化修养,还有共同的研究领域和钻研方向。在战火纷飞的年月,他们克服安全的威胁、交通的不便、物质的匮乏、健康的障碍,像两只猴子,携手攀爬了无数的亭台楼阁,勘测了一座又一座的古代建筑。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建筑毁于后来的天灾人祸,是他们绘制的图谱为那些消逝了的建筑留下了永恒的身影——试想此种生活,与徐志摩可能提供的吟花弄月诗词典赋不夜天相比,是不是要扎实许多?
未能娶到林徽因,实在是徐志摩的遗憾。就在徐志摩为维持陆小曼原有的生活水准而四处奔波的时候,林徽因正在以一个良家妇女的角色全心为梁操持家务。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儿、新生的儿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烦的,一个感情上完全依附于她的、头脑如同双脚一样被裹得紧紧的妈妈。中国的传统要求她照顾妈妈、丈夫和孩子们,监管六七个仆人,还得看清楚外边来承办伙食的人和器物,总之,她是被要求担任法律上家庭经理的角色。这些责任要消耗掉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有一件趣事可以反映她那一段时间的典型生活。有一天一群名流正在梁家饮酒作乐,仆人陈妈惊慌地跑进来报告说,在梁家高围墙的西边紧邻,房顶上裂开了一个大洞。她说那里的房客穷得修不起房顶,求林徽因向房东说说。就像平时一样,林徽因马上放下一切去调查这件事。她同房东一说,发现房客住三间房,每月只付五十个铜板的房租。房东说,现在房客的祖先二百年前就租用这房子了,每月付固定的租金。由于是同一个家庭一直住在那里,房东不能提高房租,也就不愿意掏钱修理。林徽因没有办法,只好自掏腰包,给房东一笔修理房顶的捐款。
一种选择就代表了一个方向和一条道路。林徽因可以写出这样曼妙的诗句:“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音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又能安闲地过着风清云淡的良家妇女生活,如果想赞美她,可以用这样一些词:刚强、克制、明朗、大气。总之,是健康。
凌叔华:徐志摩欣赏的第四个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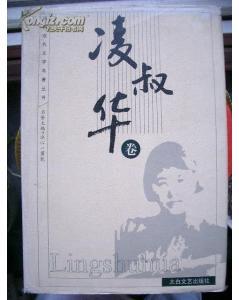
正如陈西滢难以料想他的名字会因他与鲁迅的纠葛才为后人所知一样,凌叔华也绝难想到,在她离世十多年以后,她的存在,会因一场官司而被坊间大众重新发现。关于虹影的小说《K》与凌叔华女儿陈小源的司法纷争,一般报纸都采用的新闻通稿中有这样的内容:“陈小滢认为,《K》以她的父母陈西滢、凌叔华过去的生活为背景,以淫秽的手法杜撰了许多不堪入目的情节,侵犯先人名誉。”
官司的判决由法院说了算,我关心的是,依虹影的文史修养,似乎难以想到拿这样一个故事来创作小说。后来想通了,因为有站在她身后的丈夫赵毅衡,在做场外武术指导。赵先生是个学问人,肚子里一堆有趣的陈年旧事。所以,官司输了,虹影不吃亏,可以回家痛扁老公一通,以泄心头无名之火。
与虹影的轰动与叫座相异,凌叔华只是个被圈里人叫好的小说家。与对她夫君的苛责又不同,鲁迅给过凌叔华不低的评价:“她恰和冯沅君(当年与丁玲、冰心、凌叔华并称四大才女)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而徐志摩一提起凌叔华,则会兴奋得马上要写诗。泰戈尔来华时,有一次在凌叔华家开招待会,徐志摩摩拳擦掌地对曾在英国一起留学的陈西滢说:“哥们儿,咱们今天可以看到一个美人儿了!”陈西滢却笑而不答。等到徐志摩跨进凌家大门,却见陈西滢正在以主人姿态接待來客。这就是陈西滢,有了艳福,在老朋友面前也绝不透一点风声。
按徐志摩的说法,是陈西滢在编《晨报副刊》时,写了些奇文发表,打动了才女凌叔华,她主动写信约他来家小叙,姻缘由此促成。但凌叔华却另有解释,说泰戈尔来华是1924年,到凌家作客,陪同者有二三十人。凌那时年轻气盛,当众问泰戈尔:“今天是画会,敢问你会画吗?”有人警示她勿无礼,她也不在乎。泰戈尔真的坐下来,在她备好的檀香木片上画了一些与佛有关的佛像、莲花,还连连称谢。当时徐志摩、胡适、林徽因都在座。也就是在这次茶话会上,她结识了陈西滢,在陈主编的《现代评论》上发表了她的成名作《酒后》,遂相恋并结秦晋。
与陈西滢如何相识相恋,两人的说法如此不同,可以想见,虹影远隔经年,想写那段日子,生出些是非来,原就是极容易的。所以,虹影至少给大家一个警示:谨慎无大错。陈西滢与凌叔华两个爱写作的人,就一直在互相提防。当年一位记者曾记叙过,凌与陈婚后不在同一书房写作。凌创作总是对陈“保密”,生怕这位批评家在她的作品尚未发表时,用冰冷的水将她的文思和创作激情浇灭;陈写好文章后,也不给她看,只有等到发表后,才彼此相示。
1929年,陈西滢赴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及外文系主任,凌叔华也随之到武大任教,与另两名在武大执教的女作家袁昌英和苏雪林过从甚密,结为好友,当时被称为“珞珈山三杰”。苏雪林在《其文其人凌叔华》一文里说:“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问题,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可能也正因为此,她才能得徐志摩的信任,替他保管“八宝箱”,里面是徐志摩的日记及书信。徐志摩一生的情感生活太丰富了,与张幼仪离异,与陆小曼结合,以及迷恋林徽因,林林总总的细节,都会藏在“八宝箱”内,这不是个箱子,是个富矿!因此,徐发生意外后,才会有多个当事人争夺箱子的事情发生。
1946年,陈西滢受国民政府委派,赴巴黎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代表。因为穷,住不起巴黎,移居伦敦。翌年,凌叔华携女儿陈小滢赴伦敦,从此定居欧洲,一去不返。多年后,凌叔华发现,香港和南洋书市流传着署名“凌叔华”的长篇小说《梦里心声》和短篇小说集《柳惠英》,更糟糕的是,在一些评论家的文章里,也把这两本书列在她的名下。1981年,凌叔华曾发表声明:“《梦里心声》及《柳惠英》二书,均非我的作品。我也管不得许多……也只好忍气吞声吧!”而她的女儿对虹影的小说,却绝不想忍气吞声,也许,这算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毛彦文: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毛彦文的情爱故事,最适合琼瑶阿姨来讲。不止三角,超过四角,男主演们与毛彦文的距离远近不等,由此产生的不规则矢量犹如乱箭飞蟥,纵横交错;又若流星化雨,说不定,就伤了谁的心。
毛彦文生于大户人家,父母相对开明,因此有机会成为民国第一批知识女性,读中学,读大学,还远赴重洋读硕士。毛彦文九岁定亲,十九岁时夫家抬着花轿来迎娶,她却从后门逃了。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故事,后门的锈锁,总是在呜咽的锁呐声已逼近花厅时才訇然弹开。守在门外的,是她的表哥。这一点,也未能逃出窠臼。
表哥朱君毅,清华高材生,留美博士。二人两小无猜,亲密无间——那年月,尽管风气渐开,但毕竟有男女不亲之防,而最具方便条件可以名正言顺在一起厮混的,就是表兄妹了——这也就是《红楼梦》里贾宝玉青梅表姐竹马表妹的根本情由。
朱表哥去美国留学前,与毛海誓山盟,锦书缠绕,家长们也乐得成全,一桩好事眼见得要花开蒂落,水到渠成。
朱君毅的清华同学吴宓,后世的国学大师,却被毛彦文写给朱的情书深深打动,一颗爱的种籽,就此埋下。朱与吴又有同学陈烈勋,把妹妹陈心一介绍给了吴宓。陈心一与毛彦文同学,吴曾托毛彦文了解陈心一的情况,算起来,毛彦文该是吴宓的媒人。其后,朱君毅学成归国,突然变了心,要与毛彦文解除婚约。能说出口的原因是他接受了现代观念,认识到了近亲结婚的害处。但在毛彦文看来,此是借口,六年苦候,青丝白发,一朝成空,她无法接受。毛泪眼婆娑求吴宓劝朱回心转意,未果。这样,吴又成了毛的媒人。原来,朋友妻,有顾忌;现在,媒人要往花轿里跳了。吴宓与陈心一离婚,决绝地抛妻别子,苦追毛彦文不休。这一段情丝缠绕,怎么一乱字了得。
吴追毛时,每次写信,总念念不忘说某年从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而渐生爱慕和幻想。毛彦文心口哪块疼,难道吴宓不知道?他这么往伤疤上捅,好像是在故意胡来,毛彦文的反感一日深似一日。难怪已活到一百余岁的毛彦文,耋耄之年对吴宓的评价依然是:“书呆子!”
毛缠朱,吴追毛,一场三人马拉松,漫漫无穷期。等到毛彦文心灰意冷时,抽身而退,一场游戏戛然而止。毛彦文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疗伤法子,只不过是暗下决心,要干一番大事业。可是干什么好呢?此时,恰好,金陵大学的同学熊芷请毛去北平散心,毛就离开了南京这个伤情之地,只身北上。
这个熊芷,有位大大有名的父亲,熊希龄,前清翰林,曾任奉天盐运使;民国后,又作过财政总长,国务总理,领导着梁启超、孙宝琦等,是所谓的“名流内阁”。其后他脱身宦海,全力创办香山慈幼院,聘李大钊、蒋梦麟、胡适等组成评议会,摸索出一套科学而实用的现代教育方法,把个孤儿院办得无比红火,人数最多时,达一千六百余人。毛彦文到北平后,在熊芷的陪同下,参观了熊希龄主办的香山慈幼院。恍然间,毛觉得,这就是自己该干的事业啊。
而当时,熊希龄已丧妻四年,依然悼痛不已,因之意气消沉,甚至已无心打理慈幼院业务。也许是大家从毛彦文的眼里发现了火花,也许是熊芷爱父心切,于是推举熊希龄的内侄女朱曦出面,极力鼓动熊希龄向毛彦文求婚。熊听说过毛,对毛的评价是“民国奇女子”。毛也犹豫,毕竟年龄差得太大了。只是,转念一想到“事业”两个字,心一动而不可收拾了。
1935年2月,熊与毛,在上海办婚礼,《申报》有这样的报道:“前国务总理熊希龄氏,现年66岁,悼亡四载,昨日下午三时,借慕尔堂与毛彦文女士行婚礼。毛女士为留美女学生,任大学教授,芳龄三十有八,红颜白发,韵事流传,沪上闻人咸往道贺,汽车塞途,极一时之盛。”
毛彦文对熊希龄只提了一个要求,必须剃去他蓄留了20年的胡须,熊希龄欣然听命。一场风花雪月事,就此有了一个喜剧的收场。
(主要内容刊于《南方人物周刊》)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