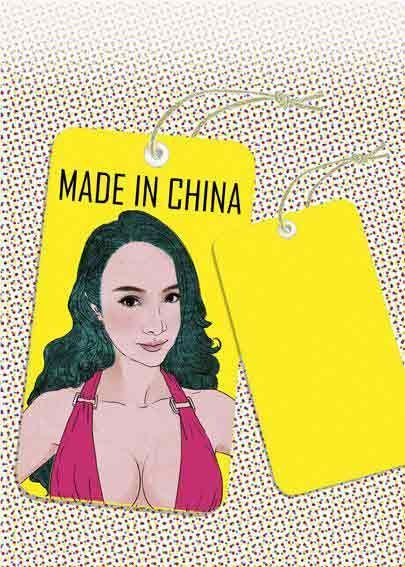
编者按
这两天关于庞麦郎的争议突然起来了,各种说法都有,我们不想凑热闹,只是想说说之前自家的报道。
《少年杀母事件》曾被誉为特稿界的杰出作品,也是前同事林珊珊的特稿处女作。确定做这个选题时,编辑蒋志高很兴奋,凭他多年的经验,这一定是个绝妙的题材。
林珊珊并没有这种感觉。起初,她怀疑张明明是不是有精神问题,如果他有精神问题,那么一切的报道都显得没有意义了。鉴定报告显示,张明明精神正常,林珊珊才开始了操作。
关于写作,林珊珊回忆当时蒋志高给出的意见是:希望的语言是像余华的冷峻风格,不煽情,不无情。因此,才有了见刊的那篇特稿。
不能判断庞麦郎精神是否存在障碍,这是我们未做这个选题的诸多理由之一。庞麦郎虽活得自我,但对于我们而言其本身便是一个悲剧;慢慢,他从自身的悲剧被迫走入了被推手消费的悲剧、被社会娱乐和被时代扭曲的悲剧。
诚然,我们也有过类似题材和相关作品。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错乱复杂的时代背景之下,能尽量以一个最为平等的角度将您带入,理解采访对象们的现实处境,重新打量这些人的生命,真实了解每个人的命运。附上本刊编辑部文章和主笔李宗陶撰写、于2013年4月15日刊发的第339期封面报道:《中国制造 欲望年代的干露露们》
南方人物周刊微信公号:peopleweekly 南方人物周刊致生活微信公号:people-alive
我们为什么要写干露露?
出发前,我们跟同行大体相似:关注每时每刻变动中的、吐故纳新的现实存在,也是在关注着时间。
众所周知,当下的北京时间浓度惊人。这个故事里一位当事人说:这两年,好像把20年浓缩着过完了。变,已经成为时代的整体特征,人们从没像现在这样处在如此急速的、大规模的、不得不的应变之中。
创造影响力、吸引注意力,以便……活下去。这是媒体今日的生存律令(干露露一家也提到生存),大家似乎别无选择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沉思并写点儿什么。区别只在于:你有多沉滞,你的内心就有多挣扎。时隔两年,我们翻回那一页的新鲜热辣,再一路跟随主人公顽强的进行中的新鲜热辣,终于在时间的小魔术里发现了一些值得哀悼的东西:假的征婚、假的表演、假唱、假摔、假的情感,掺了假的身体和容颜,还有,真假难辨的人心。这一切,都指向那个让全世界心领神会的词语Made in China。谁制造了它们?记者说,他无法断定碎片般的回溯将每一股欲望串起,人与人最终表现为:不谋而合。
七十多年前,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讲论尼采时说:这是人类的一个奇怪时代,几十年来我们就在其中漂浮;在这个时代里,人们不再有时间问人是谁。这一回合,我们问了:干露露是谁?她跟外部世界是怎样的关系?我们到达干露露家乡、也是为数不多将她作为一个人来打量而不是当作一件娱乐产品来消费的媒体。不仅如此,我们也问了自己,问了每一个通过鼠标、钱或别的形式卷入这个故事的人:你是谁。
在玛雅预言没有应验的世界末日到来之前,老师问一群孩子:有一艘诺亚方舟,可以拯救一部分人,你选择让谁登船?回答五花八门,除了体格、智慧、对人类的贡献,遗传基因的优劣都被孩子们提及。只有一个孩子说:政界、商界、文化界精英,带上一些;科学家、厨师、司机,带上一些;乞丐、流浪汉、作恶的、撒谎的,各种各样我都带上一些,因为人类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这才是自然。孩子说出了古希腊人的“混沌”,说出了哲学家那里的“存在者整体”。
我们以存在者的整体结成蛛网般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彼此之间有力的发生。这个力,在社会学意义上,是每个人的方向、欲望、梦想,它们相互作用着,产生合力,造就一个共享互通的世界。
金钱、名利、成功、喧哗,镶着时代金边的欲望大规模占领了今天的人心。它们连成一片海洋,成为最强盛的一股合力。在干露露的故事里,我们试图解析这些力,在展示闹剧的同时,领你进入悲剧的剧场。揭示干露露们的困境,便是提示我们每一个人的困境。
一种普遍沮丧的情绪:我们知道有些什么不对了,一些可疑的、令人不安的东西在周围游来荡去,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是继续抱紧还是放下些什么。我们没法停下来。缓慢和沉思,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
一百多年前,尼采预言了“超人”的存在;七十多年前,海德格尔预言了“一个超越以往的新人类”。今天,看看以鼠标为手、以屏幕为重要器官的世界,我们相信,新人类已经诞生。如何安放自己、与世界相处,并获得快乐、幸福和美,仍然是变中之常。
充当这个时代的记录者是颇有些苦涩的。记者在见证了那些失德失信失美之后,正学习安慰自己。如眼前这帧摄于故事发生地之一的街头寻常景致:李树开花了,大簇大簇的白花堆在枝头,哎,是春天来了。在这世上,终有些东西,如四季轮回冬雪春雨,常在,而且美。
中国制造:欲望年代的干露露们(正文)
男人们三三两两进了包厢。各自将宝马、奔驰或别的什么豪车泊好,在江南水乡这座农家乐的小路上彼此寒暄的当儿,他们已经从前后左右不同方位,从头至脚将眼前的干露露扫了一遍:不到1米6的个子,身材匀称,手与前臂尚有婴儿肥;劣质的黑色毛衣与皮裤之上,搭配一件纯白色皮草——在与母亲雷炳侠的对话中,她管它叫“貂”而管羽绒服叫“袄子”;长发从黑色棒球帽里披挂下来,及腰,但被旅途中的风尘粘成一缕一缕;巨大的墨镜挡住了眼睛和半张脸——娱乐版行话叫“黑超遮面”;鼻尖高耸,黯淡的肤色和成片的小痤疮无声指向主人的睡眠、饮食、保养和职业。她走路的样子有些特别:粘滞,重心偏向一边,像是在跋涉。
一瞟一瞟之间,男人们迅速完成了打分。在娱乐类节目上,这是亮牌子或旋转座椅大力按钮的时刻。
大圆桌旁不断被加进椅子,14位某总或某哥参加了接风晚宴。他们,有的是合伙开了演艺吧,通过中间人请来干露露,是夜在酒吧演唱3首歌;有的刚刚认识,彼此敬酒交换电话,相约再会。这一夜,干露露是小城贵宾,是某一阶层头面人物之间的关联。
烟递过来,打火机随之而来。干露露用手拢过一星火苗,小小的手轻轻裹在粗黑大手之上,一低头间,烟头亮了,大手满意退下。
杯来盏去,言来语去,不知所云。雷炳侠戴着一个没有镜片的黑色雷朋镜架(她解释:我脸大),笑,周旋,游刃有余。这位在网络上跟尹相杰照片放在一起、在视频上“雷人”、在Papa上被收听被爆笑的母亲快要过50岁生日了。每当感觉有人想灌醉女儿,她会拉下脸来:“晚上还要演出的。”
杯盘狼藉时,合影拉开序幕。男人们掏出手机,坐在黑超遮面的左边或右边,搭着肩膀或不搭肩膀,咔嚓,咔嚓。雷炳侠同时拍摄着,谁也不知道这些合影何时能派上用场。除了不能代女儿登台,她包揽了经纪人、保姆、保镖以及一切力所能及的角色。她的手机号码,在女儿所有的个人平台上敞着。一顿饭功夫,她接了五六个电话,其中有3个是同一号码,是征婚视频招来的。此人最后发来一条短信,表明心迹,坚持要跟露露本人,说说话。当然,她也时常接到夜半来电,劈头盖脸一通骂。
演出安排在凌晨零点过半。脸上有道长刀疤、臂上纹着大片刺青、腕上绕着佛珠的Z哥执意要送母女回酒店休息。干露露的腕上也缠着一串佛珠。她一路都恹恹地,突然冒出一声要去附近某寺烧香时才显出精神。母亲说不行,第二天要赶广州的场子。“不!明天早上6点起来,我自己打的去!”父母亲都说,这女儿是一根筋,相当任性。
宝马车里,Z哥说着体己话,对母女的作为深表理解,并向身处低谷的干露露指一条路:见好就收,把自己洗白,走舒淇那条路。他说,就在前一天,他把露露的人体艺术照集中看了一遍,认为很美,毫不淫秽,就像早些年的汤加丽。他买过汤好几本画册。
“有了名气,露露你该转向影视圈。不过你身材没有以前好,肚子上有肉了,该锻炼锻炼跑跑步。”母女并不搭腔。在他挥洒江湖义气的段落,干露露倒在后座,表现出“睡着了”。雷炳侠说,女儿早上5点睡的,6点起来赶航班。
Z哥执意要送到房间。他把自己摊在沙发上,忽然说起最近香港三线小明星到内地“做生意”的行情,并拿出手机展示靓照。转而说起本地某总或某哥有意挥金一夜,不过“都乱报价”,而他,是来代询价码的。
“媒体炒红了她,让男人有神秘感。男人也有虚荣心……”他终于向雷炳侠开口。母亲果断地摇头,也不动气,赔着笑说:“我们如果挣这种钱,就不会走南闯北这么辛苦了。”
Z哥将了一军:“今晚好些人跟我直说的,看到本人,很失望。”他最终发现不是价格的问题,走了。
干露露从洗手间出来,嗤道:“老娘不挣这钱。”紧接着是那句公开说过许多次的“名言”:宁愿在台上脱光,也不愿在台下被扒光。她看着我的反应,忽然就没有了继续的兴致,她知道我已在河南跑了一圈。四五年前,她报名《新京报》“北京宝贝”活动,编号673,受访时说自己是江苏南京人——是的,如信阳商城县的大姨所说,说河南别人瞧不起你。2011年2月14日浴室征婚视频一夜火爆的第十天,干露露一家三口上了一档河南电视台的节目,这才公开了籍贯。
那档节目似乎开启了这对母女从网络红人摆渡到主流媒体的旅程。父亲干德轩告诉我,2011年,他们跑遍了除新疆、内蒙、海南3省的全中国,电视台和商演邀约不断。两年过去,集中观看她们在娱乐类节目中的表现,可以发现基本上是河南台那档节目的延续,只不过尺度越来越大,表演越来越火。火到2012年底,她们在前江苏教育电视台《棒棒棒》节目中“翻船”,广电总局下了封杀令,干露露的事业滑至谷底。奇怪的是,节目从未在这个台公开播出过,只是假借某门户网站的视频档快速传播。而我在采访中发现,邀请过干露露母女或者再加其父其妹做嘉宾的那些个电视娱乐类栏目,如今统统不存在了。
网络还在。虽然一小部分与干露露有关的视频点开即是“你所收看的内容已被删除”,但病毒似地传播使得“名人”的影响力挥之不去。只是有时候,“名声越来越大,楼层越来越低”。“我喜欢跑车展,只要到一下场就可以了,而且都是白天。”干露露说着跑夜店的不易,“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工作了,一家人得吃饭啊。”
摘下墨镜,这个28岁的姑娘有着宽大的额头和窄小的面颊,像她的父亲。以挑选舞者“三长一小”的标准(手臂长、腿长、颈长,头小),或者上镜的要求,她也算中等水平。只是,她没有耐心读完那些文化课程。初中毕业之后,用父母的话说,她读过的那些高中、商校或艺校,没有一个拿到毕业证的。“我为什么要在学校里耗?老师也不喜欢我。我就想在实践中学。”干露露裹着浴巾,开始妆扮。
她在片场学会了站位、不挡住别人的光,也托人买过一些声台形表的教材。但表演最后拼的是对角色、对人性和对世界的理解,是需要文化支撑的。一位跟她合作过的导演告诉我:这姑娘很一般;对着镜头,她也哭了笑了action了,但背后没东西,是空的。所以许多年里,“小妞,在忙什么?”“还能做什么,疯狂跑(剧)组呗!”
她忽然想到Z哥的背景,烦躁起来。此次南下,母女俩只收到少许的定金,还不够支付两人从北京飞来的机票。不,必须在登台前把钱拿到手,这是跑场子的惯例,也是合同上写明的,然而江湖凶险,现金为王……我回避了要钱的一幕,因为干露露“很不自在”。没有人愿意被生人注视着在电话里就把钱挣了。在她扑腾经年的那个贵圈,这还涉及商业秘密,所谓身价。
她希望媒体像对待章子怡、周迅,最好像消费范冰冰那样对她,在她铁了心“要成功”的路上推她一把而不是相反。她讨厌刨根问底,更讨厌记者写她“不漂亮”。“媒体才是婊子!”她脱口而出,抬高了声音——面对这个我已经看过她童年模样、听过她不少纯真往事的姑娘,我得费点力区分,哪部分是演戏,哪部分是真的——这一句,相信是她的肺腑之言。
半小时后,一个紫红色丝绒袋子送到房间,里面是现金,不很厚,但也算一撂。干露露在用卷发器卷着长发,雷炳侠在学习使用宾馆的保险箱。当她最后把这只袋子放进保险箱并记住密码之后,找了一件女儿的衣服系在上面。“事情多,这样我就记得有东西在里面。”
干露露带了半箱子戏服,演出穿什么、怎么穿,都是她自定。在她北京的家里,有一屋子这样的衣服,包括那件银色的暴露一半下肢的连体衣。干德轩做了4个架子,才把它们一一挂起。这个世界,仿佛已经自由到可以放任个人意志,随手留下些什么,比如,一些“名言”,一屋子有些奇异的衣裳。
干露露选了一件本色丝质长袍,如果不是后背袒露,一侧裙裾开叉高到露出半个臀部,它实在就是一件睡衣。雷炳侠说,这是反穿。我不敢想象正面穿它的效果。
干露露没有请我回避或者进洗手间,开始换衣服。在意识到她可能要换装的时候,我已将脸转向别处。没有任何动静。我一转头,看见艺术照的本体,无数宅男性幻想的肉身。可我是同性,为什么也表现得这般鬼鬼祟祟、欲看又止?是了,女人在陌生人面前宽衣解带,这是禁忌。所有对禁忌的挑战都是诱惑,一经包装,便成神秘。
她在镜子前面反复打量自己,最终决定在裙子里面穿一条内裤。寻找乳贴的时候,她向母亲发了脾气:“怎么都没有粘力了!就没一个能用的吗?”待演出完毕卸了妆再赴宵夜之前,她不耐烦地向母亲要:“袜子!”
床上摊着一大堆化妆品,地上躺着一双后跟锥子般细长的红色高跟鞋,它的坡度,比儿童乐园的滑梯陡峭多了。干露露要把自己支在上面,登上1米高的舞台。
为了解决开叉过高容易走光的问题,向客房部要来4个针线包。母亲赶紧穿针引线,我找了两个别针勉强扣住那道门帘。当我的手指隔着丝绸轻触到干露露皮肤的瞬间,她一颤,极轻微,我立刻读出那种对陌生人的抗拒、防备,甚至羞涩的成分——敢于裸露身体,对陌生人的靠近却有惊悸,对世界极度缺乏信任,于是只有演戏,只有谎言,只有目的-手段-结果。当我提议雷炳侠去我房间,让她一个人换装收拾时,母亲说,她不敢一个人待在房间里。这一次,我的表情比较符合她的预期,她笑了,仿佛在说:你不懂的。雷炳侠说,这些年,女儿很少出去参加饭局,除了谈“工作”、“事业”,她把自己关得紧紧的;她对男人,没有兴趣。
她把自己堆起来,画好了,去给男人们看,像是换了一个人。她在镜前照了又照,趿着一双宾馆拖鞋进了电梯,依然对着镜子端详,毫不理会电梯里一个外国男人略带惊诧又心领神会的目光——她脸上厚厚的粉和鲜红的唇实在不宜近距离相对。母亲提着她的高跟鞋、补妆用品、“貂”和“袄子”。
跟线永京走在北京茫茫的大街上,在逃难一般肮脏混乱的信阳汽车站挤上去商城县的中巴,走在干露露童年无数次经过的崇福桥上,看放了学跳着走路的孩子们,看岸边柳树下拄着棍子摆摊算命的盲人,我常常出神:这姑娘是怎么一步一步长成现在这样子的。
线永京出生于1984年,比干露露大1岁,他们都是,如雷炳侠时常戴的那顶帽子上印着的:80’s。
线永京是北京怀柔人,在没有深度卷入网络红人制造业、成为“非我非非我”之前,他活得平淡又平静。如果不是2011年春节在一个朋友的年会上认识了干露露,他是一个点子挺多的勤奋的拍客;如果不是2008年末在地铁通道里拍摄了“西单女孩”任月丽唱的《想家》并上传到网络,他也许会继续在朝阳区一家网站当美工;如果不是女友在两周前送了一部数码相机给他,他不会这么快在街上蹓跶着就拍出了作品;如果不是2008年3月他一手炮制的恶搞音频“不入流广播电台”在互动音乐网SongTaste上疯传,他不会迷上“网友的热捧”……可是,生活无法倒带,无法如果。
短短两三年,他的容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后来在网上看到他2010年12月去上海参加“G客G拍颁奖大会”的模样,才知“阳光”是本色,“颓”是后来的造化。我们约在北京的地铁站里见面,远远看见一个瘦小的男孩,及近,发现耳朵里塞着耳机,胡子没刮,脸色苍白,额前的头发很长,拨向一边,几乎遮住眼睛。他从一副流行样式的黑框眼镜后面,睥睨着,眼光漂移着。及至开口,他思维跳跃,语速飞快,把愤怒、失望和虚无,连同那些诗意尚存的部分,一股脑倾倒给你。
拍任月丽的时候,线永京还不懂炒作,他只是感动,感动于那清澈的歌声,那种“净化心灵的力量”。他没对视频做任何处理,比方加字幕、个人logo,就传到了网上。朋友们帮着传播,很快就火了。而火,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半个月后,线永京打开博客,发现这段视频的点击量是10万;打开QQ,成百上千的人在申请加他,他的手就一直在那里点着,点击鼠标,“同意添加”,这感觉令他舒服。
早在2004、2005年,前辈浪兄、陈墨、立二拆四、非常阿锋活跃在网络上,制造出“芙蓉姐姐”、“流氓燕”、“天仙妹妹”等新鲜热辣、吸引眼球的红人。她们制造的点击率是网络营销的一部分,因为规则是这样定的:点击率代表流量,流量是网络广告投放的重要指标。没有人质疑过这种规则,比方,点开“你所收看的内容已被删除”,或者点了8下才能看完一个简短的故事,我就很想把那些点出去的,要回来。点击率,是网络的GDP。
炒作网络红人的大致流程是这样:发现有争议的人物,通常是非凡的女性,敢说敢做——这个门槛在不断抬高,退出江湖已久的陈墨近期说,如今要想在网上红,一定得是小姑娘,还得漂亮。接着,联系对方达成合作意向,开展形象推广;找知名写手挑起话题,吸引网友关注;把话题“养”到差不多熟了,联络大型网站的编辑或论坛版主开始力推——网络编辑通过首页推荐、制作专题,网络版主通过加精、置顶、标题漂色,来提升流量和排名。接下来,传统媒体跟进,推波助澜。
现实利益紧随而来,这才是关键:广告代言费和商业活动出场费。可是,名人对商品购买会产生什么样的推动力,专家们有不少研究,据说关键取决于“名人的特性”与产品特性的匹配程度。演员王志文就想不明白:产品怎么卖着卖着就变成卖脸了呢?看见某位名人捧着一袋水饺,你就会生出购买欲?还是他说饺子馅多一定假不了?但不由分说,作为时代的“常识”,大家都接受了。
还有车展。在一个欣欣向荣的发展中国家,为买车的人多提供一点视觉餐饮是商家体贴。然而,当车展都成了肉展硅胶展(网友语),进了车展只有三问:大门在哪儿,厕所在哪儿,干露露在哪儿(郭德纲语),不知静静趴在那儿的车们,怎么想。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