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钧今年47岁,依旧爱着摇滚,但身份已不仅限于只是个歌手了。这些年来,他的曝光都不多,新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发,或者可能再不发了,偶尔出现在国内选秀节目上,毒舌起来,调调也非常像“年轻时的自己”,只是尖锐程度已经降到让人能平静接受的水平了。与郑钧对话,新浪娱乐充分感受到他身上的变化——是那种有时间温度的、有世事变迁的、有自己领悟的改变——变化过程绝对不短促,而且在这个年纪谈转变,郑钧有十足把握,有一箩筐故事,更厉害的是,他的总结几乎以“金句”方式呈现,句句掐住重点,只剩下让人拍手称是的份儿。
郑钧说,云姐(妻子,演员刘云)是造成变化的重要因素,“她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总是会挑战我的底限……”夫妻生活是从两个暴脾气以暴制暴开始的,他一个西北老爷们儿,常年以大男子主义“镇压”对方,到最后却发展为,“回家云姐一瞪眼,我也心里哆嗦一下……”于是被挑战底线后的结果往往是:妥协,自省,发现自己原来还是很糟糕,还需要继续修行……对,这里说到修行,近年郑钧开始专注密宗修行,每天打坐。
新专辑主打歌取名《作》,“zuo”,第一声,大家爱说的“NO ZUO NO DIE”,在郑钧这里就变成了“NO ZUO NO LIFE”。我们就着这个话题聊了很久,他讲述自己如何从小作到大,说大多数人不喜欢别人改变,就喜欢所有人都一样,所以对他这样特立独行的人往往群起而攻之,为此,他打了无数架。不爱跟媒体打交道的他,心平气和地聊这么多,全程高度“自白”,坦然、细碎、风趣,实在难得!
理想化!纯度高!更愿意相信自己的选择。郑钧一直这么做了,就像他说的,“作别人可耻,作自己光荣!”

南音:先说这个专辑的概念,“作”(读:zuo 词语:作死)?
郑钧:《作》是这个专辑的一首歌,这个专辑有很多不一样的歌,就像我这个人一样,是一个很多面化的性格。选《作》这首歌呢,因为宣传团队他们建议第一首歌出这个,后来我想了挺好,因为我想我这个人的一生真的就是作的一生。但是我的特点是我从来不作别人,都是作自己。所以我后来跟他们说,很多人的幸福都是作出来的,作嘛就是改变自己,或者你想改变环境,有所改变吧。然后别的人,大部分都不想改变的人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这样都挺好的,你非要跟我们不一样,这就是作。所以就中国人不太喜欢别人改变,就是大家都喜欢都一样,不要老是显摆自己。所以对于那种有个性的人和特立独行的人就觉得,这是比较爱作的人。所以对作的人大部分都是群起而攻式的。我从小就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人,我总是在大家一起在干某件事儿的时候,我就去干别的事儿了。
南音:比如说?
郑钧:比如说我干的第一件作的事儿就是,小学上了俩,中学上了三个,然后到处乱跑,换了中学就打架,也不是我打架,别人找我打架,就全是这些连滚带爬的事儿。好不容易,小时候学画画,后来到要考美院附中的时候,发现我认识的画家都是跟要饭的差不多,我也就放弃了这种生活,觉得太惨了。人生本来就够惨的,如果以后你未来还是这样,那就别当艺术家了!放弃以后家里都是工科的嘛,我们家的观念是工科最起码不会饿死,有一技之长嘛,所以说那还是考大学吧。好不容易上大学,又莫名其妙爱上摇滚乐了,又当摇滚歌手,组乐队。我妈事后跟我说,当时觉得我神经不正常,疯了。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的乐队的朋友们他们正常毕业了,各自去回归现实,就该当工程师当工程师,该上班的上班,只有我……然后觉得这太不现实了。
南音:他们都特别理性。
郑钧:工科的人都比较理性,理工科,我其实也有理性的一面。但是当我特别不理性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我肯定疯了。结果神奇的是,最后我真的当了歌手。当然其中也很多的曲折,这个行业本来就有很多随机性。反正是换了两三家唱片公司。比较难相处。
南音:你说你自己比较难相处?
郑钧:别人反应比较难跟我相处,但是现在比较好相处,原来比较难相处。然后离婚,然后又再结婚,生孩子,然后开个酒吧,后来又投资做动漫公司,投资做乱七八糟的事。我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喜欢做一些不现实的事儿吧,我干的事儿都是我喜欢的事儿。如果没有一个喜欢的动机的话,只是赚钱的话我基本不去做。我有过这样的机会,好多年前朋友跟我说,合肥那有一个煤矿,多少多少钱就可以拿下,产煤可以赚多少钱。特别认真地跟我说,我觉得,这跟有什么关系啊?!(回忆起这个不由自主大乐了起来)我当时确实有点钱,可以买那个矿,但是我觉得这有什么意思呢,让我到那天天看着一口井或者看一个矿,它是印钞机。
南音:你也可以买了让别人看着?
郑钧:没有,我得用我这个歌星的身份去跟人聊,让人家把这个矿给我,肯定是这么一种情况,别人拉着我也不是白让我去。所以各种这类的项目我都拒绝了,我说我真做不了!确实赚钱的方式很多,但是有很多方式我自己觉得我承受不了。赚了钱以后,会每天抱着钱打我自己,我受不了,精神上承受不了。后来我投资动漫公司,自己放进去很多钱,又是我发起的公司,我是创始人。这个电影5000万美金,投了人民币好几个亿,大家都放钱进去,明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应该能上映吧,但是我也不能给你保证肯定。(笑)所以我干的事儿别人觉得很奇怪,我是经济管理系的对外贸易专业,从投资回报率来讲,你干这件事儿时间成本和投的钱的成本,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但是这就是梦想,我喜欢干这件事情。
南音:这就是“作”是吗?作了一笔又一笔。
郑钧:我刚才跟他们讲,我说别作别人,大部分作的人喜欢作别人,就折腾别人呗。作别人可耻的,作自己光荣,所以要多作作自己,改变自己其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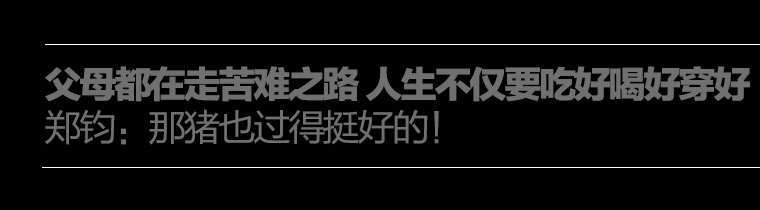
南音:你曾经有“作”到特别不安的时候吗?
郑程:我从小到大,其实大部分作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安全感,一种恐惧感,对未来的期待和恐惧。所以才想改变。因为我很小出生的家庭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
南音:很正统。
郑钧:很正统,很传统,就是西安的老家庭,传统的四世同堂的那种大家庭,一家子聚餐的时候能100口人坐在那吃饭,就从西安最大的西安饭庄请来厨子做饭。这种大家庭就一切都要保守、规矩,家教特别严,吃饭怎么吃,筷子怎么放,长幼有序,就是儒家的这一套就特别严。父母也觉得他们生活是这样,希望你沿着他们的脚印走,很安全,因为他们脚印踩过了,都是实的地方,你可以走,不会掉进沟里边去。但我要换一条路走。他们都是很好的人,非常善良,但是他们人生充满了坎坷,就是因为他们的道路就是沿着他们父辈的道路去走,那条道路就是苦难的道路。
南音:什么是你所谓的苦难?
郑钧:最大的苦难就是这种情绪、烦恼。人活着大部分时间,第一是活在这种真实的追求上,我们天性要追求某种能抓住的东西,希望有好的家庭,好的工作,然后有好的收入,赚很多钱,买很多想买的东西,然后由此我们就认为,我活的特别好,我活的特别安全,我活的特别幸福,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幸福。但其实这些幸福都是转瞬之间就能逝去的。如果活着就是为了穿好点,吃好点的话,我早就达到这个目的,那我接下来干吗,等死吗?接着穿更好的,吃更好的。所以人生绝对不仅仅是这样,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人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猪也过得挺好的。
南音:那您这个年纪还有什么事可以被年称作是作的?
郑钧:我这个年纪,我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今天在舞台上连蹦带跳唱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居然蹦成这样,居然也不喘。好像比我20岁的时候的体力还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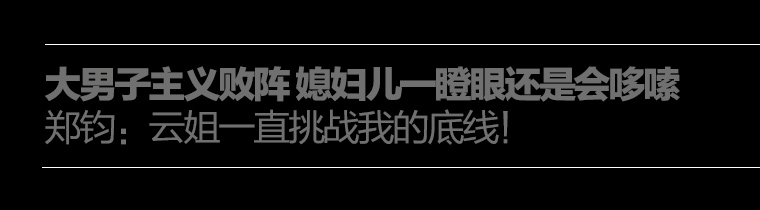
南音:现在你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郑钧:当然从普通人角度看,这种生活方式很作,神经病,你有这样的机会去赚钱为什么不多去赚钱。差不多每天早上起来先做做瑜珈,做一些我觉得西藏瑜珈,打打坐,还做一些修行的功课。这个完了当时两三个小时已经过去了。然后如果起的太早就去睡个回笼觉,然后再起来开始工作,也不一定开始工作,就不知道会干吗,也可能会出去转转。要演出就演出,没有演出的话看书吧,然后哗这一天就过去了。
南音:好像这么一说的话,你干每一件事情的时间跨度不是那么长,这样的话改变就一直在进行。那家庭方面会不会因这些有一些变化?
郑钧:没有总是在改变,我是一个挺长性的人,该尽的责任都尽的挺好的。然后做一个好老公,我现在没有夜生活,也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就晚上不出去喝酒应酬,没有酒肉朋友,完全没有。然后也就没有应酬,我晚上不出门,我也很久不去卡拉OK,也不去夜总会,迪厅都不去。
南音:云姐是不是改变了很多你平常的处事风格?
郑钧:云姐对我有很大改变,当然她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人。按照我原来的状态的话,我们俩完全不可能生活在一起。
南音:原来是什么样的状态?
郑钧:以我认识她之前的时候的那种生活状态,要遇到云姐这种女孩,我是大概5分钟之后转身就走了,我受不了这样的人。但是命运就把我们俩放在一块,而且在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然后从一开始我们也是相热恋过,也互殴过,就是很多的这种挣扎。但是依然还是相爱的。她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总是会挑战我的底限,我觉得挺好的。我从小很大部分周围人都是宠着我,让着我,走哪都是别人都对我很好。遇到这么一个老挑战我底限的人也不太容易。所以每一次当她挑战我底线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原来是如此糟糕的一个人。我原来以为我好像脾气挺好了,好像能够跟各种人相处的不错了,然后她一挑战的极限,我发现原来我还是很糟糕,还需要努力再继续地修行和改变自己。(笑)
南音:她都怎么挑战你的底线?
郑钧:她挑战我的底线的太多了!
南音:比如说呢?
郑钧:比如说出门你要穿什么衣服,这个衣服不行,我不想穿这个衣服。不行!你必须得穿这个衣服。她给我买一个黑包,她说这个包特别棒!我其实特别喜欢简单的东西,我平常大部分时间穿的都是户外的衣服。户外的球鞋,户外的裤子,防风衣什么那种,因为我经常去户外,去西藏。我就是喜欢这样的衣服穿着,喜欢这样的流浪汉状态。云姐受不了,你必须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我背的都是那种登山包,她给我买一个皮包,你必须背着!这是最流行的一个什么包!我说好好……然后夏天,她说现在到夏天了,你要换一个蓝色的包,又给我买一个蓝色的包。我说不要这么浪费,我习惯了这个黑色的包,挺好的。然后又要让我背蓝色的包,我说好。背了这个蓝色包又过时了,她又给我换一个包,我就崩溃了!我说能不能别老换我的包!我装的东西很多,杂七杂八,我的包特别重,里边又放书,电脑,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特别沉,我的喝水的户外的杯子,什么东西都在里边。所以每次换的时候,只有把这些东西分门别类的要再重新放,其实我的东西有的是乱七八糟放里边,已经习惯了,我习惯那种流浪汉式的生活,特别习惯。但是她不行,你必须换。好吧。
我身上从内到外穿的东西都是芸姐买的。她把我自己以前买的东西都给我扔了!都是她买的。所以当我们吵架的时候,她发脾气的时候,她说你没良心的!不知好歹!对你这么好!你还这么对待我!你身上从内到外穿的东西都是我给你买的!我说,那我还给你!我就脱下来给她。有一次吵架吵的最厉害,在楼道里,她大喊大叫,我特别爱面子,邻居那都听着怒吼,我要跑了。然后她说,你把我的衣服还给我,我没办法把衣服脱了,光着膀子,我想进电梯,怕别人以为我流氓呢,我就到楼梯跑下去。然后下去以后给助手打电话,我说你赶紧来接我吧,救救我吧!所以,其实她就确实改变了我。我原来是一个脾气特别不好的人。
南音:比较自我一点。
郑钧:没有耐心,然后不太会为别人考虑,特别自我。所以你看今天我能坐在这儿跟你聊成这样,谈这么好。我原来对媒体就特别,完全不给面的那种,就我行我素,想干吗,想怎么着怎么着,就特别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今天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开始考虑别人的感受。今天我的变化确实有些归功于芸姐,我学会体会别人的想法。当她对我脾气特别不好的时候,我想想我以前也是这样对别人的。所以这都是活该啊!她的变化也很大,她也为我做了很多变化。她原来也是个爆脾气。我们俩是暴脾气对暴脾气。我们家原来经常东西都碎了,经常砸东西,墙上都有窟窿。但是后来慢慢就好了,大家一个磨合的过程。然后大家都明白,其实都为对方做了很多改变,还是很爱对方。
南音:你感觉到幸福了吗?
郑钧:这几年我的变化挺大的,我家人也有点害怕。不知道为什么,你怎么现在成这样了?我哥有一天突然问我,说你不是天天也在修行吗,打坐,你能告诉我什么是幸福吗?当时说这问题的时候我还真的愣了一下,完全下意识回答,我觉得放松就是幸福,真正的放松就是真正的幸福。
南音:现在是不是家里的事儿全都是芸姐作主?
郑钧:那不行。我是一个西北人,西北人其实大男子主义的。在外边得装的特别大男子主义,我们家都是我说了算。但是回家云姐一瞪眼,我也心里哆嗦一下。(笑)我们俩就都属于那种不太知道怎么生活,柴米油盐都不太懂,糊里糊涂的。云姐也不会做饭,我也不会做饭。然后云姐买东西经常买一堆完全没有用的,垃圾的东西她也会买回来,我也会经常这样,都不现实。但是好像在一起生活的也挺好的。

南音:周边也有一些比较作的朋友吗?比如说高晓松他们。
郑钧:那都是我作完以后冒出来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你作完了到那个地方发现这一块全是这么做的人。现在我们俩已经很少联系了,因为当他沿着那个方向走,我后来发现,我还要继续换个方向走。
南音:那如果让你评价一下你周边的朋友,你现在还会去羡慕他们什么?
郑钧:我周边还有朋友吗?(笑)
南音:有啊。没有吗?
郑钧:不是我把他们抛弃了,就是他们把我抛弃了。现在我几乎没有什么老在一块的朋友,我最好的朋友就是老跟我在一起打坐的一帮朋友,编剧廖一梅是,我们俩因为一起打坐成为了好朋友。然后还有一些不是这个行业的朋友,我们在一起做这件事儿。行业内的我真不太多朋友,因为很少相聚。朋友们把我开除了。我也不羡慕他们的状态。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可值得我羡慕的,你举个例子我真的不知道。
南音:那你现在还想“作”什么吗?
郑钧:那就作我自己,我希望自己能再继续改变,把自己改变的更好。我可能下边还会投资一个音乐的项目,对这个行业会有改变的一个项目。
南音:什么样的?
郑钧:过几个月你就知道它什么样子了,花了不少钱和精力投资做的一件事情。我几乎没有时间看电视啊或者其他什么的,有微博、微信我很少去弄。现在这个时代太奇怪了,有微信这些东西。朋友们有什么事儿随时给你发微信吧,就期待着你马上回,你要不回的话他们觉得你不礼貌或者不重视他。但是我经常是不拿手机在身边的或者我不看微信,我是一个严重拖延症的人,不愿意随时去解决这些问题。